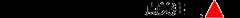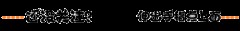《吴恩师的夏天》
文 / 武奋丰
编辑 / 杜强

一导语:
吴恩师喜欢唱歌,想成为职业歌手,甚至明星。这个梦想眼看就灭了,但这个夏天,吴恩师成了网红,“民工歌神”,人们这样称呼他。如今,他依旧在深夜穿行于大排档,卖唱、卖唱,仍在准备迎接他生活的希望。
吴恩师唱歌,唱到38岁了。
这事以前小学老师知道,说咱们班将来会出一个歌唱家,说的就是他;后来是同村人知道,说他唱着歌经过时就像一台放磁带的录音机。再后来是一些陌生人,比如2003年,他刚来广东打工的时候,有天坐车出去玩,这车把他带到一个广场上,那里正在办歌唱比赛。排在他前面的男孩唱了粤语版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吴恩师也报了名,他唱谢霆锋的《只要为你活一天》,唱这首歌时掌声响了三次,分别是刚唱一两句时、唱完第一小段时,唱到结尾时;掌声并不是浮皮潦草地响一下就灭了,而是“很多、很多”,那场面吴恩师记得清楚。
也是2003年,吴恩师在工厂旁的夜市唱歌时收到别人送的花,他因此体会到一种明星的感觉,跟刘德华似的——在这么小的舞台上也能有这种感觉,这就叫精神上的感受吗?现在,他想起这些时内心有了这样的疑问。
今年夏天,吴恩师唱歌这事几乎要被全国人民知道了,那首在老家房子里录的《他不爱我》上了网络热搜,仅在抖音上,这首歌就收到83.2万点赞,“被天使吻过的嗓音”,人们用对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的赞美之词赞美他。吴恩师不知道安德烈·波切利所谓何人,他听别人说这个时就像听一个不怎么感兴趣的八卦,没有更多好奇了,“哦,这样子啊”,他说。但即便这样,做直播也仍像之前一样没什么人看,能有400人在线就很满意了,不像今年,最多时有3600人在线,当时吴恩师在唱王力宏的《需要人陪》。

但说实话,吴恩师搞不懂互联网的这一套,视频挺火,但最核心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搞懂,为什么网络上的人那么爱听《他不爱我》,那么爱听《需要人陪》?以及,为什么自己突然火了,是因为唱歌时的表情吗?还是长相?还是录视频时的环境?再者,为什么别的网红火了可以赚很多钱,而自己却还过着和之前差不多的生活,住在深圳城中村月租一千的房子里,把每天的餐费上限定在50元,为家人在县城买套房至少眼下看来仍有点渺茫。
吴恩师梦想的是一种唱着自己的单曲、站在舞台上赚演出费的职业歌手的生活,而不是像现在,每晚踩着电动车来往于大排档,从一桌桌溢着啤酒和海鲜粥、烧烤等食物的桌旁经过,看着别人的脸色,带着试探与讨好的口吻,把写着每首30元的歌单递过去,问,老板要不要点歌?
二八月六日是雨后粘热的一天。晚上八点多,吴恩师骑电动车去大排档。他身上背着吉他,挂在车把上的白色塑料袋里放着厚厚的蓝色文件夹,那是他的歌本;立在车后座上的是用一根红绳码上去的黑色音箱,这音箱自2016年6月15号吴恩师开始卖唱时就跟着他,期间受过风吹和雨淋,也因此换过外壳。吉他则是第三把了。
来深圳后,吴恩师学过两次吉他,是别人告诉他,不管什么乐器,每个歌手都应该懂一门。吴恩师选了吉他。以便宜、实惠为标准,吴恩师找了老师,第一把吉他就是报班时送的,但质量不行;第二把则是吴恩师趁着星期天逛了很多次深圳乐器城后下狠心买的,花了400块,但还是练不好。
吴恩师心想,是不是吉他不好没心思练?他决定买一把好吉他激励自己。2014年,吴恩师花3000块买了把新吉他。同时,32岁的吴恩师又一次报了吉他班。报班时,琴行老师劝阻他,这年纪容易分心,学不下去,吴恩师不服,但上完课,发觉自己弹吉他并无天赋。
这把吉他现在每晚都贴在吴恩师浑圆的肚子,和他一起在酒声缭绕的大排档里往来穿梭。每到一个大排档,吴恩师就把他指尖结了厚茧的左手放到琴弦上,先弹唱半首,然后拿着点歌单绕着桌子走一圈,没人点歌就离开,赶去下一个大排档。若有人提着嗓子朝他喊“点歌”,或手臂往里一挥,借着酒气喊“这里”,又或朝他打个响指,吴恩师就循声过去,确认对方的确有点歌的意思后,转身去电动车上取下音箱和歌谱。几首歌之后,隔在肚子和吉他间的衣服会被汗水洇湿,而洇湿的地方会在去往下一个大排档的路上进入风中。
三这晚已将近12点,松坪山附近,药店已把卷闸门拉下,临街的炸串摊要营业至凌晨1点,711的橱窗里坐一排刚下班的年轻人。橱窗对面,一家大排档的烧烤架上仍排列着待熟的烤串,烧烤架前,客人多已散去,留下的男人们围桌而坐,年轻的十几二十,年长的三十五十。其中一桌,男人们正谈论“谁是SB”、互相争辩“我有没有给你打电话”,他们的声音总是旁若无人,自在散漫,有时又倏一下变得高亢,语气确凿:“风里来雨里去没有二话!”一天前也是在这里,一个男人乘着酒气直直地把手伸向夜空,问身旁的人,月亮在哪儿呢,问完又举起酒杯,酒杯和酒杯相碰的时候,不知谁说了句“上市!”。
一个亮着火星的烟头从饭桌上飞了出去,飞向吴恩师。他们找吴恩师点歌。围桌而坐的是一圈年轻小伙,扔烟头的那个长得干瘦,十七八岁模样。小伙们拿着歌单上看下看,等“老大”来了,才商量好要点一首《光辉岁月》。“老大”唱歌,吴恩师伴奏,小伙们鼓掌。之后是一首《父亲》,这次,举话筒的人里多了一个说四川话的小伙,小伙唱到动情处,抬起手背抹泪。
对于小伙们不加收敛的行为,比如那种使唤人的语气、随意冒昧的勾肩搭背,吴恩师秉持着一种严肃从容的神情。最后,一圈小伙争着付账,仍是“老大”作了决定,掏出手机付了钱。
偶尔也会遇到想赖账的客人,为防止到时没有凭据,有口难辩,吴恩师把客人点的歌都及时记在手机上。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周全的准备解决,吴恩师有时只能沉默。比如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次,吴恩师唱到“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时,点歌的半老男人打黄腔,伸出手指比划。吴恩师觉得难堪,但又不好说什么,后来在大排档遇到他时就远远绕开了。
也有遇到危险的时候。在南支路常去的那家大排档唱歌时,附近的住户曾因歌声太大往下泼水,这一般是客人听着歌心血来潮,开始纵声大合唱——吴恩师内心喜欢这场面,他记得电视里明星开演唱会时观众也在大合唱,但在大排档,他必须控制这场面,他得马上停止,降低声音分贝。
夜深时,吴恩师总得向点歌的人解释,“这个时间点不能唱大声”,有时客人理解,“没事没事,唱出感情来”——“上感情!”;但也有客人仍要求吴恩师放声唱,并不时说着,“大声一点……这样不行,老实说你这样不给钱的……”,或者“你那个嘴形唱歌,唱个屁!嘴巴要张得大大的!”这种喝令无论被谁遇到心里都会不快,但吴恩师渐渐习惯了,“不舒服那就顶个头好好唱,拿了钱赶快走”,吴恩师经历过更恐怖的时刻,那次,楼上的人往下扔玻璃瓶。
有时,大排档会成为某种抒情体裁,吴恩师像一个括号,把其中的一部分情感括了起来。
“我觉得生活最近需要开心”,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点了《新白娘子传奇》。
“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夹着烟,带着被酒闷红的脸挤着眉毛唱。
“我不要伤感的歌,要激情”,一个在肥硕的身体上套了黑色紧身T恤的男人对吴恩师说。
这天晚上,大排档里一个年近六旬的保安因吴恩师的到来显得亢奋,“我是打工的!”他以爽朗的口气介绍自己,并表达了对吴恩师的理解:“他们大半夜在这里嘻嘻哈哈吃饭,他给人家唱歌,不容易的。”保安频频给吴恩师鼓掌,一面夸他唱得好,一面隔着烟酒缭绕的桌子、吼着嗓子向吴恩师建议:“要唱沙哑伤感的歌——别闭眼,把眼睁开——”站在保安对面,吴恩师没回应什么,继续唱《好兄弟》。唱完后,客人紧接着又点了一首,吴恩师不会唱,他打趣地说:“大哥很时尚”。这晚,吴恩师唱了11首歌,收了260块——因为有些歌算了优惠价,有些歌则是他送给客人的。
四吴恩师知道,自己更适合唱悲伤的歌,欢快的情绪他表达不来,“唱不出那种气氛”。吴恩师将之归咎于自己的经历:如果从小生长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如果长得好看,工作、恋爱都很顺利,或许也会像现在的小年轻一样,唱出很嗨的歌。
吴恩师是2005年8月17号到深圳的,老家的同龄人基本都在打工,进工厂,搞建筑,当司机,起初吴恩师是他们当中循规蹈矩的一员,进工厂做了搬运工。但半年后,吴恩师就把工作丢了,他力气不大,不太会码货,工厂搬厂区时没留他。之后,他去自行车厂当了半年流水线工人,再之后,他决定在大芬村租房学画,他想画俄罗斯风景画,那时吴恩师23岁,觉得如果不能唱歌,画画也挺体面。
——无论是在老家养蚕,还是在工厂做工,吴恩师都没那方面的窍眼,他也不喜欢。在他眼里,农活和做工没唱歌、画画有意义。小时候,吴恩师给自己定过三个目标,唱女生的歌要唱到卓依婷的水平,男生的歌要唱到林志颖的水平,写字则写到卢定山的水平——卢定山是广西本地的书法家,吴恩师的父亲曾买过三本他的字帖,每本9.8元。后来到了深圳,吴恩师才知道,比卢定山更厉害、更正宗的书法家是颜真卿、柳公权。

在大芬村找房子时,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得知吴恩师租房是为了学画之后,建议他“最好不要学,该干嘛干嘛”,这么大年纪学画画是痴心妄想。就像后来学吉他一样,吴恩师不服气,仍在大芬村租了房,报名学画,学费每月200块。画了两个多月,吴恩师总把锥形树冠画得溜圆。
接下来,他做过投递、入过传销、摆过地摊,从十块钱的手动豆浆机到女式包,再到打气筒;从在公园门口摆摊被城管没收,再到站天桥上给路人演示打气筒如何好用,吴恩师在城市里的人流拥挤处捕食生活。摆地摊时,吴恩师遇到了前老板,前老板告诉他,你慢慢来,先慢慢起步,以后会成为大老板——“其实是错的”,现在,吴恩师回忆时这样说。
25岁那年,母亲催吴恩师娶老婆。彼时,在闲下来的日子里,吴恩师整天呆在屋中,孤独而烦闷,于是,按照情感电台的要求,吴恩师开始发信息,花六块钱,发三条信息,就能得到一个女孩的电话号码。借着情感电台,吴恩师和三个女孩见了面,但都无疾而终。和第一个在电话里聊了十多天,但八月十五那天在网吧视频之后,对方再没接他的电话;至于第二个,吴恩师曾在电话里给她唱歌,听着吴恩师的声音,女孩问:你是不是很帅?吴恩师回答,一点不帅的。到了见面那天,吴恩师吸取第一次的教训,将见面地点选在商场,还写了一幅字,卷起来带给女孩。但见面时气氛仍然不妙,后来,女孩问吴恩师,那幅字是你写的吗?她说他骗人。吴恩师不知如何解释,仍时常打电话给她,但女孩告诉吴恩师,你不要打电话过来,我们不可能的。
到了第三个,见面时女孩称自己肚子疼,提前离开了,吴恩师也没再联系。吴恩师不再给情感电台发信息了,他不是不相信情感电台,而是不相信自己。吴恩师觉得挫败,他认为问题出现在自己的相貌上,他想到小时候姑奶对自己说,以后长大了难找老婆。后来,有人给吴恩师牵线,给他介绍了一个文员。见面时,文员女孩告诉吴恩师,她想在深圳买房。这在吴恩师看来是大志向,他不敢想这些,他敢想的,是在深圳谋一份唱歌的工作。两人没共同话题,事情便不了了之。
之前,看着夜晚的高楼和灯光,吴恩师内心也觉烦躁,“这么多灯为什么没有一个属于我?连工作都找不到。”
五早前,吴恩师听萨顶顶和常石磊唱《他不爱我》听得流泪:唱歌的舞台为什么不爱自己?吴恩师感到无奈。结婚、生孩子,再回深圳已是2010年。当驻场歌手的事仍没着落,年近三十,吴恩师开始做凉茶销售。
之前几年,吴恩师一边打工,一边寻找成为驻唱歌手的机会。他为此买白衬衣,穿金色的闪闪发光的衣服去应聘,但每次都被拒绝。有段时间,吴恩师总站在布吉街边看往街对面,他是看酒吧一楼大厅里的驻唱歌手怎么唱歌。他想从他们身上寻找经验。也是从那里,他学会了《我要抱着你》。这首歌后来被吴恩师拿去参加比赛。比赛时,评委们先是说这首歌唱得好,但得知这首歌是网络歌曲后,又改了口,说他们不听这类歌。吴恩师纳闷,为什么?后来他渐渐琢磨通了,网络歌曲层次不高,不如经典的耐听。但后来卖唱,吴恩师必须学唱这种歌,因为总有人指着网络流行歌问:这首歌你会不会?直到现在,《广东十年爱情故事》仍是客人们点得勤快的一首。

后来他找到机会,在一家西餐厅当起了驻场歌手。但没料到,唱了两周,吴恩师就被餐厅老板“咔嚓”了。那天唱歌时,餐厅老板坐在台下,吴恩师唱得沙哑。后来,店长给吴恩师结钱,并说道:“老板说唱完这次就不要来了”。吴恩师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以前的老路。
2016年欧洲杯期间,因为要把场地挪给看球的人,吴恩师驻唱的烧烤吧给歌手放了假。就是这期间,6月15号那天,吴恩师站在欧洲城的街口,一个报亭旁,开始卖唱。行人陆续走过,他们给吴恩师放在地上的包里放钱,报亭老板给了10块,吴恩师至今记得他。这天吴恩师挣了140块。但转天,城管来了,“快走快走”,城管喊,不得已,吴恩师厚着脸皮,开始在大排档卖唱。
但一个问题始终困扰吴恩师,他有时向别人求证:做大排档歌手会不会丢脸?对方回答,丢脸?你没钱的时候,你需要钱拿不出钱的时候,那才是丢脸的。就在前几天,在大排档唱歌时,客人给吴恩师递来一瓶王老吉,吴恩师不停拒绝,他担心别人把自己当作可怜人,乞讨的,“虽然说凭本事吃饭,凭能力吃饭,但多少会有点乞讨的感觉”。他至今不太愿意提自己在大排档唱歌的事,但每当老家人说他在外面是给酒吧唱歌时,他又不断纠正,“不是在酒吧,是在大排档”,他明白这两个地方的区别,酒吧是“老板请你”,“请为贵,请你证明你有价值”,“但卖唱不一样,卖唱谁都可以做,只是做得好不好而已”。现在,虽有时仍不免想到卖唱不体面,但吴恩师已慢慢习惯了,就像习惯别人说他丑那样。
六今年夏天,吴恩师翻唱的《他不爱我》火了,微博上,贾樟柯也转发了这个视频,并写道:这才是唱歌。吴恩师那时才知道,原来粉丝可以成万成万地涨。那几天,他激动得难以入睡,总在睡梦模糊中打开手机,看看粉丝涨了多少,是不是又在热搜榜上涨停了、下去了。上热搜令吴恩师觉得自己幸运,上一次幸运来临是他意识到自己有唱歌的天赋。
最近,吴恩师收到粉丝发来的私信:“我想请教你一下,为什么你这么火了,好像还整天住在原来的房子里面?”粉丝说的房子,是吴恩师在深圳的出租屋。
八月初,当吴恩师在抖音直播时深圳下了雨,视频里不断传来雨水打在某种又硬又薄的平面上的叮当声。直播间有人问,怎么会有这声音,吴恩师解释,那是搁在窗户上防止雨水淋湿衣服的铁皮,“这里环境不好,很糟糕的”,他告诉那些看直播的人。

这间出租屋位于珠光村一栋五层高的老楼,老楼里有未被小广告覆盖的干净的楼梯和墙壁。楼背后是山,山上布满苍绿的荔枝树。珠光村是吴恩师2005年来深圳后住过的第六个城中村,上一个是白石洲,再上一个是贤合村,再往前,吴恩师得对着地图找名字,他熟悉城中村附近的那些工厂和商场,但日子久了,把名字忘了。
吴恩师已在这间出租屋住了两三年。青绿的房门中央是“万事胜意”的门贴,门贴的金色边缘上滚一层金光。屋子里,卧室连着厨房,厨房连着卫生间,落脚地最多容纳三人站立。一根晾衣杆从房门背后引向对面墙壁,上面沉沉地压满衣服,靠房门这边的多是厚重的冬天穿的,对面的则是洗得干净的夏天穿的。卧室里,本就不大的窗户被开辟成小阳台,挂在小阳台上的衣服将窗户挡了大半。窗户对面是一个双层铁架床,铁架床的上层像一个杂货架,放着厚厚的棉被、闪着亮光的枣红色爵士帽、卫生纸、棉签、行李包,以及一些包装盒,相比之下,铁架床的下层则宽松很多,只铺了一张凉席,凉席上是枕头和被单。此外,卧室里目及之处,多是和唱歌有关的东西:话筒、吉他、音箱、隔音海绵、拳击沙袋——吴恩师曾拿拳击沙袋练肺活量。此外是一张矮桌和一面长镜,长镜立在房门口,镜面上蒙一层淡淡的灰尘。由于在大排档卖唱,吴恩师总是晚上八点多出门,凌晨三四点到家,倒头睡着后,醒来时已临近中午,太阳将天空照得亮白。所以吴恩师在这间屋子里没见过早晨。
如今,晚上路过大沙河时,吴恩师会想起以前在工厂打工的日子,那时下班后,他会和同事经过河边,逛逛附近,现在每天出去卖唱,没时间做这些。有时,吴恩师在骑电动车时分心,甚至会打睡盹儿,他在这些时刻体会卖唱的枯燥和乏累。
在1400万人口深圳,吴恩师没什么朋友,有时想到这点,他就觉得有点失败。尽管有时卖唱结束,吴恩师也会花五六十块和做代驾的司机们拼钱吃烤串,但跟他们没共同话题,往往是他们聊他们的,吴恩师在一旁安静吃着。这种孤独使吴恩师显得任性,有那么几次,在心里的烦闷没地方讲时,吴恩师临时决定,订一张隔天回老家的车票。尽管在这城市,打工者如游鱼般分布在各行各业,但吴恩师的特殊之处,正如他说的,“滴滴司机有他们的氛围,我唱歌只有我一个人”。至于卖唱的同行,每个人都默认着彼此的工作区域,平常互不谋面,几乎不可能成为同事。
现在,吴恩师最好的朋友是老家和自己一起长大的老表,老表在广州做装修工,愿意和他在电话里聊天。坐飞机时,吴恩师举起手机对着窗外拍,嘴里念着飞机的飞行高度和机外温度,他要把视频发给老表看。
七在吴恩师唱歌这件事上,父亲有着比家里其他人更胜一筹的热情。当吴恩师来北京参加央视的节目,母亲看得平淡,得知儿子被淘汰的消息时说道,淘汰就淘汰呗;但父亲则告诉吴恩师要加油、要拿奖。
每天,吴恩师都会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例行问题是昨天唱歌赚了多少钱。若吴恩师回答赚了五六百,父亲就在电话那边说,“诶,可以可以”,但若回答两三百,电话里就传来父亲的叹气声。事实上,更极端的时候是,吴恩师连跑几家大排档,最后仅拿着二三十元收工回家。
吴恩师努力赚钱,一个原因是妻子不需要外出打工,孩子们——五岁的女儿、十一岁的儿子——不至于成为留守儿童。在广西老家,那里经济来源主要是养蚕。吴恩师家不善农活,靠养蚕获得的收入在全村排名倒数,唱歌是难得的机会。
在老家,父亲喜欢提起儿子。他打电话把上央视的事说给吴恩师的舅舅听,又说给村里小店的其他人听,这在村里是体面的:“上过央视的人”。参加宜州区唱歌比赛那次,吴恩师自付路费,特意赶回老家,原因是想在老家的比赛里拿一次奖,让大家信服自己的实力。
和老家那些还在打光棍的同龄男人比,吴恩师已经娶妻生子,建立家庭;和那些外出打工的男人比,自己每月靠卖唱能有一万来块的收入,也还不错。但继续往上,比如和那些家里有小汽车的人比,吴恩师则因只能开着电三轮到镇上赶集而觉得不体面。和他们打招呼时,吴恩师感觉自己在另一个阶层。他心里还有很多实际的渴望。
八在松坪山,吴恩师常来的这家大排档,老板对吴恩师的了解仅是“他经常过来”;在他时常经过的、与他卖唱的地方不过二十米的炸串摊,老板娘对吴恩师毫无印象。至于健身房的前台,则一度以为吴恩师是干餐饮的老板。但吴恩师想出名,想因唱歌出名。17岁时,吴恩师在县城的音像店门口看到电视屏上刘德华的演唱会,舞台上的刘德华被台下观众的尖叫声包围。“很多人想跟他握手,谁不想像他那样?”
成为网红后,签约公司找到了吴恩师。“你愿意赚钱还是愿意出名?”公司那边的人问。“我想要出名”,吴恩师回答。
这些年,吴恩师参加了一些比赛,:在2012年的星光大浪劳务工歌手大赛总决赛上得了第一名、在2017年《星光大道》深圳赛区选手选拔活动中获得十强、在2019年拿了河池市宜州区“十佳歌手”二等奖,但这些似乎没改变什么,成为歌手、甚至明星的愿望仍像一个不断融化的雪球眼看就要被太阳蒸发,就在这时,雪球又滚起来了——吴恩师成了网红。
但吴恩师对如何把握这个机会并无想法,他不懂运营和包装,之前卖唱时,有人告诉他要把头发留长、染黄、扎辫子,要穿得更时尚,这样才能显得是吃这碗饭的。但吴恩师不喜欢这些,唯一的改变,是出于礼节,在卖唱时把凉拖换成了运动鞋。与此同时,吴恩师保持着一贯的诚实做派:他依旧在朋友圈发干农活的照片,“我希望呈现的状态是真实的,我是真正的农村人,发这些令我觉得我很诚实。”
在几家签约公司中做选择时,吴恩师选了“比较大型”的那家,判断标准是它有分公司。对于合同,吴恩师没有一条一条往下看,文字多的东西他看不下去;合同中有的地方他不太理解,但身边没人商量。因此他几乎是抱着冒险、赌一把的态度签了字。事后他也犹疑:我该不该相信他们?
九出名之后,和吴恩师熟识的店老板告诉他,一定要沉住气,不能像旭日阳刚。参加拍摄活动时,吴恩师觉得自己得到了来自他人的前所未有的热情,工作人员频频对他说:这边请、这边请。吴恩师在心里嘀咕:如果我真的走上那条路,会飘吗?
刚刚,在松坪山的大排档,吴恩师遇到了想拜他为师的人。那时大排档里已有人清扫地面,扫帚拂过地砖,发出沙沙沙粗粝的响;酒瓶的盖子滚落到地上,桄榔桄榔转圈;水管也来了,一股细水刷刷地冲洗地上的油污。吴恩师身旁,一个面色红润,头发灰白的男人开始点歌。男人穿得笔挺,白衬衣掖进牛仔裤,身旁站一条大狗。歌点好了,吴恩师坐在音箱上给男人伴奏,其中一首是《驿动的心》。男人唱得尽兴,拿着话筒仿佛站在舞台上,他踱着一种跳舞的方步,步子在吴恩师身旁弹远又弹近。最后,男人提出和吴恩师合唱一首《情网》,期间,男人连连赞叹,“噢耶,你太棒了,真想拜你为师”。但对于拜师这事,吴恩师拒绝了。
不只是这个男人,吴恩师火了后,网上很多人给他发私信,说要拜他为师,但那些压喉咙、颤音,振动,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这要怎么教?
吴恩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一直唱下去,别人问他,你能唱到多少岁啊?吴恩师就答,走一步看一步啦。一起来深圳的老乡对吴恩师说,“怕个屁啊,你唱到50岁没问题”,况且如今吴恩师在抖音上已经拥有了近50万粉丝。
在深圳,能供他唱歌的大排档正在减少,比如白石洲,拆迁使很多商户离开那里,大排档随之减少;再如西丽,有的大排档不让出摊了,白天,卷闸门拉得严实,空荡的店门立在布满商店的街上,人来车往,令人想到牙床上,一颗牙默然掉了。
吴恩师还没想过去别的城市卖唱,他发愁随之而来的一切需要适应的东西:要和店家建立关系,并且,如果撞上别的卖唱歌手该怎么办……如果有天不唱歌了,自己在世界上还能干嘛?吴恩师想着。家里人不反对吴恩师唱歌,母亲总说,不行就做工,但做工无法令吴恩师快乐。“实在不行还得做工,但歌必须得唱,除非嗓子唱不出声了”。
已将近凌晨一点,吴恩师正骑车从松坪山赶往南支路,那里有几家开得热闹的大排档。在松坪山和南支路之间,一条长长的白色隧道是吴恩师往返两地的必经之路。此时,吴恩师正穿行期间,他和他的电动车一起,在隧道一侧的窄窄的小道上快速往前。在他身旁,是一辆辆呼啸而过的汽车:红的,蓝的,黑的,白的,它们从他身旁经过,经过后就能进入可以沉睡的梦乡。但吴恩师不一样,吴恩师现在要去往南支路的夜晚,去问那里的人:老板要不要点歌?

抖音联合《时尚先生Esquire》,共同发掘并定义这样一群生活英雄:来自佳木斯的快递员老四,凭借生活赋予的洞察力被称作“东北观察家”;驻守淄博的创业者朱亘,演活了“枯燥总裁朱一旦”;“普通女孩”李雪琴,凭自己的喜剧天赋杀入脱口秀大会决赛;一口贵州方言的毛毛姐,用略带癫狂的表演为数千万粉丝带来“分裂式”的快乐;日复一日劳作的农民王业坤,突发奇想将物件一个个垒起来,展示出寓言般的、“无聊的”平衡术,被誉为“行为艺术家” ……
在平凡生活中创造超越性价值的普通人,同样值得被这个时代记录。他们是真正的“生活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