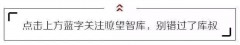4月10日,星期六,双兴堂澡堂,老马家祖孙三代一起在泡澡。马老爷子喜欢在双兴堂泡澡,周末,孝顺的儿子和孙子便一起作陪。
“东四南大街有怡和园,王府井八面槽有清华园,李铁拐斜街有东升平园,西珠市口有清华池,以前城里边儿澡堂子可多了。”一位大叔一边洗头一边如数家珍地介绍北京城的老澡堂子。他指了指自己肚子上的一条刀疤,“你看这刀口,我前两年得了肝癌,但就是忘不了每周大老远来这儿泡回澡。我打小儿住在安定门,洗遍了东城的澡堂子,这把岁数给澡堂子已经洗倒了好些个了。光为了洗澡,谁还能跑这么远?来这儿的人,都是冲着这里边儿的乐趣。”
“乐趣”位于南苑机场对面东二道街残破的空置院落和被绿色防尘网覆盖的瓦砾间,名叫“双兴堂”。有记载清朝镶黄旗子弟王双奎于1916年买下了3000平方米的临街地皮,盖上两层小楼,取号“双兴堂”,开起了澡堂子。
4月初,这间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澡堂子依然开门迎客,不过随着南苑棚户区改造,客人已经越来越少。员工李海洋已经干了13年,他说浓厚的人情味儿和老顾客是他还在坚持的动力。

双兴堂位于南苑机场对面东二道街,1916年创建。随着南苑棚户区改造,客人已经越来越少。

双兴堂洗澡票依旧保留着上个世纪的样式。

双兴堂内保存着石刻“池塘”二字。
百年间,时光荏苒,6米挑空的浴池碧水里,5道大梁的休息大厅中,24把躺箱上,双兴堂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不变的是池水荡漾、云蒸雾绕,玻璃天井下,通透的阳光里,三五成群的老爷子在这里搓着背、侃着大山、下着象棋、喝着小酒,消磨着时光,大家褪去外衣赤诚相对,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泡完澡,美美地睡上一小觉,不论待多久,全然不会有人打扰。

4月11日,休息大厅,几位老澡友刚刚泡过“头过水”。澡堂子每天一早新换池水,清澈干净,客人们都愿意抢着来洗。

4月11日,休息大厅,老澡友和搓澡工在下象棋,旁边还有澡友围观。

一位澡友在拔火罐祛湿。双兴堂拔火罐、搓澡、修脚价格都是20元。
在中国,有关公共澡堂的最早记录可追溯至宋代,并被呈现于经典画作《清明上河图》中。到上世纪30年代,北京各主要繁华街道都有了规模不等的澡堂。有数据统计,到1935年,光是北京就有123座老式公共澡堂,双兴堂便是其中之一。
独特的澡堂子文化使这里成了京城澡友最后的“精神家园”。“这里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原先这儿有一大个箩筐,里边有个大盘子,放着王麻子剪刀可以修脚,洗一次才两毛六。”65岁的齐大爷回忆起自己年轻时来洗澡的情景,“我一般一周来一次,现在还能碰到自己的同学,时间过得太快了……”
随着经济发展,家里已经可以淋浴或泡澡,澡堂子这个传统行业早已被收费更昂贵的洗浴中心替代。

4月10日,一位老爷子泡完澡后对着镜子边冲头边刮胡子。

一位澡友坐了3小时公交车从望京过来洗澡,他带着高粱酒和下酒菜在休息室解决午饭,在这里一般都是“文喝”,斯斯文文,慢慢悠悠。

泡完澡,79岁的吴大爷在做拉伸运动。他相信“筋长一寸 ,寿延十年”的说法。
4月初,中央美院油画系学生黄见晗正在双兴堂做老北京文化主题的毕业创作。“原汁原味的老澡堂子我寻找了很长时间,最终在这里找到了。和洗浴中心文化不一样,这里就是一群北京老爷子的社交场所,现在这种地方越来越少了。”黄见晗说,“老澡堂子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我想为这种古老的东西做一些事情,画出它的庄严感,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4月10日,黄见晗在浴池角落创作毕业作品。黄见晗是中央美院油画系学生,他认为老澡堂子还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1999年电影《洗澡》在双兴堂取景,电影生动呈现了老北京的澡堂子文化,反映了两代人对洗澡和澡堂子的不同态度。如今电影剧照依旧挂在双兴堂休息大厅的墙上,只是已经泛黄,但也实实在在提醒每个光顾这里的客人,澡堂曾经的高光时刻。

电影《洗澡》的剧照依旧挂在双兴堂休息大厅的墙上,只是已经泛黄。
东北小伙李海洋2008年来到双兴堂,干过领班、收银员、锅炉工、搓澡工,现在是这里的经理。他说,自2009年南苑地区开始拆迁以来,不少老澡友都搬走了,现在都是从全市各区过来的客人。以前旺季时每天能有两百多人,如今一年不如一年,在冬天旺季的时候超过一百人都难了。
但浓厚的人情味儿和老顾客是李海洋还在坚持的动力,正像电影《洗澡》中老顾客所言:“家里那热水器?一个人儿在那儿淋着,哪有跟这儿泡着舒坦!”

4月10日,李海洋在给顾客搓澡。2008年,李海洋来到双兴堂,干过领班、收银员、锅炉工、搓澡工,现在是这里的经理。
-The End-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影报道
版面图编 刘晶
本文编辑 吴飞虎 校对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