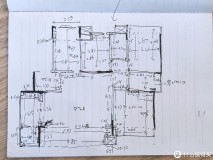每天读点故事APP独家签约作者:迟非·
1
凌晨四点。
巷子深处亮起了几盏灯火,厨房的窗户里飘飘然升出白雾,昭示着这一天的开始。
楚榆搬了把小凳子坐在门口和面。
这是她搬到昆城夕闻巷的第二天,在巷子深处租了间小房子,门口有棵歪脖子柳树,这地理位置说好不好,但说差也不差,每天傍晚夕阳西下,正从她家院子后头的围墙落下,景色一绝,只是对于做早点的摊贩来说,日出比夕阳要受欢迎的多。
和好了面,就开始调馅。
动作利索干净,一看就是手艺娴熟。
清晨六点,初春的太阳终于露出了头,楚榆在门口搭了个简易干净的小桌,蒸起了小笼包,旁边搭一个炉灶,平底锅上油滋滋的,长筷子翻出两张金黄酥脆的煎饼。
这是她的早点摊,和夕闻巷里那一排早点摊一样,摆的整整齐齐。
楚榆隔壁是夕闻巷里生意最好的早点摊,粉面馄饨一应俱全,一对年轻的夫妻档,都是圆乎乎的福气脸,眉目和善,没一会那摊子前就排起了小长队。
楚榆眼巴巴地瞧着,羡慕的不得了。
“小老板娘。”懒懒的声线响起,尾音拖得又软又长。
楚榆脸上挂着笑,擦擦手,抬眼,看见一个穿着长袍居家服的女人,桃花眼半眯着,散漫地打了个哈欠,眼角透着与生俱来的笑意。
谢檐喧一大早被江停从被窝里拖了起来,在堂屋里呆坐了半天,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才出门买早餐,一走进隔壁的夕闻巷,就闻见一股子香气,掺着油,勾的她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磨磨蹭蹭走到最里面,才看见一家新开张的早点摊,瘦弱的女人穿着干净的围裙正在忙碌。
楚榆有些小小的激动,从桌子上拿了张纸,上面写着:“您想吃些什么?”
谢檐喧耸耸鼻子:“我要两笼包子,诶,有喝的吗?”
楚榆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她指了指身后的一个长腿凳子,上面放着一个豆浆机。
“那就来杯豆浆。”谢檐喧又打了个哈欠,“多少钱啊?”
“小笼包十块钱一笼,豆浆两块钱一杯,一共二十二。”她又翻出一张纸,两只眼睛亮晶晶的,看着精神极了。
谢檐喧在口袋里扒拉半天才扒拉出一张皱巴巴的二十纸币,脸上有些尴尬,钱没带够。
楚榆把早餐包好递过去,瞅见谢檐喧手里的二十,心下了然,主动把二十块钱拿了过去,再把早点塞到谢檐喧手里,摆摆手,表示没关系。
在外面讨生活的,她贯来会察言观色,为人机灵。
谢檐喧睁了睁眼,对楚榆露出个笑:“行。”
有了谢檐喧开门,一大早上,楚榆的小摊子上还真来了几个客人,工作日的早上来去匆匆,排队的摊位不想等,就干脆去了不排队的摊位,这么一来二去,到中午十二点,楚榆早上还挣了小几百块钱,刨去成本,几十的利润总归是有的。
她也不贪心,只觉得尚算的上是“开门大吉”,满足的很。
2
“据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今年以来,昆城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在市容市貌等基础建设方面将下大力气整改,日前,城管部门透露,违规占地、违建、违拆等情况将在今年年中全部整改落实……”
一台老旧的电视机,昆城电视台正在放晚间新闻,楚榆捧着一碗热腾腾的饭,看的津津有味。
“砰砰砰!”大门被敲响。
楚榆搁了碗去开门,却实在想不到谁会来找她,毕竟她才搬来不久,这周边邻里还未结识。
开了门才发现是隔壁早点摊的老板娘,梳着整洁的马尾,笑起来两团苹果肌格外招人喜爱,她拎着袋香蕉站在楚榆家门外,见她开了门,把香蕉往前一递。
“我家老郑说你新来的一个小姑娘,咱们邻里邻居的,应该多多照顾,前些日子忙,这会刚闲下来,过来看看你。我叫何清梅,你以后喊我梅姐就成。”
许是这一片老城区还保留着淳朴的民风,家家户户都是相亲相爱的邻居,日常有个三两小事,都能相互搭把手,何清梅一家是这条巷子里最早做早点的一家,向来对街坊四邻都多有照顾。
楚榆受宠若惊,半弯着腰接过了香蕉,请何清梅进屋坐。
何清梅也不扭捏,大大方方进了屋喝了茶,跟楚榆一块看新闻。
电视画面上还在播报着城市改造的新闻。
何清梅喝了口茶:“年年争当文明城市,把我们这些小摊小贩折腾的够呛。”
楚榆笑笑,底层生活不容易,这新闻一出来,什么早点摊、水果摊、菜摊、小三轮车都得收敛起来,城管部门,那可是惹不起的。
把何清梅送走,楚榆坐在屋里理帐,想了想,从现金账面上拿了小一千块钱出来,用一个牛皮信封包好,准备随时急用。
晚上不到十点,熄灯睡觉。
时间虚虚过去,天没亮鸡没叫,四点的闹钟刚响,楚榆一个鱼打挺坐起来,搓了把脸起床干活。
六点的时候,最早的客人来了,随着天光渐亮,生意也逐渐不错起来。
那人来的时候,夕闻巷里先是一片沉寂,然后是拖桌子拽椅子的嘈杂声混成一片,楚榆正在做煎饼,冷不丁被吓了一跳,油溅到手上,烫到了一小块皮肤。
“发什么愣,快收拾收拾!”何清梅看着楚榆站在摊子后面发愣,赶紧两步过去扯了扯她的衣服,压低了声音,“城管来检查,不想被收摊子就别愣着。”
楚榆回过神,跟客人弯弯腰表示抱歉,手脚麻利地把煎饼一装递过去,然后拉起那方简单的木桌子就往后拖,桌上放满了东西,重得很,可她却顾不得那些,城管多厉害她又不是不知道,初来乍到,可不能惹上地头蛇。
着了急,就容易出乱子。
那桌子本就不怎么稳当,摇摇晃晃就要往后倒去,那桌上还有一盆热油,晃荡着吓人的很。
楚榆急躁,一个没防住,那桌子就要倒了。
眼瞧着那油将将要泼出来,斜刺里突然伸出一只大手,稳稳扶住那桌子,楚榆被人拉住,往旁边一扯,踉跄着栽进一个结实的怀抱里。
那人动作奇快,扶稳了桌子和楚榆,退了两步站开。
楚榆呼吸有些重,眼睛死死盯着那人的制服裤腿。
“谢……谢谢。”她埋着头,举起两只手,比了个道谢的手语。
“把桌子收进去,这段时间严管,就不要把摊子摆到家门外了。”
男人的声音低沉浑浊,没应楚榆的谢,自顾说着话,隔壁老郑抹了把脸笑了,抽出两根烟递过去:“行,听咱们岑队长的。”
打火机轻擦,烟头点燃,有轻微的燃烧声。
楚榆抬头看过去,是一个强悍的侧影,男人身体厚实、高大,一头寸板,鼻子挺直,深浓的眉尾后面一条短疤,将完整的眉毛破成一条断眉。
他薄薄的唇瓣里吐出一团烟雾。
看上去,很凶。
楚榆心道。
她从钱盒子里窸窸窣窣摸出一个信封,往前走了两步,扯了扯男人扎在裤腰里的衣服。
男人挑眉低头。
楚榆挤出一抹自认为友好的笑,小心翼翼把信封递了过去。
男人对上她的眼睛。
他睫毛很短,眼瞳颜色黑的发亮,盯着你的时候就像是把刀迎面劈过去,杀气重的很。
楚榆微不可查地抖了抖,把信封往前递了递。
“这是什么?”他开口。
楚榆咽了口口水,转身找了一支笔出来,在自己手心写了三个字:保护费。
初春早晨的风从歪脖子柳树的树梢掠过,扬起了楚榆额前的碎发,几缕粘在了她红润的嘴唇边上。
男人目光深深,转身就走。
何清梅瞧着男人带着城管队走了,赶紧过来拽楚榆:“那是管咱们这片的城管大队队长岑年,别看他长得凶,但人还不错,不会随便欺负人,你把钱收起来,这段时间守点规矩就没事了,不用怕。”
楚榆骤然松了口气,点了点头。
“哈哈哈哈哈哈哈,队长,我这还是头一回看到有人主动交保护费的,哈哈哈哈哈,我们又不是黑道,那小娘们至于怕成那样嘛……”
“你别说,老大眉毛一挑,那姑娘人脸都吓白了,直哆嗦。”
岑年抽着烟,带着城管队去往下一个检查点,队里的人开着玩笑,他向来话少,用力拔了一口烟,把烟蒂按熄在垃圾桶沿上,指着前面缩头缩脑在汽车堆里蹿的小三轮麻木:“柱子,去,把那台小三轮收了。”
早高峰,车流量那么大,还敢在马路上乱窜,真是不要命。
3
楚榆保住了珍贵的一千块钱。
她有些暗喜,晚饭时照例打开电视看新闻,电视台里有说起了市容市貌,城管部门负责人还接受了采访。
她看着,就想起了岑年。
像座未经驯服的沉默野山。
人还挺好,瞧着凶,但不欺负人。
楚榆决定下次再遇到他,请他吃个煎饼好了,毕竟能遇到一个好地头蛇是件不容易的事,她要是想在这里长久混下去,势必也是要同他打好关系的。
睡前做的决定,醒来就成了真。
也不知道这种体验,楚榆喜欢还是不喜欢。
凌晨起床,楚榆把屋子两扇大门打开,把小摊子支在了门槛里面,一丝一毫都没越过去。
还不到六点,晨曦冒了头,光柔和又温暖,楚榆坐在小凳子上包着小笼包,一小团肉沫放进面团里,两只手顺着折。
有脚步声过来,她仰头,欢喜的神色怔住。
来人穿一件黑色的褂子,褂子有些旧,贴在他身上显出肌肉隆起的形状,脚踩布鞋,就像小区门口看门的大爷,身材粗犷威武,往那一立就是一座山。
岑年往小摊子上放了15块钱:“一笼包子,一个煎饼,一杯豆浆,多一块不用找。”
楚榆慌慌张张起身,在围裙兜里放着的干净毛巾上擦了擦手,从蒸笼上抽出一笼就要给他打包。

(本插画为每天读点故事App官方特邀创作 插画师:THR)
“我就在这儿吃。”岑年目光沉沉。
楚榆有些为难,四下里看了看,没有位置坐,原本是有几个小桌子摆在门口的,只是过了昨天那一遭,她哪里还敢在门外面放桌椅。
“给我把凳子。”岑年像是知道她要表达什么,随口说了句。
楚榆只能照做,从屋里搬了个小马扎,把小笼包和调料放在自己的小摊子上。
岑年长手长脚,在楚榆家门口,倚着门板一屁股坐到那小马扎上,拿起包子就吃。
他进食的速度很快,吃完就走。
楚榆赶紧放下手里的活,两步蹿出去拉住他,她的手很凉,手掌有薄薄一层茧,岑年的手腕却热得很,贴上的那一刻,岑年脊柱像是通了电,酥麻到了尾脊骨。
楚榆手里攥着那15块钱,一个劲往岑年手里塞,使劲摇头,手推着他的手,眼睛瞪得大大的。
岑年倒觉得有意思了,昨天还想着给他送保护费,今天吃早餐还不要钱。
他弯了腰凑过去,漆黑的眼睛盯着楚榆。
楚榆立在那里,随着岑年的靠近迎来一阵强烈的男性气息,她倏地有些紧张,绷紧了脖子,心里打鼓似的。
岑年开口:“你很怕我?”
楚榆缩缩脖子,不敢动弹。
却见岑年突然嗤笑一声,捏住她的手,把钱塞了回去:“我不是恶霸,我来吃早点,给你钱,天经地义。”
说完直起身,侵略感骤然消失,楚榆偷偷喘了两口气。
岑年没再废话,拖着布鞋就走了。
楚榆站在夕闻巷的巷尾,看着岑年一步一步离开,巷子口是刚升起来的太阳,岑年迎着光走,脊背笔直高大,顶着天,立着地。
楚榆摸摸发烫的脸,心道:“真是个好人。”
4
原以为那日早上是偶然,却不想接下来一段时间,岑年日日早上趁着天毛毛亮就到楚榆这里吃早点,15块钱一份,吃了半个月也没见腻。
楚榆不能说话,岑年又是个锯嘴葫芦,两个人相处起来往往是从头到尾的沉默。
只是这沉默日渐变得亲近了些,楚榆不再怕他,每天早上就算岑年迟来个几分钟,她也会把他那份早点准备好,放在炉子上热着。
门口的歪脖子柳树发芽长叶,眼瞧着就绿了起来,日头一天比一天亮的早,可岑年却总能踩着日出,从夕闻巷口走到最里面,坐在那张小马扎上吃早饭。
照例是凌晨起床和面拌馅,楚榆忙里忙外,终于来了第一位客人。
那会天光已经大亮,照得歪脖子柳树的叶子绿的像是要沁出油一般,楚榆手上忙着,心里却泛起了嘀咕,忙碌间隙里转头看了眼屋里的钟,已经是早晨八点,却还不见岑年过来。
她勾着脖子往巷子口瞧了瞧,身子探出去,围裙掀泼了桌上的一碗豆瓣辣椒酱,红通通的酱料顺着桌子沿沾到了客人的身上,那客人身上穿了件浅色的运动外套,惊叫一声,跳着脚退了两步:“你干什么呢?”
楚榆回过神,脸上惊慌失措,张着嘴啊啊了两声,还沾着面粉的手挥舞着,打着手语。客人哪里看得懂,瞧着楚榆那副口不能言的样子,再看看自己身上的污渍,一大早的好心情全没了,火气一上来就嚷嚷了起来:“这是我刚买的新衣服,很贵的。你做生意就做生意,不知道在看什么,好了吧,弄我一身,你赔得起吗?”
楚榆焦急,脸上苍白一片,拽了几张纸绕过桌子就想凑过去帮人擦擦。
客人哪里容的她近身,手那么一推搡,楚榆身量瘦小,被推得往后一倒撞到了门口的桌子角上,正中侧腰,疼得她倒抽一口凉气,连身子都缩了起来。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装……”
楚榆摇摇头,满眼的乞求。
隔壁何清梅看不下去了,撸了袖子就要过去,却被身边的老郑一把拉住。
“你干什么?”
老郑不语,只是朝巷子口努了努嘴。
何清梅看过去,只见岑年穿着一身黑色运动装,正往里头走。
得了,靠山来了。
楚榆一个劲的弯腰道歉,手语打的磕磕巴巴,急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装什么可怜,残疾人了不起啊……”
客人话音刚落,楚榆那张本就惨白的脸越发白了,好像下一秒就算是断了气都不觉得奇怪。
沉沉的脚步声渐近,有一只手搭上了客人的肩膀,力气很大,像个老虎钳子把他的肩膀死死钳住,身后有抽烟的声音,火沿着烟卷往上燃烧。
“得理不饶人的滋味很好?”
岑年在烟雾里眯着眼,浑身的野性,一掌把那客人生生拽得倒退几步。他走到楚榆面前,高大的身子把她挡的严严实实,粗粝的手指夹着烟,抽了一口,然后扔到地上,用脚碾熄。
他开口,烟雾顺着往外冒:“想要多少钱?只说。”
那客人恐怕也是个欺软怕硬的,瑟缩了两下,仗着自己占理强硬地挺了挺胸膛:“这可是新款,我花了七百多买的。”
“你想要700?”岑年说话的音色较常人低沉不少,胸腔共鸣明显,总带着格外震慑人的气势。
那客人眼皮子抖了两下:“弄脏了,就赔……赔200吧。”
岑年大手伸进裤子口袋,掏出两张100和一张50扔进那客人怀里:“滚吧。”
何清梅在一边笑起来:“拿了钱就走吧,这数字真适合你。”
那客人气得脸通红,却又碍于岑年的气势不敢多嘴,恶狠狠“哼”了一声,转身就走,走之前还不忘把早点带上。
5
“没事吧。”
楚榆白着脸站在门边,手撑着桌角,眉头蹙着,有些担忧地看向岑年,然后轻叹了口气,半弯着腰走到摊子后面,从钱盒子里拿出250块钱,然后翻了张纸出来,埋头写了句话,连钱带纸一起递给岑年。
“谢谢你。”
岑年挑眉,盯着楚榆看了半天,完全没有收钱的意思,然后一个跨步也挤进了小摊子后面,手脚麻利地把楚榆摊子上的家伙什都收拾了,把桌子拖进屋里,转身对着楚榆就是一个横抱,大步往巷子口走,走的时候还不忘嘱咐何清梅。
“何姐,帮她把门锁了,我带她去医院。”
何清梅都看呆了,被他又叫回了神,应了声“诶”。
楚榆小小一团缩在岑年的怀里,扯着他的手臂,只晓得摇头。
岑年收紧了手臂,皱了眉:“别动,撞得不轻,得去医院看看,再乱动把你扔路边。”
楚榆眼底浮起淡淡的委屈,竟然还朝他鼓了鼓嘴。
凶巴巴。
可她又不得不承认,岑年出现的那一刻,她因为害怕而狂跳的心终于稳稳落进了胸膛里,那高山一般的背影,把她这只灰扑扑的可怜小老鼠遮得严严实实,把风雨都挡在了外面。
她靠在他的怀里,闭了闭眼,脸颊无意识的蹭了蹭,然后后知后觉的红了脸,竟再不敢去看他。
因此她也没看到,那个野山一般的男人耳后,也晕出了一层淡红。
楚榆坐在医院大厅里,看着岑年跑前跑后挂号等检查,嘈嘈杂杂的医院里人声鼎沸,可她却仿佛充耳不闻,目光紧跟着那个高大沉默的男人,片刻也舍不得离开。
说起来也令人难过,三岁丧父,四岁母亲不辞而别,她和爷爷生活在穷困的农村,在她能够记得的记忆里,刮风下雨,感冒发烧,都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初中毕业以后进城打工,举目无亲,浮萍飘摇。
这样的照顾与她而言,是奢侈的天边月,她曾经以为穷尽一辈子也许也只能水中捞月,妄想成痴罢了。
“没什么大问题,有点淤青,回去擦擦药就行了。”
“好,谢谢大夫。”
楚榆安静地听着,眼睛看着医生后面的窗户,窗户外有高大的法国梧桐,春天来了,枝上树叶青翠欲滴,停了只小鸟,转动着小脑袋,绿豆眼和楚榆对视了片刻,便扑腾着翅膀飞走了。
回去的路上,楚榆窝在岑年的怀里,被春日的太阳晒得昏昏欲睡。
岑年的大手抚了抚她的头:“睡会吧。”
迷迷糊糊睡过去之前,楚榆听见出租车司机说话。
“你对你媳妇真好。”
冗长的沉默过后。
楚榆脸颊边的胸膛震动了一下,头顶上有一声轻飘飘的“嗯”。
随后,是一场美梦。
6
像是无声的约定,谁也没再提起那天的事情。
楚榆常常在半夜里恍恍惚惚地觉得,那可能是一个幻觉。
街道工作人员往夕闻巷跑了两趟:“这两天市里有人来检查,咱们早餐一条街要注意一个卫生情况,尽可能展现一个良好的社区风貌。”
许是因着市里要来检查,岑年近几天忙多了,好几个早上都没能过来吃早饭,楚榆给他留了一份,从早上一直放到晚上,凉透了也不肯扔,直到第二天做了新鲜的。
周末有一场细雨,缠缠绵绵下了一整天,连空气都潮湿的不行。
楚榆傍晚挎了篮子去菜市场买菜,菜市场里夕闻巷不算远,过两个十字路口就能到。
天气不好,路上行人不多,前些日子猖狂的小三轮麻木也基本没了踪影。
楚榆刚过第一个路口,就听见一阵喧闹,街角挤了一群人,人群里有几个穿着城管制服,没打伞,湿了半身。
“啊……不准收,还给我,我操你娘的,你们这些城管就是一群强盗,只会仗势欺人。”
“胡说八道什么呢!信不信我抽你。”
“你抽啊,你抽,就怕你不敢。”
“我操,我给你脸了是吧……”
“柱子!”
穿过雨幕,是熟悉的声音。楚榆脚下一转,急急往人群里挤了进去。可刚进去,就看见一个男人手里不知道拿着什么往岑年那边扑过去,岑年退了半步还是让他划了一下,脸上划拉出来一个口子,顺着雨水,立马染红了半边脸。
有两个城管队员赶紧上前死死箍住那个男人。
岑年脸色极差,像是酝酿着一场暴风雨,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动手。
却只听见他说了句话。
“老子穿着这身皮一天,就要对得起这身皮。要是想讨打,等下次老子脱了这身衣服。”雨水混合着他脸上的伤口,看着可怖极了,“柱子,放开他。”
楚榆站在人群里看着,听见这句话,突然就有些怔忪,她想起十几岁进城打工的第一年,在夜市里给一个卖宵夜的小摊当服务员,那年夏天的夜晚,整条街都被打打摔摔得不成样子,领头那人状似流氓,凶神恶煞,掀倒的桌子噼里啪啦从她身上倒下去,生锈的小钉子在她胳膊上划开一条极深的口子。
那人眼中的轻蔑,仿佛匍匐在地的不过只是一只狗罢了。
记忆闪回,眼前的场景依然狼狈。
男人被放开,还准备再扑过来。
像是一场动作戏突然变了画风,一个瘦小的身影从人群里疯了一样冲出来,把雨伞挥得虎虎生风,往男人身上拼命打,就像是巷子里的妇人撒泼扯皮一样。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就见男人愣是被一个女人追打着跑远了。
岑年先是一愣,随即勾了嘴角,放轻了声音:“楚榆,过来。”
楚榆大口喘着气,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雨水从她的额头留下,沾染了睫毛,像树梢上嫩叶缀住的露水。
岑年看着她,脑子里突然就想到了一句话。
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瞧瞧,完全就是剧情再现,只不过换了位置。
他一向凶狠的脸上竟然有了几分松动的笑意。
楚榆走到他面前,看着他半张脸血糊糊的,张了张嘴,然后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却一点声都没有,看着可怜极了。
岑年瞧着她,心里软成一团,又被揪的疼。
大手粗鲁地往她脸上一抹:“多大点事,哭什么哭。”
楚榆却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恶狠狠地在他胳膊上打了一下,声音清脆。
城管队员瞧着,嘴角抽了抽,转开脑袋,全当没看见。
7
那天楚榆带着岑年回了家,烧了热水给他擦了个脸,好歹总算能看,才晓得只是道不深不浅的划口,只是混了水,瞧着吓人。
上了药,贴了创口贴,坐在桌前唰唰写了半天。
“不能沾水,不能吃辣椒,这两天别洗脸,要按时换药换创口贴……”
岑年看着满满一页纸,想象着,如果她会说话,一定是软绵绵的声音,絮絮叨叨个不停。
他贯来不喜欢人啰嗦,只有她,啰嗦再多,他都愿意受着。
楚榆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气性,好几天都没搭理岑年,早餐也不留了,等着人一大早巴巴赶过来,连个小眼神也不肯给。
想着第一天见的时候,她那股子畏缩的小模样,还真有些怀念。
小白兔变母夜叉。
岑年却也觉得不错。
没有早餐的日子里,岑年倒是找到了事情做,高高大大的身子挤在小摊子后面,给楚榆打下手,只是位置太小,他一个人占了大半,挤得楚榆总是烦的跳脚,狠狠踩着他的脚丫子。
看着狠,其实就像是挠痒痒一样。
傍晚收了摊子,何清梅过来给她搭把手,调笑着:“岑队长对着你,真是大灰狼变小绵羊。”
楚榆双颊飞红,眸光明亮。
似乎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在一起了。
可只有他们俩自己心知肚明,谁都没开口戳破这层纸,日子还是照常过着,岑年半分逾越都没有,他给足了她尊重。
这天下了班,路过菜市场给楚榆带了菜,顺路送过来。
六点多的时间,夕阳正好嵌在那围墙上,歪脖子柳树的树梢从夕阳的边缘垂下。
楚榆正在门口扫地。
岑年快步过去,半路截住了她手里的扫帚。
楚榆抬眼看他。
他拍拍她的背:“你进去做饭,我来收拾。”说着把手里的菜递过去。
楚榆打开看了看,两斤小排,几样青菜。
她顺其自然地打了个手势,打完才想起来岑年或许看不懂,想回屋找张纸,却别岑年拉住。
他近来表情温和了许多,眼神里总藏着一团棉花似的软:“好,我留下来吃饭。”
楚榆睁了睁眼睛,似乎不敢相信他竟然看得懂手语。
岑年也不多说,老老实实拿着扫帚干活。
8
春末夏初的时候,“种玉”来了个客人。
谢檐喧彼时正在忙,江停把人引进来,找了个凳子让他坐。
两个男人气势都很足,一个是外放的野性,一个是内敛的阴郁,王不见王,都不大待见对方。
等谢檐喧忙完,才来得及招待。
“哟,岑队长今儿怎么跑我这里来了?”谢檐喧在这里住的久,跟岑年也是熟识,她想来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打趣起岑年来一点都不觉得有压力。
岑年开门见山,红包往桌上一放:“我也不让你帮我介绍什么对象,我就想让你帮我去提亲。”
谢檐喧一口水没咽进去,全喷了出来。
江停黑了脸,拿了抹布过来擦桌子,顺便捞了张纸在谢檐喧脸上胡乱蹭了蹭。
谢檐喧被他蹭的一点老板的气势都没了,狠狠瞪了他一眼,转过头去继续跟岑年说话:“也没听见你最近跟谁处对象啊,怎么就突然要提亲了?我……已经很多年没干提亲这活了。”有一种旧社会,长着痦子,肥头大耳的乡间媒婆的感觉。
她挠挠脸:“你确定直接提亲?”
岑年点点头:“我想娶她。”他还郑重地起了身,朝谢檐喧鞠了躬,“拜托谢老板了。”
谢檐喧被他弄得还挺不好意思,挠挠脸:“成,那我试试吧。是哪家姑娘啊?你确定人家会答应嫁给你,现在可是新时代。”
“夕闻巷最里面一家早点摊子的老板娘,楚榆。”岑年抿了抿嘴,罕见有些紧张,却也十分自信,“你只管去,她会答应的。”
谢檐喧夸张地做了个表情,朝他挤挤眼:“人刚来,你就瞧上了,动作够快的啊。”说着还伸手过去拍了拍他隆起的肌肉。
江停瞧见了,脸黑的不能看,从厨房里倒了杯水出来,重重地放在谢檐喧面前,目光狠戾地盯着还放在岑年肱二头肌上的那只小手,恨不得给剁了。
谢檐喧茫然地瞧着他:“你吃错药了。”
谁知江停身上煞气更重,黑着脸去了院子里,搬了盆花,咔嚓咔嚓地剪。
“不理他,咱们继续说。”
岑年摸了摸眉尾的疤,像一个引子,点燃了一场回忆。
9
四年前的岚州,她是他的救命恩人。
那大概是岑年不太愿意回忆的一段过去,在鱼龙混杂的黑道里,给人当打手,帮人要债,整天活的昏天黑地,信奉着暴力才是解决一切的办法,那些年里,吃喝嫖赌那都不算事,要不是见不惯吸毒之后的荒唐样子,估摸着,他也是得去尝试尝试。
老头子临死前都闭不上眼,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小王八蛋”。
大概是老天爷实在是有些看不过去了,随手给他一些报应,差点没把他那条小命给收了去。
那天在赌场里,他有些红眼了,却遇上了硬茬,被人打了个头破血流扔在一个老旧小区的背街里,他也不过是人家组织里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喽啰,死了活着都没人在乎。
血流了满脸,渗进了眼睛,视线里血红一片,他仿佛看见他家老头子穿着白褂子大裤衩,坐在小椅子上摇着蒲扇,横肉遍布的脸上恶狠狠的:“小王八蛋……”
他嗓子里“嗬”了一声,卸了力气,倒在垃圾桶边上,突然很想念那个老混蛋,那个总是打他抽他,见不得他好的老混蛋。
说到底,他在那守着,他总还是有家的,只是,那老混蛋已经不在了,这世界上最后一个在乎他生死的人已经没了。
眼皮很重,他耳边是一遍一遍的“小王八蛋小王八蛋”。
再醒过来是在医院,多人病房里,他身边坐了一个小姑娘,扎着土气的马尾,发际线崩得紧紧的,露出光洁的额头,再往下是面黄肌瘦的一张脸。
陌生的一张脸。
岑年推了推她,她睡得浅,张开眼睛就是一激灵,那是一双很好看的眼睛,干净透彻,没有一丝一毫的阴暗,让他无端有些自惭形秽。
她有些惊喜,起身去按护士铃。
来人很快,她站在护士面前,手忙脚乱地比划着。
岑年动了动嘴皮子:“小哑巴啊。”
后来她在纸上写了经过,他才晓得,原来那群人把他扔到了她家后门,小姑娘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吓得不轻,发现人没死,火急火燎地送进了医院。
“你有家属吗?医生一直在问?”她写。
岑年包着一头的绷带纱布,脸还肿着:“没有。”
她有些丧气,提笔有写:“那我来照顾你吧,我请不起护工。”
“你怎么不报警?”岑年有些好奇。
谁知小姑娘轻飘飘看了他一眼,又写:“我怕报警,会有麻烦。”
“可你又不认识我,你怎么肯救我?”
“你还活着呀,我不能见死不救,我是好人。”写完这句话,她兀自点点头,像是自我肯定,又重复写了四个字,“我是好人!!”
干净的眼睛里有浅浅的骄傲,好像身为一个好人,是件令人骄傲的事情。
她不会说话,他贯来话少。
两个陌生人日夜相处着,她给予了他最好的照顾,不问名字,不问过往,尽心尽力。
岑年没见过这样的人,她很辛苦,打几份工,还有照顾一个病人。但她每天都很开心,她常常坐在他身边看着手里的旧书就能乐呵呵笑起来,她常常给他擦脸的时候还会揪揪他的眉毛捉弄一下,她常常跟他一起吃一份盖浇饭就觉得很满足……
他不懂,为什么她可以活得这样快乐和知足,甚至愿意倾尽一切去救一个陌生人。
他总是看着她,目光渐渐缠绵,但却充满了自卑和无望。
身体渐好的时候,他出了院,没告诉她,不辞而别。
“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电影里的台词,他曾经觉得肉麻,后来却觉得,真戳心。
再见,是四年后,在夕闻巷,她在一个早点小摊的后面忙碌,长胖了些,养白了些,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可很明显,她没认出来。
也是,岑年变化很大,壮了、黑了、高大了,和从前判若两人。
小哑巴啊。
希望四年后的我,能够配得上你。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你好,我是岑年。
10
谢檐喧上门的时候,岑年刚走,楚榆正在屋里喝水。
“谢老板,你怎么来了?”她打了个手势问?
谢檐喧十分自来熟地拖了把凳子坐下,翘起了二郎腿,眼角眉梢都含着笑,开口是个晴天霹雳:“我来帮人提亲。”
???
!!!
楚榆的嘴张大了,人都傻了。
可脑子里一晃而过的,是岑年那张脸。
耳后飘红,不知所措。
“别紧张,来坐。”明明是别人家里,谢檐喧搞得像自家一样,还招呼着主人坐。
楚榆乖乖坐下,像个守规矩的小学生,抿抿嘴,眼里都是疑问。
谢檐喧也没忙着开口,只把手里的袋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一张房产证、一把电动车的钥匙、一张银行卡、一个户口本和一把钥匙。
“岑年来找我,让我来帮他提亲,说实在的,现在这个年代按理说都应该是家中长辈来干这事,可岑年家也没其他人了,我托了大,替他来办这事。”
谢檐喧勾着水壶给自己倒了杯水,“这是他在来找我之前准备好的,挖空了家底把你现在住的这间房买了下来,房产证上写的你名字,还给你准备了一辆电动车代步,这是他的工资卡,他的户口,和他家保险柜的钥匙。”
楚榆伸手拿过房产证,看了半天,突然狠狠拍了一下桌子,气极骂了句:傻子,混蛋。
没有声音,可谢檐喧就是猜到了。
“岑年跟我说,你在这个社会里辗转漂泊了很多年,一个人,他很心疼,想给你一个家。无论你答不答应嫁,房子和电动车都给你。”
谢檐喧自己都觉得牙酸,瞧着岑年那副五大三粗、油盐不进的模样,想不到还是个痴情种。
楚榆又把户口本拿过去看,看着看着就哭了,眼泪哗啦啦往下掉,唇瓣张合了半天,颤抖着。
十四岁辍学进城,便是爷爷去世那一年,她带着几件衣服和二十块钱,坐着长途大巴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这个世界会吃人,她只能战战兢兢地努力活着,她羡慕城里同龄孩子的生活,只是她没有拥有那些东西的资格,她没有所谓的港湾可以供她躲风避雨,她只能一个人踽踽独行,希望未来能有希望。
她必须像一个成年人那样生活,为自己在这人海里找一个能够立足的角落。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她不曾停下漂泊的脚步,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她安心地休息。
可有一个人,淌着世俗的水,举着一块安稳之地,送到她的面前,甚至……不求回报。
其实,从他挡在她面前的时候开始,她就在想,或许她能在昆城一直呆下去,不再流浪了。
因为,吾心安处,即吾乡。
在他身后,她感受到了自爷爷去世后,十二年都未曾感受到的安心,所以,她已经疲惫的脚步,不想继续往前了。
“你让他……自己来跟我说。”楚榆写了几个字推过去,红着眼睛,脸蛋鼓着。
谢檐喧瞧着就有戏,乐的不行,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口袋里:“得,让他自己来说。”
那是初夏的傍晚了,谢檐喧背着夕阳离开,身后是一个青翠茂盛的歪脖子柳树。
来得晚的人大概不晓得。
那颗歪脖子柳树,二十年前就不再发芽了,直到今年。
隔天,谢檐喧就把这事给岑年说了。
岑年低头思索了一下,随后笑着离开。
谢檐喧拉着江停:“走,咱们也去看戏。”
一路尾随,看见岑年吃了个闭门羹,满脸郁色站在门口,十分嘴笨地解释。
街坊四邻难得看着城管大队队长出糗,一时间都不肯收摊。
何清梅在门口叫句:“楚榆啊,还是让你家岑队长进屋吧。”
一片笑声。
楚榆打开门,跺跺脚,恶狠狠瞪了他一眼,却没再关门。
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岑年冲何清梅讨好地笑笑,抬脚欲跟进去。
楚榆转身的时候,瞥见了谢檐喧,和她身边的人。
仿佛被按了暂停键,她盯着江停的脸,不可置信和惊恐来回交错。
无声地张张嘴。
“江先生……”(作品名:《风和日暖·蔻梢绿》,作者:迟非。来自:每天读点故事APP,看更多精彩)
点击屏幕右上【关注】按钮,第一时间向你推荐故事精彩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