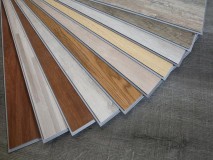随着电子媒介文化时代的到来,相关的讨论和研究也如火如荼。在众多乐观主义者为电子媒介促进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欢呼的时候,不少学者对电子媒介的发展产生忧思。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工业的潜在危险忧心忡忡,他担心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文化工业成为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

哈贝马斯则在《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中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化和舆论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它使得作为理性-批判论争私人场所的公共领域逐渐蜕变为一个文化消费的领域。哈氏发现,某些利益集团借助舆论管理技术将自己的主张和要求被合法化,而公众则被从公共讨论和决策过程中排除出去。同时,报纸内容走向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既是商业化的必然表现,也反过来成为商业促销的手段。这两点被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进一步强化,他提出电视媒介并没有促进民主和开放,反而通过各种机制在文化生产领域加深霸权和专制的危险。这种危险主要可以概括为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两点。

布尔迪厄是如何揭示这两个主题的呢?
一方面,电视在当代社会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而是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和工具性质。电视在当代社会中的符号暴力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首先,电视行业的职业眼光和内部循环使得电视节目内容同质化。“为了第一个看到或第一个让人看到某种东西,他们几乎准备采取任何一种手段,但是,为了抢先一步,先别人而行,或采取与别人不同的做法,他们在手段上又相互效仿,所以他们最终又做同一件事,那就是追求排他性,这在其他地方,在其他场可以产生独特性,但在这里却导致了千篇一律和平庸化。” 其次,电视上的呈现受制于强加的主题和制约的环境,需要经受来自记者和观众的审查,因此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表达。所以,电视只赋予某些“媒介常客”以特权,这些“快思手”则通过电视提供过滤的信息和预先形成的想法。再者,电视因其颇占优势的经济实力和符号表达力,进而对传统媒介构成一种暴力和压制,甚至影响到它们的生存。值得注意的是,“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

另一方面,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中的僭越使得电视从文化和交往的传播手段沦落为一种典型的商业操作行为。布尔迪厄回顾电视的发展趋向,总结道:五十年代的电视要的是文化品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利用自己的垄断给众人强加了有文化追求的产品,培养公众的品味;可九十年代的电视为了尽可能地招徕最广大的观众,竭力地迎合并利用公众的趣味,给群众提供一些粗俗的产品。而引发这个变化的关键就在于商业逻辑不断通过收视率来侵蚀电视、新闻场甚至整个文化生产场。
第一,电视在收视率这一杠杆的作用下走向非政治化或中立化。即使是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只要能够吸引观众,便被大肆报道。对现实事件的有意识地筛选和处理直接导致了信息的垄断和排斥,电视的文化品味和政治功能也在对耸人听闻新闻的追求中逐渐消解。第二,电视借助非凡的影像手段制造现实,控制受众对事件的理解,并达到指定的目标,从而引发强有力的煽动性和情绪效果。更重要的是,通过哈氏所说的“舆论管理技术”,电视可以反过来影响政治决策和司法程序等。因此,电视一边把一切事件都非政治化,但另一边又可以把非政治事件政治化,这种双重功能使得电视成为民主社会一个危险的符号暴力。那么,谁是话语的主体?电视到底代表谁的声音?事实上,电视人一方面揭露了某些社会的不公,同时又在为自己捞取象征资本和名望。第三,电视把他律的生产者引入独立自治的领域,科学知识和艺术创作在收视率的主导下受到商业逻辑的蚕食,进而危及科学和艺术的自律性。科学理论和艺术价值不能以公决的形式来裁判。但传媒与学人或艺术家的合谋,使得那些不被当作作家的作家,不被当作哲学家的哲学家等等,借助外部的力量,可以得到无法从他们的同行那儿得到的认可。
《关于电视》是上世纪末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公学院讲授的两堂电视公开教学课的内容,旨在揭示电视媒介的内在机制,并提出对此的担忧。纵使现在电视不在成为主流媒介,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发展也能在其中有所借鉴和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