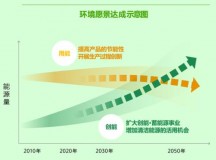它保留着旧时代的样子,与新时代的光鲜没有半点关联,你在全国的城中村都能找到这样的店——广州的石牌村,南京的峨嵋岭,徐州的事业巷——只是沙湾村更普通,更原始,没有高大而破旧的建筑,以及剧烈的拆迁冲突。
沙湾村有些年头了,几十栋两层或三层的宅子,横的斜的,外墙看得到泪痕般的雨渍和铁锈。粗大的电线缠在一起,时而在楼与楼间跨越,时而在电线杆上交织成乱麻。
附近唯一对外的出口,是条仅容两辆车并行的小路,越向外地势越低,最后在与八一路延长线交汇的地方,形成一个三四米高的梯形台子。站在上面,能看到中国地质大学前些年新修的侧门。


下午四时,学生三三两两地从校门出来,穿过马路,围着公交站聚成一片。这里没有地铁,公交是主要的出行方式。每当有车开来,人群隔着很远便开始躁动,像是被抬离水面的鱼群,剧烈地挣扎着,只等车门洞开的瞬间一股脑涌入。
人完全是被推上公交的,脚踩在地面、空中和其他人脚踝上没有区别,这在地铁通行后很少见了,有种上世纪九十年代挤蓝白巴士的感觉。
逆着人流的方向,高大爷拖着折叠车从公交上下来,晃晃悠悠地穿过马路,看一眼人群,再一点点挪回位于沙湾村163号的便民万能修理部,也是他的家。
高大爷八十多了,穿着身格子外套,休闲裤,布鞋,裤腿处露出浅灰色毛裤。他腿脚有些不利索,每走一步鞋底都会和地面用力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
上午九、十点出发去汉正街打货,回来时,大爷的折叠车上多了一个鼓鼓的黑色布袋,里面是零件和废旧钟表之类的东西。
一个年轻女人从门口迎了上去,“师傅!我放你这里,晚上过拿来好不好?”

她手中的塑料袋里躺着双黑色高跟鞋,跟底的灰尘又厚又硬,中间位置露出一点金属。
“好!好!”大爷低着头往里走,每走一步说一个字,用力地像是从肺里喘出来似的,带着沉重而嘶哑的鼻音。
“那我放这了,大爷!”女人抬高音量,把塑料袋放在门口的桌子上,“晚上!过来拿!”
“高跟鞋跟,”大爷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回过头,伸出左手一指,“五块钱。”

高大爷早年得过大病,去过几家医院都查不出病因,打针吃药不见好,最后才确诊为肺囊肿。手术后康复了,但听力受到永久性损伤,助听器效果一般,说话超过三个字便会含糊不清,所以家人通常通过写字和他交流。
老伴冯婆婆走到忙碌着的高大爷旁边,递了张写字板过去,上面写着:“你中午吃饭吗?”

为了做生意,老伴两人住在一楼,二楼是两个儿子,儿媳,还有孙子。
高大爷不耐烦地挥手,从里屋来回两趟,拿出铁脚,纸盒,铅笔盒,又从外间搬出小板凳,戴上黑框眼镜,开始忙活。
高跟鞋倒着套进铁脚,从废纸盒做的工具箱中翻出锥子和拔钉钳,一点点把鞋跟拧下来。高大爷的手很稳,但做这一步时有些吃力,脑门和手背上鼓起青筋。这令他的眉骨和高鼻子显得格外冷峻,再配上短而薄的颧骨、凹进去的脸颊,看着有种雕塑般的深沉感。


拔下鞋跟后,高大爷打开铅笔盒,从一堆鞋跟中选出匹配的,用锤子把它敲进鞋跟,502粘合后,锉刀用力搓几下,最后用电动打磨机磨平毛边。整个流程用时六、七分钟。
几个三十岁左右的人站在不远处,聊天时视线一直盯着高大爷。一对学生情侣从旁边路过,他们先注意到了电动打磨机,随后目光停留在门面,发出惊叹的低呼。


很少有人能第一次路过万能修理部而不产生好奇的,尤其在这个年代。
两扇涂了蓝漆的铁板构成大门,上面有防盗的尖刺。一里一外两张牌匾,分别写着“武汉市洪山區義雲便利超市”和“武汉市洪山区迪迪五金商店”,但门口黑板上的“便民万能修理部”才是最贴近现实的店名。
门口还有一个钉在水泥砖里的遮阳伞,两个陈旧的柜子,上面摆着、贴着或挂着各种货物——货物这个词在这里比商品贴切,它有种复古的、摆地摊的感觉,而商品更像是专柜中精致的陈列。


在万能修理店,你看不到主人推销货物的意图:抗战碟片、袜不湿、热水袋和两性用品的包装蒙着灰尘;吊带金属夹子上满是铁锈;玻璃板下的军事报纸,用大字体印着“南海局势再升级”——印象里是很早以前的新闻。
它看上去更像是高大爷在展示自己的生活态度。
“武汉市第一家最低价军事报出售,关心国家大事,国防强大是华夏儿女最大的福利”,又用红字强调,“半价出售”。这是高大爷最在乎、最骄傲的事,相似的布告他写了四份。


但昨天晚上,一块五一份的四开报纸被人拿了四份,没有“自觉投币”,高大爷很生气,用三种颜色的笔写了份声明,谴责偷报纸的人,又在一块木板的背面写,“这便宜报纸也偷,你说可不可耻?”放在柜子旁靠着,给路过的人看。




爱国是高大爷的大事。贴在门口、每年一换的手写对联,今年写着“听改革开放高歌继猛进,看两百年梦铸就大中华”,横批,“中国万岁”。
发财则是高大爷的小事。蓝色铁门上贴着“开门大发”,而铁门对面的白墙贴着“对我生财”。这算是风水学了。
“你看着像有客人吗,不赚钱。”冯婆婆坐在里间的躺椅上说。这是一个由椅子、纸板和竹席共同组成的躺椅,旁边是台缝纫机,正对面是一台插着天线的电视。


七十九岁的冯婆婆一头黑发,看着只有五十多,脸上一直挂着笑,热情,好客,让人完全想象不出她生气会是什么样子。她会赞美“老头子退休前是工程师,很聪明,什么都会修,不会的一晚上不睡觉也要想出来”,也会抱怨“老头子怎么劝都不听,儿子媳妇都不支持他修,修这个干嘛,又没人要,他耳朵不好,你说,就当听不到”。
但末了还是高兴,“之前地大一个小姑娘来和老头子写字写了好几天,来这拍片子呢。”
在冯婆婆心里,半工半读、技校出身的老头子是值得尊敬的,附近老人拉链、鞋、电饭煲等东西坏了过来修,他不收钱。当然也会有修不好的时候,外间摆放的黄纸和灯笼旁边,有十几个电饭煲的尸体,还有一架飞机玩具。

生意惨淡,婆婆觉得正常,“为什么不去磨山呢,来这做什么?”她觉得年轻人不会对沙湾村感兴趣,它是她的生活,但不是年轻人的。
从沙湾村再往东,八一路延长线走到尽头,向北拐入鲁磨路,是磨山和武汉植物园,过了湖是落雁岛,景色宜人,附近的村子里隐居着艺术家和乐手。

而沙湾村呢,东边靠湖的部分有人盖了茶馆,有人建起书院,有人意图做民宿,贴着马路有花卉市场,但到万能修理部这里,只有再往里的红砖婆婆烧烤,同样透着老气的东湖医院,还有下午便坐在外面打牌、仿佛身在成都的中年人。
但这些都和万能修理部无关了。
它保留着旧时代的样子,与新时代的光鲜没有半点关联,你在全国的城中村都能找到这样的店——广州的石牌村,南京的峨嵋岭,徐州的事业巷——只是沙湾村更普通,更原始,没有高大而破旧的建筑,以及剧烈的拆迁冲突。

曾有在沙湾村盖私房的人想转手,却找不到下家,因为“不知何时就要拆迁”。每隔几年就被翻出来问的沙湾村拆迁问题,之后都没有下文。

所以已经开了十四年的便民万能修理部,仍在提供着如今不太需要的旧服务,但它和旧时代,就像如今人对待损坏物品的态度一般,终将被抛弃。

万能修理部里屋积压的货物不知何时才能卖掉。柜子里的白酒、扑克、包包、CD、指甲刀、日光灯管、避孕套等大多落着黄褐色的灰尘。挂着各式钟表,圆的,方的,带响的,没响的,在手机变成人体器官的当下,也仅剩装饰意义。
大爷修好了高跟鞋,面色微红,高兴地笑着,“麻烦,六块钱。”

夜幕下的便民万能修理部
text | 王博璨
photo | SANTA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
END

喜欢今天的推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