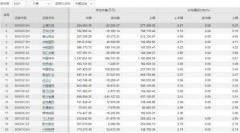谢其章

《受命》,止庵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320页,49.00元
读到止庵的长篇小说《受命》已经三个多月了,迟迟没写读后感。三个月来,看了大量关于《受命》的书评,及二十来篇报刊对止庵的采访之后,我感觉现在可以动笔了,而且验证了,没有抢在第一时间着急八火地写,真是做得对极了。
我的阅读史非常浅薄,小说阅读尤其是外国小说阅读,简直是只菜鸟。直说了吧,我的水平也就够读读十七年革命小说“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受命》的评论和采访,尤其是采访,透露了许多我很可能读不懂的小说情节和小说技巧。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具备写“书评”的资格。
思来想去,计上心头。《受命》的时代,《受命》的北京,我不是全程“人在现场”么,我不是有日记、有生活账薄么?不妨与《受命》来个“对照记”。
我读《受命》,想起了两段话和一部小说。
一段话是张爱玲说的:“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惘然记·前言》)
另一段话是黄裳说的:“从几十年前起,在北京这地方就一直有许多人在不断地‘怀旧’,遗老们怀念他们的‘故国’,军阀徒党怀念他们的‘大帅’……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中间很换了不少花样,但这与住在北京的普通老百姓的牵连则不大,比较复杂的是作为文化积累的种种事物。”(《琉璃厂》)
一部小说是王朔的《动物凶猛》。《受命》与《动物凶猛》有一点非常相似,除了故事“纯属虚构”,其余无一不真。我在北京生活了近七十年,我的家庭有过相似的经历,好像有点儿资格“鸡蛋里挑骨头”地验明真假吧。谈一个看法,如果说《动物凶猛》讲的是七十年代北京故事,基本同意;如果说《受命》讲的是八十年代北京故事,就事论事,错是不错,但是没有七六五十年代牵引着故事发展,《受命》似乎只不过是《动物凶猛》的翻版。
前几天在鼓楼剧场的文艺圈诗文朗诵活动上,史航朗诵了《受命》第31页到37页。我一直以为朗诵是拿腔作调的,故作深沉的,尤其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倘若是话剧,则另当别论(电影《哈姆雷特》第六十九分钟到七十二分钟劳伦斯·奥利弗那段话何其精辟)。谢谢史航,他这个“31-37”朗诵法给我作此文提供了一个简便的方法,下面的“对照记”(或曰“对读记”)即采用此法。
第10页。陆冰锋母亲用补发给丈夫的钱给三个孩子各买了一个大件,冰锋是手表,弟弟是自行车,小妹是缝纫机。——这三件再加上收音机,就是那个年代流行的“三转一响”四大件。所谓“四大件”的内容,到了八十年代更新为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音响录音机等等。“大件”也是那个时代的专用词。比如说买家具,大衣柜双人床五斗柜算“大件”,须凭家具票或结婚证购买,椅子凳子不属于“大件”,无须票证。“大件指标”和“小件指标”及“出国人员服务部”则是另一码事,等到193页时再说。
第11页。我家五十年代就有了缝纫机,肯定不是陆冰锋小妹使用的蝴蝶牌,五十年代的缝纫机上面有个木制的罩子。七十年代我学会了踏缝纫机,拿父亲的领带练手砸成鞋垫。那时并不是家家都趁缝纫机,老演员蓝马的外甥时不时来我家用用缝纫机。
第12页。陆冰锋母亲住在甘家口,陆冰锋不和母亲住一块,看望母亲后,陆冰锋乘102路到动物园,换乘107路回自己的小屋。——甘家口,我太熟了,生活于斯,凡四十年。动物园是许多路公交车的终始站,那里有我青少年的记忆,有些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第18页。冰锋寻仇来到崇文门某胡同,于疑似仇家大门口附近游荡,“路边,两个木匠正在打一件双人床之类的活,满地的刨花”。——七十年代初京城百姓开始自制家具改善生活,这股热潮据称是从“一根扁担”开始的。木料奇缺的年代,连个扶手沙发的扶手木料也成了难事,不知哪个聪明木匠率先想到了扁担,因材施教,一根扁担一锯两半,稍加打磨便是合格的扶手。我不属于心灵手巧之辈,但是打造过从凳子到高低柜到写字台到双人床等一应家具(当然,手艺跟阿城比不了)。双人床我设计为组合式的,可以放许多杂物。慢慢地街头巷尾出现了许多“打木工”者,戳个“打家具”的小牌子在路边揽活,市民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小木匠”。在楼房小区里揽到活的小木匠,做了一家等于在全楼区做了广告,一家接一家,干不完的活。百姓中的“木工热”和“小木匠潮”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消退,直至绝迹。1993年我在甘家口路边请了个小木匠,打了两个书柜,今天仍在使用,书柜样式也是我设计的,可见,手不巧,心还是有点灵的。
第23页。陆冰锋父亲平了反补了钱,母亲落实政策,一家子户口迁回北京,分了一套两间半的房子。乔迁之日,是这家人“有史以来最幸福的一天”。——幸福两字该加上引号,因为是用父亲的命换来的。新房子的家具大多是朋友送的,“一张桌子和四个凳子”,则是在信托商店买的。信托商店和“丢失物品招领处”均为那个时代的特殊行业,背后均有公安在站台,失物招领处更是写在明面上的。信托商店也许只对卖家格外警惕,担心东西来路不明,卖家须出示户口本。我与信托商店(西单中昌信托商店)仅打过一次交道,下乡插队回城后用不着的大头鞋卖给了他们,好像卖了几块钱。特殊年代,信托商店有那么几年“货满为患”,东西又多价钱又贱。我表哥没少逛也没少买,一组一大两小的真皮沙发才十几块钱。围了半圈的沙发缺个茶几,表哥知道我会一点儿木工,让我做一个。茶几好做,木料难寻,四条腿中的一条腿是两根细木条拼成的。现在易如反掌的事情,当年何其难也。
第30页。陆冰锋应父亲的老同事贺德全之邀,去贺家当面打探“父亲之死”。冰锋前次往贺府打电话直接询问:“想请教一下,祝部长,您知道他住在哪儿么?”——贺德全乃家里有资格安装电话的老干部,官场沉浮,反应机敏,这种事怎么能在电话里谈呢,遂邀冰锋到家里面谈。进门之后,“冰锋把装着六个国光苹果的网兜递给她(贺婶婶)”,国光苹果相当于现在的红富士苹果,是那个年代北京很畅销的平民水果。国光苹果酸中带点甜,个头有大有小,大也大不过最小的红富士,小的堪比鸡蛋,送人是拿不出手的。红香蕉苹果和黄香蕉苹果比国光苹果高一档次,送人有面子。冰锋送六个国光苹果略显寒酸,网兜眼大的话,说不定把苹果漏掉地上。
第41页。冰锋看着燕苹“中等身材,略显丰满,四六分锁骨发,圆脸,眼睛弯弯的,下巴稍尖,皮肤红润,确实像苹果,而且是红玉的”。——红玉亦如国光,是一种苹果的名字,口感近乎红黄香蕉苹果的又沙又面,老人小孩爱吃,因为咬着不费劲,比较适合给没长牙的孩子㧟着一小勺一小勺喂。
第51页。“冰锋带来了一个早花西瓜,现在在副食商场买水果可以自己挑选了,他用上了大学学过的叩诊功夫。”——早花西瓜是八十年代北京较为知名的一种西瓜,上市早,5月中旬就能吃到了。早花西瓜有个弱点,皮很脆,轻轻一碰就裂了,甚至四分五裂。裂口的西瓜只能马上处理,贱卖,不然很快就馊了,用现在的话叫“止损”。尝见西单某店卸西瓜的场景,颇似杂耍,从卡车上往下扔西瓜,接西瓜的售货员单手接住西瓜,随手稳稳放在栏内,观者叫好,扔西瓜的和接西瓜的则表演起来,越扔越快,越接越准,鲜有失误。这样有如篮球竞技的卸西瓜场面仅于西单此店见过。西瓜堆放在围栏里隔一段时间就得倒腾到另一空栏,为什么呢,因为早花西瓜皮薄皮脆,经不住久压。再来说说冰锋的挑西瓜“叩诊”法,此法对国营店来说尚可通融(还得碰上服务态度温和的售货员),个体瓜摊是不大会允许的。早花西瓜看似硕大坚实,其实与鸡蛋差不多脆弱。挑西瓜除了“叩诊”之外,还应学会“望诊”。最保险的方法是请售货员用尖刀挖个三角口,生熟立判。
第55页。诗歌小组准备一起骑车去西山赏红叶,冰锋抱歉地说,“我不会骑车”,另外三位都很惊讶。——那时的北京一个男青年不会骑自行车,虽说不是绝无仅有,也得说极其罕见了。我倒是早早学会了骑自行车,但是,列位别笑话呀,我只会骑,但是不会上下车,上下都得找一台阶或马路牙子。直到1973年在青海一条空旷无人的公路上,每天上下工骑自行车往返。突然,有一次我蹁腿下了车又蹁腿上了车,惊喜万分,赶紧蹁上蹁下好几次以巩固战果。
第62页。尽管这样的人往往声称“我只负我应负的那一份责任”。——1997年秋中国男足兵败金州痛失1998年法国世界杯出线权,球迷愤怒了,主教练戚务生回应时也说了这么一句:“我负我该负的责任!”呵呵,说得跟一场小刮小蹭的交通事故似的。
第71页。这是高干病房,楼道安静且干净,甚至连气味都与普通病房大不相同。——我曾经无数次地进出医院,近年来进出更加频繁,不是我得病了,陆续送走五位至亲,可谓看尽人情冷暖、尊卑贵贱。高干病房偶尔一瞥,有一幕很有印象,高干半坐半躺在床上,端举着报纸,好像在办公室而不是病房。
第91页。叶生约冰锋看罗马尼亚电影《神秘的黄玫瑰续集》,“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咱们在门口见面吧”。——北京电影院的名字具有时代印记,“工人俱乐部”即其一。另如“二七剧场”(见第93页)及“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剧场”“红星电影院”等等。我在按院胡同住的时候,“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离家不远。我在洪茂沟住的时候,三里河工人俱乐部离我家也很近。巧合的是,我与《受命》的男女主角在同一家电影院看同一部电影,我的日记上还有日期呢。读《受命》格外有亲切之感,就是因为里面无一臆造的细节。
第97页。他们想方设法找到几家内部书店,“去得更多的是西绒线胡同东口路北那家内部书店”。——《受命》说了好几家内部书店,我才知道“机关服务部”也算内部书店,这样的话,《受命》所说的那几家内部书店差不多我都去过。可是西绒线胡同这家与我亲,因为母亲工作了二十年的“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就在内部书店右首。发行所今只存大门洞,五十一年前母亲突发脑溢血,同事给抬到平板车上,最后一次经过大门洞。
第101页。他们去首都体育馆听了一场演唱会,多半是女歌手,叶生评价了刘欣、王兰、毛阿敏、田震、张菊霞、王虹如何如何。——红颜易老,红女歌手更易老,如今仅毛阿敏偶尔冒个泡。有那么几年混迹于首体周遭,多难搞的票都拿得到,见证过多少名场面。若论最令人血脉贲张的一场,当属阿兰·德龙大驾光临首体,出席歌星演唱会。主办者特地请来达式常和周里京两位当红男星迎驾,我在现场感觉:这不是以卵击石么?
第104页。他们还去逛北京新开张的几处夜市:东安门大街。地安门大街,西单路口东侧,还有西单服装商店门前。——我有很长时间在西单一带谋生,对西单一带非常熟悉,冰锋叶生游逛的几处夜市,尤以西单服装店门前的夜市我最熟悉。西单服装店的右首是西单菜市场,往西凹进去一大块,形成了一个小空场,正适宜办夜市而不影响交通。这个夜市以服装为大宗,一辆辆平板车挂满各式衣服,鳞次栉比,沸反盈天。当时有一个口号:“让西单亮起来!”夜市是一招,另一招是国营食品商店延长营业时间,西单路口东南角有一家“燎原日夜食品店”二十四小时营业,不在此列。林海音怀念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单牌楼,那时“燎原日夜食品店”是私企“和兰号”,听说公私之间的房屋产权纠纷闹了几十年,直到西单大变模样。
第109页。天已黑了,冰锋拉了一下灯绳,屋顶悬挂的日光灯却不亮。蹬着凳子去拧灯管上的憋火,还是不亮。他抱歉地说,憋火坏了,得换一个。——日光灯也叫管灯,七十年代才进入寻常百姓家,记得我家是七几年才用上的。管灯比灯泡亮,瓦数却并不比灯泡高,因此院子里各家算电费时曾经惹过疑惑和议论。公家六十年代就用上了管灯,上初一时我在教室里打闹,扔什么东西砸坏了一个管灯,老师说你要赔五块钱。五块钱,是一学期的学杂费呀。
第114页。冰锋到屋前自家搭的小厨房里做饭。现在流行一个义正辞严的词“私搭乱建”。——其实那个时期,房子够住的话,谁没事吃饱了撑的私搭乱建呀。尤其是煤气灶刚刚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七八十年代,那通宣传呀,煤气泄漏多危险呀,煤气罐会爆炸呀。健康和安全,兹事体大,住房面积有限,不得已才在窗外搭个小厨房。您以为我愿意搭呀,小厨房还挡亮呢,本来我住的就是西房,大白天也得开着灯。当然了,小厨房的正当理由后来被滥用了,变成了你盖我也盖、不盖白不盖的圈地行为。
第115页。不过得知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内部放映意大利电影回顾展,叶生托人买了两套票,都是晚场,晚饭又得在外面凑合了。——“内部电影”比“内部书店”更勾人心魄,七十年代我还在农村插队时就听说北京放内部电影《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呢,心里痒痒地羡慕。那个年代能搞到“内部电影”票,证明你路子野。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原来是给专业从事影业的人员放教学参考片之类的,慢慢地不那么严格了,非本专业的社会闲杂人员有票就让进了。曾经和情人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看过肖恩·康纳利主演的《玫瑰的名字》,一点儿也没看明白。《受命》此页提到的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我是去年才在电脑上看的,冰锋喜欢女主角莫尼卡·维蒂,而我是搜“理查德·哈理斯”,无意中看了这部色彩奇幻的电影。
第117页。他说得去关水管子了,不然明天早晨就冻了,还得烧开水浇开。这又引起了叶生的兴趣,非要问是怎么冻法,又是怎么浇法。——这是住过北方平房院子应该具有的生活常识,叶生这位部长千金“少见多怪”,不足为奇。吾妻非富贵人家,却一直住楼房,嫁给我这个平民(房)户后,对院子里一应生活设施很久不能适应,同样对寒冬院子当中的水管子浇开水感觉好奇。叶生所说的关水管子,实则是把水井里的水龙头给关了,然后把地上的水龙头打开,把水放干净,这样管子里没水冻,不坏管子,即使水龙头冻上了,开水一浇就能打开了。如果不按程序弄,那一壶开水可就不够了。三九天气酷寒之时,地上的水管子得包裹上厚厚的草帘子,水井里也得铺上草帘子。
第126页。整页都是祝部长给冰锋念花经。若不是叶生在一旁,若不是冰锋磨磨叽叽非得让仇家“死个明白”,这倒是个机会(之一),从后面一把推倒仇人不就结了,形式主义真耽误事。
第128页。叶生说,有两个阿姨,张姨在我家多年了,我就是她带大的,现在家务归她料理,还帮爸爸浇浇花。但她一直坚持老规矩,从来不和我们同桌吃饭。——祝部长真是人生大赢家呀,几十年风霜雨雪严相逼竟然毫发无损,连保姆(阿姨)竟亦不弃不离。保姆不与主人同桌吃饭,这倒没什么稀奇,行规也。不与主人同桌吃饭的行规,大户人家如此,小户人家也如此。俺家五六十年代的老保姆李奶奶就算白天家里全是小孩也不和小孩一桌吃饭。观念新潮的今天,行规还在。
第133页。他(铁锋)说,三里河新开了一家大型自选市场。——这里说的自选市场和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同在月坛南街上,名字应该叫“京华自选商场”(第一任经理是我邮友,他在猴票从八分钱涨到四毛五时就提醒过我),我虽然离自选商场住得很近,印象中没买过东西,太贵了。如今京华自选商场没有了,原位置是同和居饭庄等餐饮店。
第143页。铁锋说,这是寻呼机。——八十年代裤腰上别个寻呼机,比四十年代敌后武工队腰上别着二十响驳克枪还拉风呢。寻呼机也称BB机(抠机),分数字和汉显两种,我用得晚,1995年公司给配了一个汉显,两千块钱,现在用不着了也没扔,和1997年自己买的飞利浦手机一块搁抽屉里。有篇文章称某名流备两BB机,一个朋友抠一个蜜抠。
第171页。芸芸说,五月十日起副食调价,听说饭馆价钱涨得厉害。——查我日记:“十号开始,部分食品调价,人们纷纷涌上街头到处抢购,罐头卖了不少,平时下里巴人是吃不起它的。这只是个开头,各种食物将陆续涨价。每人发了七元五角补助费。”
第171页。路过电影书店时,他说,咱们进去看一眼。——电影书店在西四路口北,窄窄的门脸,却有个二楼。查我的购书帐:“1986年2月6日。今天其相在同和居办婚宴,我们三口到的最早,到西四书店逛,买了《书人·书事·书话》。电影书店新开张,顺便补齐了两本《世界电影小说集》》。”今西四新华书店还在,电影书店不在了,过于专门的书店长久不了。
第193页。他(徐老师)说,这儿还有个小件指标,送给你吧。我自己打算拿大件指标买个松下21遥,你想买什么,趁我提货时一块去。惠新东街四号,出国人员服务总公司营业部。——那年月的电器有个区别,原装和非原装。原装的需要美元和指标才能买,美元可以托关系兑换,而指标只有出国人员才能分配到。电视冰箱音响算大件,当时吾三口之家,冰箱电视洗衣机咸备,忽然追求起高雅来,花了四百美元(约合两千四百元人民币)求亲戚匀一个大件指标,买了日本先锋牌组合音响。买得起音响买不起唱片,也就听听收音机和磁带,始终没有高雅起来。
第194页。冰锋想,有了刀,还需要配套的家伙事儿。第二天下班回家,乘22路汽车到西四下车,在路南的绳麻商店买了一捆麻绳。——这家绳麻商店与街北的广济寺隔街相望,有一度我也经常光顾,买一种不甚粗的麻绳。我做过沙发,自家一个岳父母家一个都是三人沙发,单人沙发做过两个。麻绳是用来绑(固定)坐簧的。收废品的对自制沙发是看不上眼的,你只能倒贴钱请他们拉走,好腾地方。
第201页。对门的刘老太太走过来问,劳驾,这个月的水费,还是一个人吧?——那个时代,全院子或全楼门的水电费各家轮流着计算,水费是报人头,电费是报瓦数,到日子该你家算了,就得家家去敲门问数,这是一趟,算完了去敲门告知钱数,这是第二趟。第一趟碰锁的话,就按上月的人头瓦数算,第二趟碰锁的话,就先把钱垫上。事不大,就是琐碎麻烦,搞不好会影响邻里关系。
第232页。上面有“美国彩色宽银幕故事片第一滴血”字样。——查日记1985年9月16日周一:“单位组织在首都电影院看美国电影《第一滴血》,不错,就是太短了点。”佐罗、瓦尔特、高仓健之后,影响力最大的男明星要数史泰隆了。若论我看的遍数,《第一滴血》第一多,就在写到这儿的时候,又在电脑上看了一遍,片长一小时三十三分钟。结尾时兰博边哭边说:“在越南我负责上百万的装备,在这里我连停车的工作都找不到。”《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与《追捕》遍数差不多,阿兰·德龙人是帅极了,可是《佐罗》一遍足矣。值得留恋的是七八十年代的电影配音演员邱岳峰毕克乔榛们,听惯了上译厂的配音,换拨人配简直无法接受。现在倒是看惯了原声加字幕。
第253页。冬贮大白菜的销售点设在一个胡同口,场面就像一处战场,白菜码成一垛一垛的,有如一座座小山,售货员都穿着蓝布围裙……——在北京,很久以来漫长的冬季,大白菜是老百姓的“当家菜”。进入11月,有两周左右的时间,千家万户贮菜忙,几分钱一斤,买个二三十棵百十来斤,所费不多,一冬天一家子就没急着了。大白菜归副食店销售,但是忙不过来就得求助于兄弟单位。我曾经参与过在火车站卸大白菜,在街头巷尾装卸码垛大白菜,挨家挨户蹬平板车送大白菜,这么说吧,除了卖大白菜,其他活儿都干过了。这些活儿都是粗活,没啥技术含量,就一个字,累。11月的北京总要来几次寒流天气,大白菜怕冻,预报来寒流了,就赶紧给白菜盖大被子,这活是又急又累,刚喘口气,又来了一车白菜,还得赶紧卸车,经常干到半夜。大白菜怕冻也怕热(捂),热大发了烧心。寒流一过还得倒垛,怕把中间的白菜捂烧了心。一冻一化,白菜垛前可就和了泥,雨靴和单面胶手套比围裙更要紧。蹬着车送大白菜是件美差,我送的人家都是平房,热情点的还让进屋喝口水。再啰嗦一件趣事。有一次送大白菜,人家让进屋喝水,我却先拿起桌上的报纸翻看。不久有位同事对我说,你送大白菜的那家正是我女朋友家,她夸你真爱学习。
第293页。冰锋近乎敷衍地说,你真的是很乐观,说得跟人类的历史和现实拥有一种自愈能力似的。——冰锋是个本本分分的牙科医生,他不相信历史和现实及一颗蛀牙能够拥有自愈能力。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