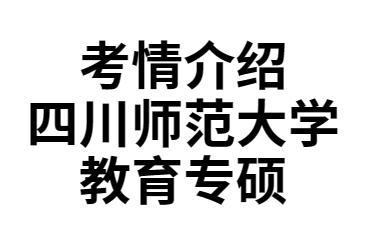当异化成为人们在畸形世界的无奈和宿命时,就会出现对异化的另一种反动。就像久病的人会形成对“病”的依赖甚至迷恋,在异化的大氛围里,有人会对异化充满跃跃欲试的期待,当然,大多数人的异化还是被动的。
在美国影片《人狼生死恋》(Wolf又译《妖之恋》)中,尼克尔森是个倒霉的出版社编辑,自己要被上司炒鱿鱼,老婆与年轻的同事背地里勾搭成奸,更不幸的是,他在一个大雪天被一头黑狼袭击咬伤,所谓“更不幸”当然是站在人的角度去看,这次被狼咬整个改变了他的人生,换句话说是把他的人生改写成人狼或干脆是狼生。
表现人的异化的影片很多,比如令人恶心的《苍蝇》等等。这类影片通常喜欢说明人是怎样由于异化而变成了与人为敌的魔鬼,基本上流于突出刺激功能的一般恐怖片。而《人狼生死恋》则不是通常的“异形”和恐怖电影,它有点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将同情的视点转向了变形者本人,是生命历险记,是一个普通人如何逐渐演变成另一个完全不同生命的非凡过程。它的恐怖之处不是异化者怎样害人,而是异化者不知道他将要怎样害人,尤其是他无法把握当他的本我脱离自己的时候,怎样不去伤害他爱的人。
一种人要变成另一种人需要很多主客观的因素,从本质上讲,人都不愿被迫改变自己,但如果可能又充满好奇地想尝试体验不同的自己,我相信这也是人的共性。影片中,当满腹学问的亚历博士请求正在变成人狼的尼克尔森咬自己一口,以使自己也能变成人狼时,异化的被迫便演变成对“异化”的好奇憧憬和追逐了。
亚历博士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因为疾病,更因为对红尘俗世的厌倦,反正是他认为时日不多,在残存的生命的最后时节,他想获得神秘恐怖的经历。他说,魔狼不是罪的,除非被咬的人本身罪恶。还说,并不是每个被狼咬的人都要变成狼,有人不被咬亦可能变成狼,只要他有狼的激情。亚历满嘴生命哲理,他的局限性是所有人的局限性,如果恋恋不舍于人生的滚滚红尘,如果不是到了风烛残年,他也许断不敢有体验做狼的恐怖欲望,但他毕竟有了超越的心愿,他要冲破人本的囹圄舍身去体验狼的生命,虽然没能实现。
我一直有一个愚见,生命即体验,完满的人生应该是半生为男半生为女,如上天假以时日,甚至再顺便过一些半男半女的生活,次序上可以颠倒,比例上可以再灵活。总之,人应该在极其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充分体验生命,通晓各个不同性别的妙处和局限。我以为这还不算什么,再进一步推想,人虽属于万物之灵长,但谁也无法证明人的生命感觉是最好的,何况所谓最好从来就是可疑和见仁见智的。我对人比畜生幸福的观点表示深刻的怀疑,人要诅咒某人常会说咒他来世变畜生,你怎么就肯定畜生要比人活得更糟糕呢?套用一句哲学语言就是:未成畜生安知畜生的喜忧?诗人食指曾写过一首《疯狗》,说甘愿做条疯狗好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疯狗要比人的生存更艰难,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这个结论也是属于人的臆断。我有时想,如果可能,人确实有必要变一变畜生,比如变成狮子、虎豹或者是尼克尔森似的人狼。
有风华绝代的美女蜜雪·菲佛相伴(在电影中她最后也变成了女狼人,遁入茫茫的黑夜中),甭说做个尼克尔森似的狼人,即使随便做个什么行尸走肉肯定也是其乐无穷。有权利而不感觉罪咎,有情爱而不存疑惑,做个狼不是很好吗!当然,标榜向往极端体验地做狼人,最终也还是从人的角度去思考,且难以摆脱人固有的红尘俗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