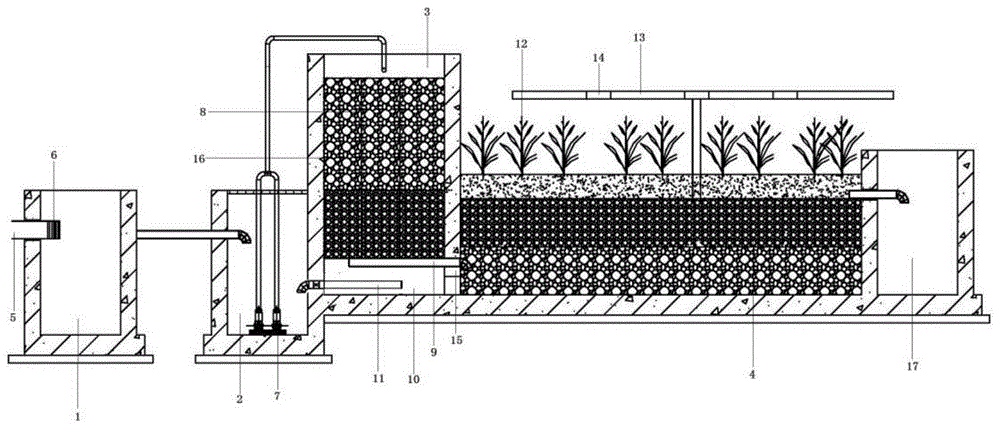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在《为了一种境遇剧》中提到:“如果认为人在一定的境遇中是自由的,他在这个境遇中,并且通过这个境遇选择自己,那么就应该在戏剧中表现一些简单的、人的境遇。”再透过萨特的哲学想象,不难发现,萨特的境遇不是一般的生活情景和人际关系,而是经过了人为精心设置的“地狱”,体现在《禁闭》对人心和环境的真实描述。
这么说来,其实萨特的“地狱”也是一个哲学现象。
大约从启蒙主义时代到19世纪西欧,许多思想家力图将上帝、天国、地狱等观念的“彼岸”性,回归到“此岸”。萨特的巧妙的戏剧安排更好地揭示“地狱就是他人”的主题——“地狱不是另外一个空间,不在彼岸,而在日常生活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地狱”空间无限大:墙外是走廊,走廊的尽头,是别的房间,别的走廊……从“地狱”的角度看,没有“彼岸”,全都是“地狱”。萨特的这种思想当然带着一定的残酷元素,房间里的主人公——人类没有出路,尽管可以“走出”房间,但却永远离开不了地狱。加尔散不经意打开了房门,却没有胆量离开,可见,“地狱”的魔力是无穷无尽的。
“房间”里没有刑具,没有一般人概念中的惩罚、煎熬。但是,却有永不熄灭的灯。萨特在强调对人类罪恶的煎熬惩罚,并不是尖头桩、烤人的炭火和紧身的铁衣,而是另外一种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惩罚、监视、永不停止的追问。而且更多的是自我的逼问,无法逃避的自残。怪诞的感情怪圈煎熬着三个灵魂,使他们不得安宁。他们在一起就像不断转动的木马,永远旋转着追逐,边追逐边相互伤害,相互成为对方欲望的陷阱和刽子手。直到最后加尔散痛不欲生地喊出了“他人就是地狱”的结论。这更是一个极限境遇的体验,是极端化的人类生存境遇的寓言,是对灵魂的一次集中猛烈的大撞击。
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孤独的,这就是说现实存在着巨大的不合理,人面对现实必然产生巨大的痛苦,这种荒谬性、孤独感和痛苦感严重阻碍了正常个体的“自由选择”。其实,“他人就是地狱”阐明了两种关系,一个是人类生活之间就是一种地狱关系。戏剧中三人始终处在争吵、追逐、勾心斗角、相互厮打的状态。萨特用这些动作象征整个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另外,“地狱”更来着于人内心世界对自己罪行的观照,这种观照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梦魇一般追逐着人不放开。剧中三人都在寻找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的镜子,他们需要镜子来削减自身存在的虚无感。
被禁闭在房间里的三个人物,他们搞不清楚是谁遣送他们进入“房间”的。与其说他们是“别人”送进来的,不如说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萨特认为每一个人的行为并不是别人或者环境迫使他做出的唯一结果。每一种境遇都存在着各种可能性。人以自己的观念、原则选择某种可能性,一个人一旦选择一种可能性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在这样的价值判断中,人因为自己的行为倍受煎熬,而他人的存在也正是自己存在的参照。这一点在杨昌龙先生的《萨特评传》中所说的:“如果你不能正确认识自己,那么,自己也就是自己的地狱。”
《禁闭》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提炼和载体,他进行了艺术上的渲染和夸张。在复杂的现实关系中,在无数多灾多难的心灵发展史中,人们确实是一方面相互需要,一方面又相互排斥;一方面相互热爱,一方面又相互伤害;一方面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另一方面经常进行决裂和斗争;一方面需要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信仰,另一方面也需要非常个性化的张扬。加尔散、伊内丝、艾丝黛尔是精神地狱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精神地狱的受害者。他们的灵魂互相纠缠着,继续在令人恐惧的罪孽中越陷越深而无法自拔。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面临上述各种排斥、伤害、压抑时,他人就是他的地狱;当一个人不顾周围的一切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志时,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时,他也可能成为他人的地狱。这是人类一个永远存在的不可思议的怪圈,一幅自我嘲弄的人生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