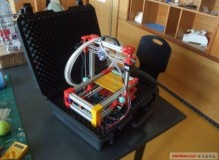其实,在与车前子的《苏州慢》相遇之前,我就已经在苦苦地寻找适合宿迁的叙述方式。或者说,在寻找打开宿迁的正确方式。
多年来,我一直在别人的故乡里闲逛,走马观花——王稼句的苏州,罗文华的扬州,薛冰的南京。还有沈嘉禄的上海,方方的武汉,阿成的哈尔滨,黄永玉的湘西,李娟的新疆。还有,虚构的文学故乡,如鲁镇,刘镇,木基市,香椿树街……
苏州,扬州,南京,那是江南丝竹。是凉月映水,花影在墙。是古琴,竹笛,琵琶的深旧,老屋的青灰,院子里一寸一寸的草木深深。那里的文字,笼罩着一股草木气,茶墨气,烟雨气,青石气。那调子是,从前的日色变得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上海,武汉,哈尔滨,那叙述的开头,是带着西洋乐器的,像民国老电影中那样的场景:洋车洋房,西装革履的现代人,一手文明棍,一手刀叉,在偌大的盘子上忙活着巴掌大的牛肉块。她们是潮流的,时髦的,但又是泛着旧的。湘西和新疆,究竟不同,那质地,就只是说话聊天,就只是听远山的回声,看水里的人影,人小于山,小于水,甚至小于草木,牲口。她们的世界很大,包涵着所有,但人排在最末。字里行间,尽是山水草木般的天然,纯净。
我确信我的宿迁不是丝竹,不是西洋乐器,不是天然的本真的人声回音。她是新的,流动的,少有起伏的。它是一步一步的推进,一点一点的积累,最后,终于大厦筑成,鞭炮齐响。比之乐器,有点像快板。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的这些年,宿迁给人的印象,就是袖子撸起来,露着干瘦的手腕,一脸精神地打着:当里个当,当里个当……向前进,向前进。我以为我找到属于宿迁的调子和气质。于是,我开始实地考察,走访,做笔记,在宿迁的大地上自我放逐。我执着于新式的建筑,城市的扩张,夜市的变迁,我开始把宿迁描绘成一个奔跑者,就像她在江苏地图上那样,脚步飞扬,双手张开,准备触线。我洋洋得意,兴奋于自己的发现和见解。我觉得只有我懂宿迁。
与车前子的苏州相遇之初,我的这种自我的状态,其实还没有产生多大变化。直到真正的阅读,尤其是临到尾声的时候,才有一些清醒。我那时,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怎样来评价这一个苏州?如何比较车前子的苏州与王稼句的苏州?事实上,我一直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以为王稼句的苏州,才是苏州。其他人的都不是苏州。但这一次,我分明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苏州。这个额宽、颧突、嘴平、须短、颈长,着一身浅色粗布盘扣衫的人,仰着头,侧着脸,看着我,让我一惊。这个人先是写诗的,诗写成了,才由诗入随笔。诗,是他随笔的底色。诗与随笔,都是码字,却又是文字中的两座不一样的山头。一些人用尽一生,才勉强翻越一座大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忙了一辈子,才觉得文字通畅了,有远意了。于是放下身子,口吐莲花,立地成佛。但,这个人却翻越了两座山,看够了两座山的风景。他的视线更宽广,写得更得心应手。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我喜欢这个苏州。这个苏州也是苏州。这个苏州,更有韵致。从此我也知道了,苏州不是某个人的,就像宿迁不只是我的——我寻找的故乡叙述方式,它仍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它需要不断的肯定,不断的否定,不容偷懒,不许自满。
《苏州慢》是第一个让我明白,打开故乡,或许没有最正确的方式的一本书。让我想到,叙述是有局限的,但局限里,也有不一样的精彩。就像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样。作为作者,我只能提供一个打开故乡的视角,让外乡人或是家乡人,跟随我的视角参观游览。(姚大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