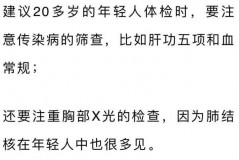那天晚饭刚过,突然电话响起 ,我顺手接听,里面传来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朱大夫,我们到了县医院了,该去哪就诊呀?”我猛然想起,今天下午省医院的高大夫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说他们那儿有一个病号,急需颈椎手术,但病号家庭条件特差,所以想回县医院来手术,主刀医生约定的是王主任。我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在我们骨科,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而且预约的是王主任。这可是实力派专家,已来我县医院做大型手术多次了。每次都是稳操胜券,我对这事儿信心满满。于是,马上告诉了病号该怎么过去,并且交代了值班医生小张大夫。
第二天上班儿,我像往常一样走进了骨科病房区。小张大夫对我说:“这个病号,还是你来接吧。”我挺不解,但想病号是我同意转过来的,我接就我接。于是,小张大夫便把我引到了最东边的大病房,只见小张招呼了一声:“你过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便站起来 很快的走到了近前,小张冲他说了句:“这是朱大夫。”这个女人便一扭脸儿和我的目光瞬间相遇,只见她吱唔了一声:“哦,行。”小张说:“以后你就找他吧。”“找谁都行。”她倒是挺爽快地应承着,我和小张便同时转身出来了。
等了一会儿,我查完房后,便叫这个女子把以前的片子拿了过来。谁知她居然抱来了一大摞的片子,分别是x光片,CT,核磁,足足有三十多张。原来,一了解,才知道他是从二院到三院,辗转了和平医院。又到了省医院,几经周折,才回到了县医院。我不禁愕然,天呐,这么复杂,这么曲折,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号啊?眼前的这个家伙,该不会是个偏执狂吧?我心里想着,不免惊讶。从那一大堆的片子中,可以肯定,这个病号是严重的颈椎压迫,急需手术。他们已经预约了王主任,看来手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接着,我便去了病床前看了看病号。那是一个七十多岁又干又瘦的老人,两眼凹陷,腮帮下塌,饱经风霜的脸上已经被病痛折磨得十分憔悴了。他瘫软地躺在床上,还下着尿管儿。令我不解的是,他们连夜从省医院过来,怎么只有一人陪护?看这情形来的不易,他们是经历了怎样的行程啊?
经过询问,原来病床上的老人,只有一个独生女,就是站在床边的那个刚见过的女子。她现在守在病号身边,向我讲述病号的病程及病情,很是详细,很是耐心。可见,他对老父亲的感情笃深。
就这样,这个一看就知道病的很严重的病号,无可拒绝的被我接手了。几天后,术前准备工作开始了,检查化验后,依手术医生的嘱咐,我和科室主任又对病号进行了颈椎枕位测量,以便手术顺利。这一切的术前前奏结束后,我把病号女儿叫到了医生办公室签字,她在署名处签下了“于佳”两字,原来她叫于佳。谁知她问了一句:“还需要输血吗?”我马上拿出了输血单子,她嘟囔着:“实在不行,用我的血……,不行,他是o型,我是ab……”“啊?”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心想这怎么可能?但嘴里还是“哦”一声,顺手收起了单子。她的脸上略显尴尬,有点儿生涩的转身出门了。我顿时感到这个女子好像坐在云里雾里似的,她给了我一种无可名状的朦胧感,我懵迟迟地坐在办公桌前,心想他们的血型居然……,她该不会不是……,可这么辛苦的大费周章的辗转医院,又是为什么?不可思议呀!
接下来我真的感到有点儿惶恐不安了。原来病号年纪过大,极度耳聋,基本上听力丧失,患有糖尿病,还有脑梗。吃的药比饭都多,小便靠尿管儿,大便因压迫无法自行排出,竟然要他的女儿亲自下手去掏。远远瞧着就感到挺腻歪的。这样的病号,也太棘手了。但想想有王主任出马主刀,应该可以胜任得了吧。
熬了几天后,病号如约进行了手术。一向严谨的王主任,在病号上手术台前,还询问了病号以前的伤口愈合的情况,确定万无一失后,才进行手术。
叫我意外的是,根据病号特殊的情况,在手术中用了枕物支撑颈部,这还是我行医多年第一次见到的情形。但手术进行的还算顺利。四个多小时后,病号从麻醉中渐渐苏醒,且有了意识。谁料这个病号的术后反应过大,情绪极不稳定,整天没日没夜的喊叫,折腾,摔东西,没有一刻安生。把他的闺女和女婿都折磨的够劲儿。
我每天查房都不见起色。病号两腿挺直,不能动弹,连翻身都不行。腰部两侧都磨出了大血泡,下半身皮肤溃烂,肛门处红肿,看上去挺吓人的。女婿买来了气垫子,我连忙跑过去打开,不由分说的鼓起了腮帮子,就给吹了起来。于佳顿时看着我,目瞪口呆,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你怎么给我们吹?”唉,作为医生,我又何尝不盼着病人早点儿好起来吗?我的心情和你们家属心情是一样的急迫的呀。
那天早上,我刚上电梯。身后传来了幽弱的声音。“才上班啊。”我扭头一看,于佳头发披散,眼睛布满血丝。“昨晚又闹腾了一宿。”我“哦”的一声,看来病号病情更严重了,我意识到这回我遇上缠手的难题了。可低头一想,我这一生行医总不能连几个重病号也遇不到吧?总会有挑战型的病例吧。
就这样,我坚持着给病号查询,观察,治疗。看得出来,于佳和她丈夫都在日日夜夜的悉心照顾,积极配合治疗。那天,我查房意外的发现 于佳不在。她丈夫说,她去省医院办出院报销的事儿了。到这会儿我才知道,病号在石家庄的住院,辗转,以及赶回县医院的全程,主要都是于佳一人操持。原来那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居然是送送他们回来的司机,而不是她丈夫。太令我震惊了!
还没等她来,省院的王主任却打来了电话,原来于佳向王主任描述了术后的病情及反应。这也是王主任所始料未及的。他在电话中交代,拍一个核磁片,看一下神经传导的信号如何。我马上叫于佳丈夫带病号去做了核磁。可病号极为不配合,情绪激奋拼命反抗,核磁没有做完便败下阵来。没办法,我把不成功的核磁结果发给了王主任,片刻,王主任的回答是:“赶紧通知病号准备一下,准备二次手术,我下午就过去。”听起来声音急促,有点儿慌乱。向来镇定自若的王主任,这回好像也乱了方寸。我赶紧开了术前准备药物,并交代于佳丈夫准备二次手术。
时近中午,于佳背着包回来了。我把她叫到办公室,转达了王主任的意思。她立刻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她,一副无法置信的模样。“看不见信号?二次手术?取胯骨替代支撑体?”我如实回答了她那几乎处于崩溃边缘的所有疑问。“老人能承受?”我沉默以对,递给她我手中的手机。“你自己问王主任吧。”她抓过手机,侧耳对王主任大声质问“怎么会这样?我们不想二次手术。”“那这次手术危险会不会更大?”“再探寻一次吧……”对面的王主任也在极力解释。“二次手术我们不做!”于佳丈夫跑过来大声反对,电话终于挂断。此刻的于佳像被电击过一样,软弱无力拉过一把椅子,蹲在地上,脑袋垂在椅面上,两手支撑着太阳穴,用力扎着头 ,露出一副愁苦入骨的样子。我坐在她背后,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安慰她,也不知该有什么样的举动,只能让她一个人静静的冷却一下。果然有十几分钟功夫,她猛地站起来,一脸坚定,迈开双腿,飞快地跑了。我真替他感到发急,毕竟这事儿放在谁身上也不好接受,何况只有她一人在肩挑重任,怎能轻易承担呀?我正踌躇着,突然,电话又响了“刚才我又看了一下手机中的片子,发现还是有信号的,虽然很微弱,但也应该不会是全瘫的迹象,先不考虑再手术了,观察一下再说吧。”我一听,赶紧把于佳叫到了值班室,她听着我和王主任的对话,张嘴欲言却被我的眼神和手势劝止,电话挂断,我告诉她虚惊一场,于佳终于如释重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术后治疗还在继续,每天仍在按部就班的查房,下药,观察病情。于佳和她丈夫伺候着这个病情加重,且情绪不稳,而且听力,智力都几乎丧失的病号,看得出来,他们都累得精疲力尽了。我不值夜班儿也知道他们是一宿的看护照料,夜不能寐。俩人憔悴萎靡的的面容告诉我一夜的疲倦。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能替一下班儿呢?我暗自感慨,同时又庆幸我有姐弟五人,我的老人在生病时,我因手足众多,分解,减轻了我许多负担。而于佳呢,孤立无援,我心中隐隐的升起了一丝恻隐之意,有意无意中总给她一些照顾和帮助。有一次,我随手丢给她几只手套,她便稀罕无比。,开心异常。这个于佳呀,天真的像个孩子一样。是很容易被满足,被感动的。
那天我在护士站办公,忽然听见最东头的大病房,传来一阵喧哗,吵闹。而且声音越吵越凶,整个走廊都被震撼了,有不少人都争相围观。我赶紧跑过去,原来,是于佳和她丈夫正在争吵“我爹看病花钱了,你不高兴。那你家人看病花钱,你怎么不说?”“我们拖累你了,你嫌我们累赘了?”“这要是你亲爹,你会说这样的话吗?你会侮辱你亲爹吗?”“我怎么了?我说什么啦?。”“我又干什么啦?你喊叫什么?”“好像只有你自己有理 ,我就没有付出吗?我懒得管你们。”“走吧,别来了,不用你,有本事别再来了,滚蛋吧!”在我面前一向挺斯文的于佳,居然还有这么泼辣的一面。我想过去劝说,可又觉得身份不太适宜,不好插手,只能躲在一边听之任之。看来为了给老人看病,于佳不惜和丈夫反目。大庭广众之下,两人争执不休。 于佳的咆哮愈演愈烈,声波一浪盖过一浪。把她丈夫击得连连后退。最后,同室的室友拉住了她想要离开的丈夫。过了一会儿,两人都默不作声了。于佳两口子的口角之争,终于偃旗息鼓了。
这个女子呀,在对待老人行孝上真的是不遗余力。,不带半点含糊的。我行医多年,什么样的病号都见过,什么样的病号家属也接触过。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抛弃良知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了。但像于佳这样尽孝到这种份儿上的,还真不多见。我心里默默地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也许是同情,也许是怜悯,也许是感动,也许是赞许,总之,我也说不太清楚,这或许就是作为医者的仁心所致吧。但无论如何,作为医生,我在病号面前,只能以医者的姿态行事,履行着一个医生的职责,尽心竭力的给病号提供最优质的贴切周到的服务。
谁知,在接下来的一次换药过程中,我打开纱布,意外地发现了伤口处有不少的渗出液,我顿感诧异 ,立刻和于佳一起,给病号做了颈部b超检查, 发现液体已经渗到皮下骨了,确定伤口感染了!这下可糟了。我一下子没有了头绪,于佳和她丈夫推着病号回病房了。我略一思忖,心想还是让他们回省医院吧,这种情况我根本没有处理过,现在就走,还能来得及办理出院结账手续,不至于耽误了病情,我询问好了财务,就这样吧,这也许是最好的方法了。我顾不上乘电梯,直接爬上了十楼,汗流浃背地对于佳说了我的建议。可于佳及丈夫却不同意,他们要王主任亲自回县医院处理。我立刻给王主任打电话,可他在百忙中,哪能一下子到位?我感到了迷茫,无助。于佳此刻则急得坐在椅子上,嚎啕大哭,逼问我为什么得么王主任上次立刻能来 ,这次就来不了了。我无言以对,给病号换完药,就走开了。
回到了值班室,我思前想后。从一开始莫名其妙地接受这个病号到现在的无计可施。我好像经历了一场梦魇。鬼使神差般的走到了这步田地,弄得无可收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当然我这一生行医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路轻松,这种情形也是在所难免的。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感到了前所未有有的焦虑和恐惧。坐在床上,我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待了一会儿,我终于冷静下来。唉,按科里的规矩办,走一步看一步,尽人事听天命吧。
很快,我把病号的情形汇报给了我科主任。主任的意见是赶紧做必要的处理,也就是清创手术。但病号高龄,体弱,且第一次手术刚做了七八天。再说这种情形,我们科也没经验。所以还是建议回省院。可于佳及其余家属强烈反对。这次体现的是于佳整个的家族力量。几乎所有的亲属都表示必须在县医院做二手术,坚决不走。态度很强硬。其实,换一下立场想一下,毕竟手术一开始就是在本院进行的,人家不走也是情理之中。无奈之下 ,我和主任经过协商,决定还是请王主任尽快回来做二次手术。这次王主任很快便答复了,二次手术指日可待了。
这次手术,较上次手术,难度会更高,风险会更大,对病号的体质和承受力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考验。而且谁也无法保证,经历这次手术,病号会安然无恙,伤口感染会被彻底清除,做了这样的清理,病号是否一定会痊愈。这些都只是待定的。我把所有能设想到的后果都毫无保留的向于佳交代了清楚。就等她大权在握下最后的定夺了。叫我感到意外的是,于佳却很踌躇,有些顾虑。看上去她应该有某种难言的苦衷吧。果然,他的亲属都纷纷离开病房聚在了一起,窃窃私语。“万一不测她怕落抱怨?怕担责任?”“到时候不好交代?”我穿梭在走廊中,无意听到这样的话,看来于佳的犹豫,只是对手术结局的担忧和慎重。她身上还背负着无法言说的苦楚与无奈呀。在她这个看似简单的家庭情况下,真不知她还隐藏着什么样的不为人知的家庭矛盾和秘密,太让人费解了。
一番研讨之后,只见几个长辈向于佳凑过去。好像对她承诺了些什么,于佳立刻果断拍板儿了。
紧接着,王主任带来了麻醉师,二次手术马上进行。可就在手术窗口签字时, 又有一道难题摆在了于佳面前。原来,省医院的麻醉师观察了一下县医院手术室的抢救设备,发现不是很完善。如果全麻的话,一旦出现什么情况抢救设施怕不给力。所以建议病号回省医院进行全麻手术。但是病号的病情,已经迫在眉睫了,于佳的全体家属都表示反对。一时之间,手术窗口前的场面出现了僵局。病号躺在手术室前却不能前行一步。无奈之下,手术医生和我科主任再次协商,决定施以局麻。但不能保证清理干净。
我站在窗口,只见于佳及所有的亲属都在交头接耳。商量讨论。“局麻可行吗?不会是敷衍吧。”“人家不給施全麻就局麻吧。要不就做不成手术了”“那可怎么办呀?”“局麻会清理干净吗?”眼前的于佳急的是抓耳挠腮,没有任何主意,过了一会儿只见其中的一个长辈突然疾言厉色大声喊道:“于佳,你签字啊!”那表情可以说是风云突变,横眉立目,一脸的秋霜。我看在眼里,真不知道这究竟是建议 ,还是命令,还是斥责。于佳回过头,瞥了他一眼。居然没有说话,然后又愤然地转过身去,对着楼梯口若有所思。看来她的家庭矛盾的确是不为外人所知哓,我目睹这一幕真不知所措。急得大喊了一声:“于佳你过来。”只见于佳立刻跑到我眼前,我对她说:“你考虑清楚,赶紧拿主意吧。病号等不及了。”她顺从地“嗯”了一声,回头对丈夫嘟囔了几句 ,便迅速地走到了窗口 对我说:“朱大夫,你能保证不敷衍我们,好好清理吗?”“我保证,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尽最大的努力,清理干净。”我急切地回答。她说:“行,我听你的,我同意了。”我赶紧转身跑过去通知手术室,病号终于再次被推进了手术室。
到了手术台上,我低头对着迷糊状态的病号大声嘱咐道:“我们再给你清理一下伤口,你别乱动。”他很听话的点点头,仰起了脖子。我们小心翼翼的打开纱布,病号睁着眼睛竟然无所畏惧的看着我们,还挺配合,没有过激的行为,没有反抗。我负责拉钩,王主任 又一次亲自上台手术。凭我的直觉王主任依然是是有条不紊 ,双手熟练有度。一个多小时后,手术完成。病号被推了出来。等候在外面的于佳赶紧迎了过去,王主任对于佳说:“用了大量的消炎药,把能清理的地方,全部都清理了。你们要严格控制好血糖。”于佳听了以后连连点头。
一切都回归原位之后,我把于佳叫到了办公室。向他坦言了那天我闻听了他们夫妻的口舌大战。于佳顿时眼睛往上一翻,同时左眼角往下一耷拉,左边的嘴角往上一挑 ,现出一副很窘的样子。看来她的另一面。也是不愿意暴露的,最起码不愿让我看到。我隐隐约约向她传递了可能有不好结果的预测,她好像也听懂了我的言外之意 ,低头沉默不语了。
二次手术我们在伤口处下了引流管儿 ,术后日夜不停的输上了抗生素,并且一日四次的严密监视血糖变化。于佳和她丈夫又开始了不眠不休的日夜护理和照顾。为了病号的周全考虑,我推掉了所有的新病号,一门心思的专治这个让科里所有医生都感到眩晕的病号。我和于佳都全力以赴的治疗和照料着,都盼望着病号早日脱险,早日康复。于佳守在病床前每日喂饭,喂药,擦洗,剪指甲,侍弄大小便,看管输液。有的时候累得在输液瓶底下打盹儿,我感到了一种无奈的孤独与苦楚,这种场景 ,即便铁石心肠的人见了都不忍心打扰 ,都会为之动容。
那次病号因躺在床上 时间太久体位下滑至床尾,于佳赶紧跑过去探过身子,病号习惯性的双手一楼闺女的肩胛骨,于佳便托住病号的颈部。顺势 往前一挪,把病人又重新拖到枕头上。这种情况,我已经告诫她好几次了,托颈部时候,要连带肩部一起带动用力再去往前拖。否则对刚做的颈椎不利。很显然,她一着急,把我的话便抛之脑后。我歪头对她微笑着嗔怪,她立刻恍然大悟,不好意思地冲我莞尔一笑——又忘啦。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谢天谢地,病号的病情已日渐稳定,情绪也趋于平静 ,意识也慢慢恢复,精神头也有了,脸颊也慢慢泛起了红晕。甚至身上的皮包骨也渐渐有些肉了。 最主要的是引流管儿。慢慢的往外拱了,可以一点点儿往外拔了,这一切都证明伤口在慢慢的愈合了!主任的巡视查房也表示非常的满意。护士长也在高兴的替于佳欢呼。这五十多天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都看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于佳从刚开始时的愁眉苦脸,愁眉不展,到现在渐渐的喜上眉梢,喜形于色可以说是老天保佑有了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的心里也慢慢的敞亮了,舒服了。这是作为一个医生最希望看到的结果。看来,亲情是无可战胜的,真心有的时候,是不会被辜负的。我的每一份付出,也在这个病号身上都得到了相应的回馈。我不再彷徨,不再后悔,而是有点儿庆幸,庆幸巨大的困难和考验的背后,所收获的经历与欣喜。
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治疗后, 病号的病情基本痊愈,可以考虑出院了。但在最后一天的查房中,我发现于佳一脸沮丧 情緖很低落,我又看了看床上的病号,一如既往的躺在病床上,没有任何异常,于是我很好奇的把于佳叫了一边询问,可她只是扎着脑袋摇头,什么也不肯说。俨然一副云山雾罩的样子,算了,还是让她保留几分吧。我心中暗想。其实我倒有点儿欣赏这份神秘感了。
我向于佳传达了出院的通知,她立刻喜出望外,收拾好所有的东西,便顺利办完了出院手续。就这样,于佳带着她的老父亲,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踏了回家的旅途。我目送他们渐行渐远,告别了这哭着进来,笑着出去的病号 ,结束了我行医史上的又一大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