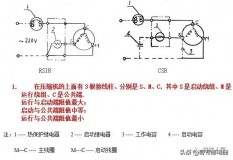乾隆四十二年年初的一天,江西新昌县衙的大门前出现一位”不速之客“,此人中年模样,满脸横肉、面相恶俗,腋下挟着一本厚厚的大书,扬言有一桩大案要告。
新昌县令升堂后,目光向堂下一扫,立刻认出告状之人乃新昌有名的泼皮无赖,王泷南。
新昌县令颇有些厌烦地问道,你要状告何人?
王泷南说,小人要状告乡里举人,王锡侯。
新昌县令哼笑一声说,本县知道你和王锡侯积有宿怨,若要诬告,你是要反坐的。
王泷南听了,扬起手中的大书说,小人不敢,这是一桩大案,请大人过目。
说着,王泷南将手中的大书呈了上去。
新昌县令接过一看,王泷南所呈的大书原来是王锡侯编纂的一本字典,《字贯》。
新昌县令粗略地翻看了两页,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于是不耐烦地说,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字典,何来的大案?
王泷南跪行几步,上前指着这本字典的序说,王锡侯犯有狂妄悖逆的大罪,他在序言中说,《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字遗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掩卷而仍茫然。《康熙字典》乃圣祖康熙皇帝御制,王锡侯为了标榜自己编纂的字典有查字之便,竟敢指斥圣祖皇帝所编字典有种种缺憾,这不是大逆之罪,是什么?
新昌县令听罢,再一细看这本《字贯》,王锡侯不过是把一个字的同义字或者近义字排在了一起,这纯粹是为了方便查找,也是一件好事。至于序言中提到的《康熙字典》有查字不便的缺点,这只是指出了字典编排上的一个小问题,如果非要上纲上线,硬给王锡侯扣上一顶”狂妄悖逆“的大帽子,未免有些小题大做,鸡蛋里非挑骨头。
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新昌县令本想斥退地痞无赖王泷南,但想到事关文字的官司在乾隆朝一向敏感,为了不出差错,保全乌纱,新昌县令最终踢了一脚皮球,当堂表示,此案将呈报巡抚衙门,一切由巡抚大人裁定。

江西巡抚海成看到新昌县令呈报上来的卷宗,觉得此事小如芝麻,根本不值一提,王泷南状告王锡侯,完全就是无事生非,蓄意找茬。
然而,在乾隆朝,无论官居几品,凡是事关文字,都有一套官场心得,心里越是明白,手上越要宁重勿轻,因为当今皇上阴晴不定,太难伺候。
就这样,江西巡抚海成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在奏折中,海成说,新昌举人王锡侯编纂《字贯》,虽无”悖逆“之实,确有”狂妄“之语,为显示朝廷威严,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头衔,妥否,请皇上批示。
从官场经验上看,海成此奏,既小心谨慎,又公正严厉,乾隆看了,应该挑不出毛病。
可结果呢?
这一道滴水不漏的奏折递上去,竟差点要了海成的性命。
何以至此呢?
实在是因为乾隆的帝王眼光太阴毒。
接到海成的奏折,乾隆先看了看王锡侯为《字贯》写的序言,感觉海成所奏大体说得过去。但是,乾隆并没有因此将王锡侯所编的字典放下,而是带着极为严苛的目光,仔细查看了这本字典。
这一查看不得了。
乾隆发现,在《字贯》的第十页居然连续出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名字。仔细一看,原来是王锡侯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避讳“,特意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名字”玄烨“、”胤祯“、”弘历“写了出来,王锡侯提醒读者,写文章时凡是遇到这六个字,一定不能写全,要么要少写一个笔划,要么改用其他字。
平心而论,有一说一,王锡侯在此处丝毫没有悖逆之心,有的只是读书人的责任心,仁善之心。
可是乾隆却勃然不怒,一口咬定,此人名义上在提醒别人,实际上却借此明知故犯,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
骂出此番要杀人的话,乾隆还觉得不够,跟着又把矛头对准了江西巡抚海成。乾隆在批复中痛骂海成,说《字贯》中”大逆“开卷即见,你居然说”无悖逆之词“,你就是这样审事,效忠朝廷的吗?你这个奴才,简直”双眼无珠“、”天良尽昧“。
骂完海成,乾隆颁下酷令,将逆犯王锡侯迅速押解进京,交刑部严审。

一件原本是泼皮无赖蓄意陷害乡间良人的恶毒之事,到了乾隆这里,转眼之间就成了古今未有的特大逆案?
中年乾隆这是怎么了?
何至于丧心病狂、暴虐昏庸到如此地步呢?
要回答这一切,还要从乾隆刻意营造维系的所谓”乾隆盛世“说起——
自乾隆二十四年起,得益于康雍两朝的积累,大清在乾隆治下进入所谓的巅峰盛世。对此时的乾隆而言,历史上所有威胁皇权的传统势力都让他清除干净了,他也有了旷世明君的优越感。但是,作为一个极度恋权,又极度敏感的满人帝王,他又有着难以驱除的自卑与警惕心理,大清虽然已经建立一百多年了,可他还是担心民间暗藏着反清复明的思想和力量。在他看来,这是乾隆盛世最致命的隐患,是横在他面前最危险的无形之敌。
很长一段时间,乾隆最阴沉的帝王心机都沉在此处,那就是如何才能彻底铲除这个无形而致命的隐患。
在帝王的御座上,乾隆对自己的”雄才大略“是相当自信的。的确,乾隆的帝王大手有一种可怕的魔力,他能够将浮华虚荣、沽名钓誉、血腥残暴,巧妙地隐藏在他的宏图大业,古今未有的”帝王圣明“之中。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乾隆祭出的就是这样一双表面伟大实际黑暗的帝王大手。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下旨,为了大兴文治,他立意修撰一部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此书将囊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成果。
此举的伟大显而易见,那么何以说实际上它又是黑暗的呢?
乾隆宣布,为了修撰《四库全书》,朝廷有必要将天下的古籍全都收集起来。为此,乾隆专门派人到全国各省,重金悬赏,大肆搜集民间藏书。为了防止百姓怕”犯忌讳“而不敢献书,乾隆特意颁布谕旨说:”文人著书立说,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段谕旨的意思说,民间文人学士写书,讲究的是兼收并蓄,岂能要求字字正确。文字即使有些许违碍之处,也不要紧,大家不要害怕,畏首畏尾,大胆拿出来,献给朝廷,我是不会怪罪你们的。
看到这份谕旨,民间百姓深知乾隆老儿得罪不起,该配合的地方还得配合,但配合的同时,民间百姓更知道乾隆在这道谕旨中表现出来的宽厚当不得真,他之所以这么说,为的是”引蛇出洞”,因此,民间百姓在“积极”献书之外,纷纷留了一手。
一年后,乾隆查看搜书成果。
有关方面报告,圣旨一下,一年多的时间,全国各地一共向皇上献出一万三千五百部藏书,搜书成果十分显著。乾隆听了很高兴,可是再一仔细查看这一万三千五百部献书,乾隆脸上的笑意立马就凝固了,嘴里更是骂出了刁民二字。
骂完民间百姓,乾隆没有罢休,跟着下旨指责各地官员说:“各省进到遗书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pou)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乾隆话说得很直接,难道你们不知道全国搜书的目的是什么吗?现在好了,你们弄来一万多本书,竟然没有一本有问题的。真是岂有此理!
各地官员接到这道谕旨,纷纷低头不语,企图蒙混过关。
中年乾隆是个不依不饶的狠主,见全国的官员、百姓统统跟自己玩起了心眼,他也就不再含蓄,直接亮明了野蛮意图。就在宣布修《四库全书》的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乾隆直接命令各地大员:“再令诚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
乾隆说,既然民间百姓不交,那么你们就派可靠能干的人到那些藏书多的人家去查禁书,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总之一定要让他们把不法违禁的书籍统统交出来。
这是一件很失民心,而且难以办到的事。各地大员都不愿趟浑水,于是能拖就拖,能躲就躲,妄想应付一阵子之后,皇帝老儿能够知难而退,事情能够不了了之。
乾隆见状,手中端着一时无法开火的枪,很是郁闷。
就在这个时候,可怜且无辜的王锡侯撞到了乾隆的枪口上。所以说,乾隆在王锡侯冤案中所表现出来的丧心病狂不是偶然,而是他帝王阴谋的必然。
史书上说,《字贯》的作者王锡侯本质上是个老实巴交的读书人,此人穷苦出身,三十八岁才考中举人,之后又连续九次会试落第。冤案发生的这一年,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全部家产,把锅碗瓢盆、猪仔母鸡统统计算在内,只有六十几两银子。他之所以呕心沥血地编纂这本字典,为的只是能留下自己的才学,把书卖出去,赚一些散碎银两,补贴家用。
可悲的是,此时的乾隆极度刻薄寡恩,根本不理会这些实情。
为了杀鸡儆猴,有力地推动查抄全国禁书,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乾隆做出裁决,王锡侯大逆不道,斩立决;他的几个儿子以及年满十六岁的孙子,一共七人,斩监侯,秋后处斩;他的妻子儿媳以及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孙子,一律赏给功臣之家,永世为奴。
为了震慑搜查禁书不积极的各方大员,江西巡抚海成也跟着倒霉,成了靶子,被判了一个斩监侯。乾隆说,重判江西巡抚海成,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教训,“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
在上谕中,乾隆还说:“各省地方务须时刻留心省查,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
见乾隆的屠刀已经举起,全国各地的封疆大吏再不敢怠慢,顷刻间,一场满清毁灭中原文化的血雨腥风随之卷席而来。
有史记载,浙江巡抚三宝,为了搜出辖区禁书,将全省的教职人员统统派回各自的老家,三宝要求,返乡人员,要以走亲访友串门的名义,一家家暗访查抄。谁查出的禁书多,就升谁的官。
此法奏效之后,三宝将搜书经验写成奏折上报军机处,军机处随即向全国推广三宝的“宝贵经验”,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搜书毁书进展得如火如荼,甚至许多穷乡僻壤也被闹得鸡犬不宁。
那一时期,紫禁城武英殿前树起了一个巨大的字纸炉,不分昼夜地焚烧禁书。
乾隆一共烧了多少书呢?
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章太炎在《哀焚书》中说得更是一针见血,“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乾隆这皇帝老儿,实在是混蛋透顶,他一面好大喜功地向世人宣布,修了一部《四库全书》,可背地里他又残暴无耻地烧了一部更珍贵的《四库全书》。
他的功里全是罪!
让后世的清醒文人更加愤怒的是,乾隆烧了一部《四库全书》,还不放心。他认为光靠官员搜书是不够的,要想烧尽天下“反清禁书”,最好是让老百姓彻底地恐惧,主动地悄悄地去销毁家中的藏书。
于是,比窦娥还冤的文字冤狱成了乾隆朝中期的一种常态。

不妨来讲几个。
还是乾隆四十二年,王锡侯冤案发生之后,一个叫蔡嘉树的江苏扬州人,跑到官府,指控一个死人“大逆不道”。
这个死人,名叫徐述夔,是蔡嘉树的同乡,生前他写了一部诗集,《一柱楼诗》。
蔡嘉树说,《一柱楼诗》中有这么一句诗,”明朝期振翮(he),一举去清都“,这句诗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叙事抒情,意思是说,明天早上我要展翅高飞,离开这个城市。但蔡嘉树却一口咬定,这句诗很反动,徐述夔要复兴明朝,还想毁灭大清都城。
蔡嘉树这厮跟江西新昌县的王泷南属于一路货色,都是地方上恶名远播的地痞无赖,他状告死人徐述夔,为的是霸占徐家子孙的几亩良田。
此案层层上报上去,”乾隆圣君“最终是怎么判决的呢?
毫无人性,残酷之极。
徐述夔和他的儿子虽然已经死去多年,但罪不可恕,当以大逆之罪,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家第三代徐食田等活着的五人,判处斩监侯,徐家家产全部没收入官。
类似这样的冤惨之案,在当时还有很多。
湖北黄梅有一个人,名叫石卓槐,一辈子没写过几首诗,结果就因为写了两句”大道日已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最终落了个凌迟处死,亲属缘坐的悲惨结局。
这两句诗有什么问题呢?
无非就是发了两句文人的牢骚,说了一句当今社会风气有些不好,太拜金了。
一句牢骚被凌迟,乾隆盛世投射下的阴影是多么的让人恐惧。
再讲一个,同样让人感到无语。
有个康熙年间的老文人,生前写了本诗集,全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诗集的名字没有起好,叫了一个《亿鸣集》,结果到了乾隆那里,就成了”追忆明朝“,罪不可恕,其孙缘坐,秋后处决。
文字狱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乾隆一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盛世?
乾隆朝的大学士梁诗正六十多岁终于退休后,曾与密友谈起为官秘诀,他说:”一切字迹最紧要,我在内廷时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至于民间,
天下尽是纸灰,尽是沉默至死······
可叹那一部《四库全书》,吹走面上的浮华,露出的都是山河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