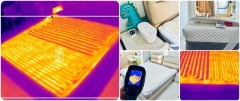本文章为“一条”原创,未经允许不得删改、盗用至任何平台,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88年的张弘扬,
出生在苏州太湖边上,
8岁,开始系统学习吴门画派国画,
18岁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
而后多次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举办个展,
大家都喊她“小菩提”。

她痴迷于传统的、断了代的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屏风上作画,
收集从国外回流的素屏,
绘上茶室、山水、树木、花鸟、小红人,
一屏在屋,仿佛置身于中国山水中;
她也将屏风融入自己的生活中,
作画、喝茶、吃羊肉火锅时,增添私密性。


她一人独居北京,
家亦是创作空间,
一条在立秋拜访了她,
并和她一起去郊外爬了次野长城,寻找灵感。
撰文 陈薇沁 责编 陈子文



机缘巧合之下,我在小菩提家中的客房住了3天。她是个极随和的人,不过深夜她的柴犬豆豆替我守门,这倒让她伤心了小一会。
与其说是客房,这更像一个艺术的仓库,堆砌着她创作的国画,墙边斜插着巨大的六联屏风,画作上随意放置着她刚画完的桂花团扇。
她创作力最旺盛时在深夜。燃上炭、茶壶在炭火架子上翻腾、泡上一壶又一壶的岩茶,聊上许久白天记不起来的故事,不怕咖啡因扰眠……柴犬豆豆已经在脚边安然熟睡,她整个人却是宛若新生,从客房里拉出1米74的金绢屏风,展开的一瞬间,金光从幽暗中绽放。


屏风源自三千多年前的周,为天子专用的器具,以木为框,上裱绛帛,画了斧钺,《史记》中记载“天子当屏而立”,经过漫长的发展,成了一种断代的艺术品。小菩提在8年前留意到了古画中的屏风,深受吸引,陆续收了好一些50岁、100岁的素屏,尝试屏上作画。
夜色正浓,一个姑娘在月色、屏面和炭火的陪衬下,起笔落墨。
以下是小菩提的自述。

屏风:当历史走进了现实
大家都喜欢喊我“小菩提”,苏州出生,杭州读大学,在北京已生活了10年。我总开玩笑说人生愿望是“吃遍五湖四海,玩遍四海八荒”。


刚进大学的时候,在国美的国画系,有一堂课是临摹宋元小品画,其中有一张叫《山馆读书图》,里面的主人在伏案读书,外面的小童在洒扫,两人之间就隔着一张巨大的屏风,它就像主人的一个影子,默默屹立在那陪伴着他,这个小东西就吸引到我了。
当时,国内专业绘制屏风画的人是不多的,我就关注了一些写屏风的作者,学者巫鸿着重写了古代屏风的“画中画、屏中屏”,央美的老师、学者黄小峰,专门注解了屏风的种类、式样、功能。

屏风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礼记·明堂位》记录了周天子坐在一个屏风前,接受群臣的朝拜,它是一种天子威严的象征。随着时代的变更,它更多成为文人士大夫审美的体现,变得居家化、私人化。

宋代《槐荫消夏图》,一个男子躺在榻上闭目惬意,有一面屏风为他挡了风,又遮了阳光。
回到苏州我就叫小伙伴帮我一起找一找这样的屏风,却一直没找到大小合适的素屏。直到2018年在朋友的店里,我看到了他从日本收来的小小的屏风,金光闪闪的,当时我非常激动,说让我拿回去试试吧,画完后效果特别好。之后,我便陆续去收类似的老屏风。



这些屏风通常分为三种材质,一种是金箔面,一种是金绢,另外一种是纸。边框是朱砂色或黑色的大漆,以前的文人雅士在屏风上放一些珍贵的材料,像是螺钿、象牙,现在我们会更喜欢装裱金属的边框,不怕搬运上的挪动。


《幽居图》是金箔面的,画在了1米73的六联屏风上。一棵南浔古镇上的老树是原型,后半段枯死,前半段新生,我当时觉得这棵树长成了年轻和年老的两种状态,在树窝上,画了一个小红人,幻想着这些成百上千年的古树上,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精灵呢?

金箔面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好画,笔墨落上去就像是点在了塑料上,我就和好友探讨了很久,在部分区域撒上一些婴儿爽身粉,再用砂纸细细给它磨了一些,墨水才终于能上去了。
同时,金箔面上的颜料墨色是遇水则融,我思考,过了三五年,看腻了,把这幅图擦了,再来一幅。

金箔面是很多人的乍眼之欢,永远泛着黄金的光泽;金绢面则是久处不厌,它泛着淡淡的金色,比较适合表现笔墨层次,一旦落笔就不能改了。

最近在画的《萱草柏树图》,构思花了1个多月,树枝的走向、萱草的数量,等真的动笔也就几天时间就有了雏形,柏树和萱草,寓意着长寿和爱。
大屏风可以给空间做一个隔断,但它不会像一堵墙一样给你堵得死死的,挪动起来很方便。北京的春天会有一点风沙,在院子里涮火锅的时候,就会拿它在后面挡一下。


55公分的小屏风《侍花图》,是一幅纸面屏风,画面中间一块玲珑剔透的太湖石贯穿两面。
它更多是一个装饰的作用,适宜放在茶室中,沸水煮叶,起了炭以后屏风微微替炭火挡了风。

住在城市里,觉得大自然太遥远了
我从小生活在苏州的光福,那个地方真的是小桥流水,家里背靠着一座铜观音寺。外婆是一个很虔诚的居士,小时候过年期间,我会跟着她去卖一些香烛。
我就在坐在她身边卖金花菜,人来人往,有一天特别幸运,我单独卖了100多块钱,外婆就带着我去街上买“野小吃”。
我的母亲是体育老师,父亲是公务员,我自小学习了书法、国画、长笛、古琴、二胡、琵琶,主要是受到了舅舅的影响。
他是一个会木匠、会谈古论今的小镇音乐班班主,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天傍晚,他会在家附近的小河,隔着大约五米的两岸吹笛子,记忆里的笛声会传得很远、很久。

大学毕业以后,我就跟家里人说,我想去北京闯一闯,全职画画,他们都很惊讶。
在北京久居的苏州人是特别少的,苏州人太喜欢安逸、舒服地过小日子,很多人甚至是照着二十四节气在过,相比之下,北漂的我算是“奇葩”了。
我认为做一个画家跟一个工作之余画画的人的状态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吴门画派的吴养木先生,他复旦毕业、曾在银行工作,最终还是彻底辞职传承这一派,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没法干这一行。

一人独居,租住在北京二环内的一个200多平米的空间里,书架、书、画册占领了一整个屋子,卫生间的浴缸里都放满了画轴。
一楼特别开辟出一个榻榻米的茶空间,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摆上一面小屏风,看着窗外一场阵雨突然而至,赏雨喝茶。


院子里种了一颗洛阳的牡丹,一颗芍药,还有两棵李子树,古人云“不可居无竹”,我就认认真真问了别人怎么种竹子,种了一排都没有活,我后来放弃了,你能活就活,它反而长得特别好,成了一片。
北京的冬天特别分明、萧条,风吹上来是干干的像小刀片一样,我可以在院子里观察枯树枝,画一画小瓷杯。


二楼是我一个更加私密的画室,我的很多小幅作品都在楼上完成,中午12点起床开始画,没人打扰,可以画到凌晨2、3点。

我身边喝茶的朋友很多,历朝历代画茶画的人和作品众多,也会让我想画这一个题材,《有关茶室》系列,把茶会场景从庭院、书斋挪到大自然当中去。



有时候在山崖之上,有时候在荷塘边上,我那个景是造,但也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状态。
可能许多人住在大城市里面,觉得这些东西离他们太遥远,但是如果你是在苏州,这些场景就真的太常见了。
我外婆跟我说,她们年轻的时候出门都是靠船,家家户户临水而居,每户都有一个台阶到水面,几乎每家都会有一个简易的小船,靠一根竹竿在水中行进。

《应月感怀》则是从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创作。当时的生物钟颠倒得厉害,凌晨2点我在小区遛狗,突然抬头看到了一轮圆月,过年回不了家,一个人在北京有些思念家人和家乡。

我就突然想:中国画里是不是可以多一些夜景?以前国画里的夜景是纯水墨的,月亮用淡墨勾出一轮,我在想能不能用颜色去表现晚上的一种状态?


一次偶然,我画出了一张晚上的白云,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一朵云和我画得一模一样。

那些国画里的场景,其实在我小时候都是真实存在的,月色下安静的村庄,包括湖面上的船只。
其实不是古画脱离了现实,而是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脱离了大自然。

单身,柴犬,快乐:先静心,才能去写字画画
不知不觉,在北京已经住了10年,目前是单身的状态,用现在的一句话来讲,是“沉浸式单身”。
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很多人就很难理解,问你一句:你一个人不孤独吗?当我回到老家,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的那种状态下,我画不了画。只有你先静心,才能去画画写字。


家中一人一狗,想去旅行就去旅行,带上笔墨纸砚,去那些风景特别好的地方写生。
每隔1、2个月,就会去怀柔地区拜访我朋友的山居,一群女孩子扎堆玩,各行各业,金融的、新媒体的、作家等等都有,有些是00后刚上班,有些年龄比我稍大。大家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民宿里面还有两颗老的核桃树,我们也会在下面,喝别人刚从武夷山带回来的茶叶。


山里信号不太好,甚至连可乐都不提供。一群人吹吹山风,去爬野长城,登山、远望,我带上尺八,在烽火台上吹一曲《虚铃》,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尺八本身也是一个断了代的乐器。2012年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视频,一个外国人吹着尺八、配着一个比丘尼的吟唱,像是一个修行的长老在低吟,我当时就疯狂地找这是什么乐器,声音如此迷人。辗转问到朋友,他说尺八起源于唐朝,后来流传到了日本,随着时代更替慢慢落寞,《虚铃》是我国唐朝以来唯一流传下来的曲子。

像尺八、屏风,它们以前都是文人墨客大量研究、使用的东西,现在都成了小众。
最近,由画家,包括收老屏风的人、爱好尺八的匠人,慢慢又把这些文化带了起来。
大家会慢慢重新看到屏风,家里、茶室或卧室都可以摆上,其实大家的审美品味都在提高,对自己的生活品质也越来越有美的要求。
本文章为“一条”原创,未经允许不得删改、盗用至任何平台,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