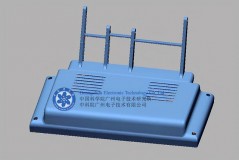2017年,摄影师张克纯的《山水之间》系列,
让他成为中国唯一入围过马格南摄影奖的摄影师,
可以说是中国山水摄影第一人。
作品曾被美国《时代周刊》、
英国BBC电视台等权威媒体刊载,
被视为中国最具潜力与收藏价值的摄影师之一。


2016年,张克纯在成都的市郊,
买下了一套300㎡的清水房,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亲自改造,
作为四十岁之后的避世之所;
他还将自己多年从全国各地收回来的,
老物件、高古陶器塞满屋子,
虽然价钱不贵、但却足够美。


疫情爆发以来,
张克纯没有办法出门拍照,
就一直待在家里,
钓鱼、喝茶、发呆,
彻底放弃了社交:
“人过了40,
不会说为了面子上的事情去迎合场合,
我习惯一个人完成所有事情。”
自述 张克纯
编辑 陈稻稻 责编 邓凯蕾


徒手装修清水房,一张图纸都没画
我的家位于成都的西边,从市中心打车过去大概40分钟的路程。成都西边说是要西控嘛,再发展也就是做园林、种种树什么的,2016年就在这里买了这套房子。
我又不是上班族,待在市中心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我不喜欢凑热闹,让我一个人待着没问题。

房子买回来的时候,是清水房,什么都没有弄过,都要靠自己。
我以前是室内设计师,晚上经常熬夜画图,有时候客户晚上6点给一个想法,早上9点钟就要。觉得自己干不了这个,就闪了。
自己的房子就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方案来做,我甚至连一张图纸都没有画。就是想到哪做哪,相当于凑一个房子出来,前前后后弄了一年。

房子将近300㎡,有三层。一层是客厅、厨房;二层是卧室;三层原本是一个主人的卧室,我把它改造成了工作、休息的地方。

成都有太阳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特别在冬天,基本上跟过节一样。所以朝太阳的方向,我做了一个榻榻米的空间,可以从早上一直晒到下午。

收藏的东西都不贵,但足够好看
我的老家在一个小镇上,有一套清早期的房子,两三百年了,一直保留着。里面有很多老的雕版、银元、罐子。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对于老的东西,我是不排斥的。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曾经辍学半年,走村串户地去收老东西,买了很多钱币、陶瓷。后来爷爷把我揪到学校去,不然已经成为辍学青年了。

这几年出去转、拍照,有时候还和朋友坐着高铁,专门去赶地摊、老市场转一下。
河南有一个老师,是做古董生意的,收了几十年的老东西。我们跟着他学一点,辩个真假。我对于官窑不感兴趣,去的都是破烂的店。不喜欢太贵的东西,一万块钱顶天了。

客厅里的小茶几,是从广东江门那边收回来的。它是清代木头做的保险柜,背面有被虫蛀过的痕迹,一户人家觉得是一个破烂,200多块钱就卖给我了。

高古的陶罐是从各地方收回来的,有些年代相对久远一些,有2000年的历史。像羌族的羊头罐,应该是汉代的,是在成都的古玩店买回来的。
大罐子是秦代的。据说埋在土里可以听到马蹄声,有军事的作用。秦代过后,因为罐子没有足,使用不太方便,就淘汰了。但现在韩国有艺术家,照着这个形状在仿制。

我收藏的东西都很素,但好看,有时间的痕迹,符合我审美的需要。
有一段时间,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花在收藏这件事上,过一段时间,就会让自己远离一些。因为实在太耗费精力了,我不想玩物丧志。

斩获法国摄影奖的中国第一人
家里挂满山山水水
我是2005年开始从事摄影的,拍了差不多三年。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期,我拍了一张照片叫《地震中的狗》,获得了当年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自然类一等奖。但这张照片太惨烈了,至今自己都不敢看。
之后,我不再满足于做新闻类的纪实摄影。2009年,就辞职从上海回到成都,开始准备自己的摄影系列。


2014年,《北流活活》系列获得了当年法国阿尔勒摄影节的发现奖。
阿尔勒摄影节在全球是一个很重要的摄影节,当时能够去参加展览,就已经觉得很好了。没想到最后一天晚上,在一个特别古典的古罗马剧院里面,把奖项颁给了我,当时很惊讶。得奖或者入围,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是一种肯定。
在中国,艺术摄影还在一个起步的阶段,中国国家博物馆、美术馆,没有摄影这个部门,目前大部分关注到的摄影还停留在纪实的阶段,要靠这个糊口特别困难,但也不想用其他职业来养活摄影,还是希望它能够独立运转。

幸好现在有不少民间机构,在做艺术摄影的收藏与研究。前一阵子,某国际大牌中华区的老板还收藏了我的作品。这些也更加坚定了自己走艺术摄影这条路。


我现在客厅里,挂了一幅2米6的摄影作品叫《黛山》,是2018年拍的。
当时,我本来是想去藏区拍另一座山的,但因为时间和天气都不合适,就没去。黛山,我是经过很多次都没有进去,那次路过,就想去看一下,结果一看,发现这个地方太棒了。
我在这个场景里做了置换,画面里其中一个人是我,其余是我的朋友,也是游客。

这张照片体现了我观看山水的一个维度,有一种像王希孟《千里江山图》青绿山水的感觉。它是由好几张照片拼接起来,放大,细节仔细看都没有问题。

二层则挂了一张在山西拍的照片。山西的土比较松,山容易塌方,所以他们用石头把整个山给包起来,在上面建了一座小寺庙。
早上有很多人喜欢在那遛弯跑步,走到头,有一个小的山崖,他们都喜欢探头去看一下。我很好奇,他们看什么?就也去置换,探头拍了一张。


三层挂的那张,是在重庆拍的。
长江的中心会有一些岩石形成的小岛,重庆冬泳的爱好者特别多。因为我小时候也会冬泳,就特别想拍一张这样的照片。那一次,我好不容易游到对岸去拍,还冻感冒了。

水对我来说,是很亲近的
小时候,我就住在一个小河边,喜欢钓鱼。
去年因为疫情出不了门,正好家旁边有一个水库,就去玩一下。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真的是每天都去钓鱼。钓鱼很安静,不能急躁,急躁了也没用。甚至有时候,我睡不着,半夜三、四点,就会一个人把小船驶到水库中央,把小鱼放在鱼竿上,模拟自己在钓大鱼。最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再从水边回来,回家休息。

在我的摄影里,水也一直是很重要的元素。小时候,我偷偷一个人跑到水边上玩,钓鱼、冬泳。长大之后,走的地方更远了,水面更大了,会关注到江、河周围发生的事情。
就像沈从文先生,他小时候是在湘西,一个小的溪流边上长大,然后慢慢地,他写的很多故事都是围绕水边来发生的。


水对我来说,是很亲近的,比如我可以在黄河边上发呆。从上午坐到下午,晒晒太阳,不拍照也行,或者就坐在那,就会发现江边上也有些人什么都不做,看着水在动,感受到了,我就愿意为他架上机器、按下快门。

踢球是我从小一直延续下来的爱好,年轻的时候,曾经想过把踢足球作为一个职业,但后面发现根本不可能。我在成都也踢了20年的球了,踢的都是“野球”,踢着玩的。半个月前还把腿踢伤了,就停下来了。
我在球场上,跟我去拍照、钓鱼,在家安静地坐着喝茶完全是两个人,是特别急躁、疯狂的人,场上歇斯底里地嘶吼,更加本真,不会去压抑自己,会全部释放出来。

不社交,习惯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
我基本不社交,周围的朋友办个展览,我都不参加。人过40,不必要的社交,我想就算了,不会再去考量面子上的事情。
我习惯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包括这么多年出去拍照,都是一个人,没有助理。因为旁边有一个人的话,我总是会顾虑、考量。

曾经有一次去拍云台山,当地人找了一个年轻人来做助理陪着我,因为景区需要爬很多山,就想让他帮忙背包。
早上需要很早起,5点钟就要去拍瀑布,为了在那个点赶到,我背着包就开始跑,小朋友跟不上,差不多隔了一个小时候才到,帮不了什么忙,所有还是喜欢一个人来做事情。


出去拍照,每天要背着东西走很多路,去找场景和人,它对于体力是有一定要求的。虽然有时候很苦,但这个苦是我心甘情愿的。而且工作的时候就不能太舒适,太舒适我就会躺上一天。
我冲洗照片的地方连网都没有,之前就是拍婚纱照的,旁边就有一个做外卖的小哥。我觉得自己有时候状态跟他们差不多,见了面,还会互相打招呼。

可能等我腿好一点,又要出去拍照了。大的方向不会改变,还是会关注小人物、中国宏大的山山水水,但也会更多地关注到自己身边一些小事情,这是以前很少做的。
或许是在钓鱼、发呆的时间久了,想到的东西不一样了,也会关注到身边的树枝、花花草草。


虽然我的照片,一直有人认为总是带有那么一点点小的忧伤。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情绪化,并没有上升到悲伤、伤感。我看待事物的方式都相对比较平静,也不会怼上去拍,或者特别剧烈的那种。

可能15年前,我比较喜欢马格南的摄影师,当时想要去拍摄、记录纪实摄影这一块的新闻报道。但现在我连电影都不敢看太悲伤的,肯定也不会为了疫情去创作,想让它尽快地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