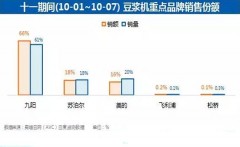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美国有网友相信德州大雪是拜登政府与比尔·盖茨联手制造的假象,英国有网友相信5G信号制造了新冠病毒,中国有网友认为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是对北京奥运会的蓄意破坏……受进步论影响的人不能理解古代文明为何如此辉煌精致,考古便成了极少数人谋财图名的托伪;坚信人性趋利避害的人不明白富豪为何要慷慨解囊,关心他人的生活和地球的命运,于是比尔·盖茨的所有公益之举都不过是在暴露他控制人类的极端野心;置身历史的浪潮而身似浮萍,如果时也命也的解释无法安慰自己,那么想象一群精英用心险恶地策划了整个事件,倒也算有个交代。只要还有超出人类经验和理解范围的事,阴谋论总能在世界的任意角落生根发芽。
相信阴谋论的人固执于自身经验,凡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就一定比别人的更真实可靠,即使是面对反思性的知识(即有关知识的知识)也不例外,因为后者是二手的,远不如“我”掌握的一手经验有价值。因此,阴谋论总是带有反智主义色彩。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德(Richard Hofstadter)将民主与平等情怀视作反智主义的根源,但正如起源于四面八方的阴谋论,反智主义的实际来源与动向要比这复杂得多。它可能来自民间的流言和对精英的不信任,也可能源自知识分子的言论,它或许始终潜行于下层,也可能与上层的意图不谋而合,又或者,它是由上至下的一种政治实践。

如果反智主义仅限于对知识精英的批评,那么它是否意味着比代议制更直接的民主,并导向一种更良好的生活?为什么反智主义总是与民粹主义政治结伴,而民众的声音最终被掩盖在民粹主义领袖的话语之下?推崇群众与民间智慧的反智与“民不可使知之”的愚民之术有何相似?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尝试循着霍夫施塔德、余英时等人对反智主义的论述来思考上述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反智主义从来不关心知识的正确性,它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涌现。另外,尽管霍夫施塔德在著名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中试图指认反智主义对智识生活以及知识分子的损害,但他对这种伤害的剖析最终绕回到智识生活所追求的美好价值上;然而,反智主义绝不仅是民主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个世界上,智识还面对着远更森冷可怕的危险。
反智与秩序:当智识被迫与美德分离
阴谋论的支持者总是怀疑,历史大事件以及自己的生活被一小撮精英秘密操纵,比如他们相信新冠病毒是由邪恶科学家福奇制造并散播的,目的是为了和富豪比尔·盖茨联手,用疫苗控制人类。阴谋论的批评者会将上述言论和行为指为“反智”。“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一词兴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彼时,美国知识分子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时常遭到攻击,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德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里用反智主义来描述当时知识分子的遭遇,并试图对美国的反智主义做一次历史的追寻。他认为,反智主义并非一套理论学说,而是一种“怨恨和怀疑”智识的态度,这种敌意有时针对智识本身,有时也指向那些被认为代表智识的人。

霍夫施塔德在其论述中区分了“智力”与“智识”:智力“在情境中抓住直接的意义并且评价它”,而智识则“评价‘评价本身’”。按照他的说法,人在运用智力时获得了对事件的第一印象,它类似于快速、直接的观察和判断,是特殊的个体经验、一种未经检验的知识;智识则后撤一步,检视整个情景与多种不同的经验。在我们的常识中,水往下流,但虹吸管里的水却可以向上走,如果一个人单凭智力来抓取这个场景的意义,便很可能认为水是反力学的,甚至进一步怀疑经典物理学是一场骗局也未可知,而运用智识精神去弄清虹吸现象液压差的道理之后,我们会发现它仍在经典力学的解释范围内。

前段时间的德州大雪被说成拜登政府与比尔·盖茨的阴谋,便是只知智力而轻贱智识的结果。TikTok的一些用户在视频里用打火机烧雪块,却发现雪不但没有融化成水,反而烧焦变黑了,这不符合常理——一定又是比尔·盖茨联合政客、科学家弄出来的假雪!其实,早在2014年暴风雪横扫亚特兰大的时候,美国天文学家Phil Plait就在一则Youtube视频里解释过“雪块燃烧”的现象——雪水没有滴落,是因为它被剩余雪块的多孔结构吸收了;雪块表面焦黑;是由打火机燃烧的丁烷造成。在知识朝着专门化一路纵深的今天,颠覆常识的阴谋论总是会被真正的专业人士戳破,尤其是在科学领域。于是,阴谋论采用了反智主义的另一条路径,即反知识分子——阴谋论不再质疑知识分子的专业能力,而将矛头对准其人格、品性与道德。
在阴谋论里,知识分子尽是阴险狡猾的自利之徒。因为聪明,他必定机关算尽;因为博学,他必定自视甚高;因为理智,他必定冷漠无情。然而智识一定与人类其他美好的素质相对吗?直觉性的情感与判断就一定向善吗?地铁上的乘客闻到建筑工人身上的汗臭,第一直觉恐怕是屏息,而后产生嫌恶,恐怕只有克服了第一直觉才能尝试了解他人的处境。又如在残障人士的问题上,简单直接的“为你好”态度已经多次受到来自残障人士内部的批评,光有好心不一定能办好事,反倒会造成许多强制和压迫。霍夫施塔德指出,反智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分配性的秩序,尽管智识与人类美德有诸多的联系,但它被迫与之分离,被发配到秩序的底端。在性别和种族问题上,我们也常窥见这种外加的不平等秩序。

无独有偶,这些秩序通常都诉诸与阴阳相关的表达。美国镀金时代的反智主义将智识与教养视作阴柔无用的“女气”,与崇尚实干、竞争、无情的阳刚相对立——讽刺的是,女性又至多被认为是有教养的,她们与智识可不能搭边。阴阳与其说是对自然价值序列的描述,不如说是预先设立了高低贵贱的一套修辞,中国古代文献在这一点上讲得更直白些。余英时曾引用马王堆帛书“称”篇的一段文字来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反智主义:“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世间万物,力强为阳,势弱为阴,无不可归入阳尊阴卑。所谓阴阳,不过给尊卑二字添了一层自然的矫饰。智识怀疑并挑战现状,为等级秩序所不容,指出错误和短处便会被骂为挑刺找茬、崇洋媚外。余英时认为儒学在西汉经历了法家化,“从道不从君”的精神被反智识的三纲所取代,公孙弘等人以等儒术缘饰吏事,使人“不但死于法”,而且 “同时又死于理”,这才是最可怕的。汉代的经义断狱为谏诤者罗织“大逆无道”“不忠不孝”之罪,今日对异见者的打压同样以叛国为诛心之法宝,麦卡锡就曾在威灵演讲上大肆污蔑美国的知识分子:
“出卖国家的,并不是那些不幸的人,也不是弱势群体的成员,而是这样的人:他们相拥着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不得不提供的一切利益——最温馨的家居、最优秀的学院教育和我们能给的最棒的职位……这帮出生时嘴里含着银勺的青年才俊从来都是最下作的家伙。”
大半个世纪过去,麦卡锡的话术我们仍不陌生。
反智与民主:源于对民主的追求就必然导向民主吗?
等级秩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上而下的反智主义,却不能很好地解释公众乃至知识分子的反智倾向。知识分子反智,乍听起来十分不合理,但正如霍夫施塔德所言,反智是充满矛盾的,极少有人完全地痛恨智识,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又爱又恨,敬畏与羞恼交杂,他们对智识的态度受各种影响左右摇摆,最能使其转向敌视的,恰恰是现代人对民主与平等的信念——如果是人人平等又民主的社会,怎能容许知识精英凌驾于众人之上,对大众生活进行评判乃至安排呢?无论知识分子是否享有精英特权,以及某些接近特权的人是否算是知识分子,智识,或者至少说专业化的知识,的确将一小部分人与公众区别开来,尽管这种区别在很多时候并没有使两者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利益相对,但他们在文化上确是不平等了。
一些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言论较为系统地呈现了这种源于民主情怀的不满。旅美学者薛涌可谓21世纪中国推崇反智的先锋人物,他曾在新浪博客上自称“反智的书生”,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通过加入反智潮流来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
2008年,薛涌曾与学者唐小兵等人围绕反智主义进行过几次论战。薛涌在《“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一文中继承了美国右翼人士Frank Chodorov的观点,宣称所有人都是经济学家,因为大家都在从事谋生的活动,他质问,“一个由所有家庭主妇参与的经济,和一个由十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操纵的经济,哪一个是市场经济?”在薛涌看来,主流经济学家们凭借专业知识的霸权性力量垄断了普通人对经济问题的发言权,反智主义就是以“人人都是经济学家的精神”来打倒“知识暴君”,突破知识阶层的话语垄断。
“最健康的制度,其公共决策是建立在最广泛的参与之上,而未必是最专业的知识之上。知识可以为人们的参与提供参照,却不能代替参与本身。这种参与性,最终要求把我们的市场经济建立在宪政的框架之中,建立在一人一票的游戏规则之上。”对怀有民主和平等信仰的人来说,薛涌的这番话不乏吸引力,但细究起来却令人疑惑——个体的经验直觉的简单加法,是否比智识性的知识更为可靠?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就必然同大众的诉求相冲突吗?阻挠政治参与的真的是“知识霸权”吗?推倒知识精英就意味着民众当家,并最后走向民主吗?

反智与民粹:单数的“人民”只存在于民粹话语的虚构中
鼓吹反智的民粹主义者激情澎湃地宣称,权利属于人民,时代也属于人民,只要打倒窃国的精英,就能夺回财富与荣耀,但实际上,反智的民粹主义者在这么说的时候,就已经破坏了他们所许诺的直接民主。他们说直接民主好过代议制民主,却从未真正想过推翻后者,不过是要自己坐上那个位置。薛涌写过一本书叫《草根才是主流》,但他的照片占去了书封的四分之三,“薛涌”二字也比书名还大,上面还有一排小字,写着“中国民间意见领袖”,极力反对启蒙视角的“反智书生”到头来还是免不了要领导一回民众。

比单纯蔑视知识分子更可怕的,是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政治的合流。像薛涌一样,许多民粹主义者常常以借反智、反精英的姿态拉拢民众,他们的话语带有“为人民发声”的使命感,似乎在有识之士里,只有自己因坚决地同人民站到一处而掌握了真理。德国政治学者扬-维尔纳·米勒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一书中提出,反对精英只是成为民粹主义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乃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现实生活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虽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具体的人民在每种特定情境下的利益诉求却是不同的,唯有当“人民”以复数的形式出现时,这些不同的诉求才有可能被听见。同质化的、单数的“人民”只存在于民粹或是极权话语的虚构当中,它以非道德化的方式排挤其他声音。这就是为什么反智的民粹主义叫嚣着要打掉知识霸权,主张万声其放,而我们却只能听见一种声音——民粹或极权领袖自己的声音,民众只不过充当了他们的回音筒和扩音器而已。

如果反智的倾向因民主和平等理想而永远不可消除,那么比起特朗普利用反智情绪来打压政治对手与科学家,造成美国新冠乱局,TikTok用户偶尔怀疑一下雪块烧焦,骂骂知识精英,似乎倒是无伤大雅了。而比起特朗普之流对反智主义的投机式利用,自上而下的、成体系的反智主义又更为可怕。霍夫施塔德所说的反智只是一种普遍弥散于民间的态度,而在韩非所代表的法家那里,反智却是一套可以具体实施的愚民政策:“……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斩断历史,禁绝思想,唯一需要学习的只有经官方阐释的行政命令。韩非以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微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总而言之,百姓鼠目寸光,缺乏大局观,不能理解统治者的长远用意,反加以最坏的揣测,因而对这样的民众,更不可“使知之”,任其妄议国事。
由此看来,霍夫施塔德仅仅将反智视为根植于民主理想的一种态度和观念,不足以概括有关反智的全部事实。反智可以起源于民主的对立面,也可以是系统性的治理术,这在历史上都曾发生过。每个地方都有反智主义言论,但我们切不可因“环球同此反智”就放松警惕。霍夫施塔德的另一个观察是,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反智主义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有时它以迫害知识分子的方式存在,有时它依赖于审查和系统管制,有时它是市民与学生之间的动乱。这些反智主义的来源与动向都需要我们进行细致的甄别与思考。
参考资料: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德 著 何博超 译 译林出版社 2021-3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余英时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6
《什么是民粹主义》 [德] 扬-维尔纳·米勒 著 钱静远 译 译林出版社 2020-5
《“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 薛涌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56
《底层、知识分子与民粹主义》 唐小兵
http://www.chinafolklore.org/web/index.php?Page=2&NewsID=3995
Fact check: Explaining ‘fake Texas snow’ posts and ‘scorched snow’ videos.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k-factcheck-not-fake-snow-idUSKBN2AN1R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