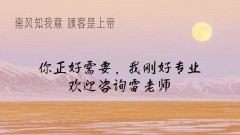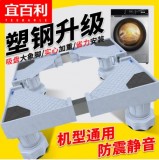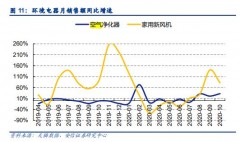北京的冬天很长,也很冷——现在仿佛没过去那么冷了,十冬腊月常看见年轻女子蹬着长筒或短筒单靴很潇洒地走在街上,有的还光着腿,我们当初穿着棉鞋脚还生冻疮呢,后来有段时间女人脚上也是鼓鼓囊囊的棉靴。反正那会儿的冬天很难过。公家规定的采暖期有4个月之久,若是生火取暖头尾总要各延长一段时间,一家人小半年都在围着煤炉过日子,那种生活迄今难忘。我的长篇小说《受命》以1980年代的北京为背景,其中有些相关描写,说来均系真实情景。
“这时屋里已经该生炉子了,但上星期天冰锋忙,还没来得及装上。春天拆了炉子,把烟筒、拐脖洗刷干净,口用报纸包上,吊在房檐底下。得去胡同里找人帮忙,连搪炉子带安烟筒”“家里已经装好炉子,是新搪的,生了火,就摆在进门不远。为了多留下一点热气,烟筒一直伸到尽南头的窗户才拐出去。叶生说,怪不得窗台上码了那么多煤呢。她要冰锋打开炉盖,炉火烧得正旺,她烤了烤手,又指着炉台上摆的一圈烤得焦黄的馒头片说,看着很香啊,我能吃一块吗?”(摘自《受命》第二部第四章)
那时候家里用的都是铸铁炉子,新的喷为灰色,久用就成铁锈色的了。下有炉门,上有炉台,一大一小两个炉圈,中置炉盖。炉台与炉门相反的一端伸出一个向上的口以连接烟筒,还有个风门。烟筒是铁皮的,有黑色与本色两种,后者稍贵,但更经用。烟筒有整截的,有半截的,还有拐脖。

最早烧的是煤球,搪炉子是个技术活。蜂窝煤炉有配套炉瓦,但炉瓦烧裂了,或结砟子太多,更换时也得搪一下,上下炉瓦的缝隙,炉瓦与炉口的连接处,均需用耐火泥抹好。烟筒和拐脖都是一头稍粗一头稍细,安装时细头朝前,插进下一截烟筒,还要用纸条把接缝糊住,自墙上横拉铁丝将其固定,从窗户高处所装铁皮中的圆孔伸出,直达房檐外,稍稍里高外低,口上安个拐脖,以免倒烟。烧煤球时还要挂个铁盒接烟油子。
家里常备几件工具:火钳子、火筷子、火铲子、火钩子,都是铸铁的。蜂窝煤用火钳子夹来,添上后用火筷子通一通煤上的火眼。最底下那块煤烧完,用火钩子擞一下就变成炉灰,掉进下面的炉膛,用火铲子铲走。要是蜂窝煤质量差,多半是黄土掺多了,烧完还是整个的,须将燃着的煤依次夹开,自上面取出。

炉台上可烤(北京话叫“炕”)馒头、白薯等。平时火上总是坐壶开水,随时可喝。炉子围个铁皮挡板,烘晾洗的衣物等。春天拆了炉子,烟筒洗刷前须轻轻敲打或在地上磕几下,以除去里面所积烟灰、铁锈。烟筒若有沙眼即不能再用,可择尚完好部分铰成半截,坏的拐脖安在屋外,废物利用。
“他身上原本有股戾气,虽然让人不太舒服,却很有精气神儿,可是那回我见他,已经一点都不见了,整个人看上去——怎么形容呢,就像过去咱们北京冬天家里生的炉子,煤还烧着,底下的铁箅子给撤掉了。”(摘自《受命》尾声)
大概20世纪70年代起,我家改烧蜂窝煤,之前烧煤球,这里提到铁箅子,乃是煤球炉的一个部件。煤球在煤铺制成,系煤末子掺少量黄土,最早是手摇的,后来改为机制。在窗根底下砌个砖池子以存放煤球,上盖苫布,免得下雨被水浸泡。还要买劈柴引火。煤球破碎造成的煤末子,攒多了加水和泥,在地上摊成一饼,用刀横竖划开,干了即煤茧儿,亦可烧用。煤球比蜂窝煤火力大,还有烧煤块的,火力更大,当时单位的澡堂子,烧的就是煤块。

蜂窝煤分大煤、小煤,厚薄不同,另有炭,厚同小煤,煤末子掺木屑制成,生火时置于最下,炉口里塞上报纸点火,先烧着炭,再引燃上面的煤。也可借别人家的炉子烧炭夹回,叫“引块炭”,系旧日邻里间常有的照应之举。20世纪 70年代中期有了液化气罐,在灶上烧炭更为方便。附带说一句,没使用液化气之前,各家夏天也要生炉子,因为要做饭。一般都放在房檐下,只装一节或半节烟筒,用来拔火。
送煤当时煤系定量供应,每家发一煤本,凭此按月叫煤,由煤铺派人送到家里。煤叫少了,则须自行去煤铺购买,以平板车或手推车拉回。我家住西颂年胡同时,煤铺在东直门南小街上,临近24路慧照寺车站;住红星胡同时,煤铺在相隔两条胡同的干面胡同里。

《受命》初稿有段文字,修改时删去,不妨抄在这里:
“冰锋去乘24路汽车。上了车,最后一排尽右边有个空座,他正需要全车厢这个最隐蔽的位置。没开出几站,车突然刹住,站着的乘客纷纷向前冲去。原来是一辆送煤的平板车从胡同口出来,大概因为拉的煤太多,拐弯又没扶好把,在汽车前头翻倒了,幸好没有被撞上。道路很窄,汽车无法绕行,只得等着满脸黢黑的送煤工从摔了一地的碎蜂窝煤中拣出一块块勉强还算完整的。只有他一个人在收拾烂摊子,过往的行人没有停下帮忙的。”

送煤是个很苦也很脏的活。平板车只能停在院门口,进院后全靠人工搬运。送煤工拿一块木板搬煤,约摸是一板6摞,每摞6块。以一家买400块计,得来回搬10趟以上,整整齐齐码在各家指定的地方。家里的窗台,宽窄恰好够放一块蜂窝煤的。
“刚才他进门时有些紧张,不小心将窗台上码着的一摞蜂窝煤碰倒了,有几块摔碎在门口。”(摘自《受命》第四部第七章)
送煤工在搬运过程中将煤摔碎,会以完整的替换,自己家的煤若摔得不太碎,往往拼在一起,对付着烧。
封火与生火烧炉子最麻烦的是封火。煤得烧旺才能封,不然就灭了;但太旺也不行,又容易烧过头了。需要根据当下火力大小,决定盖火是否盖严,中间的孔是否堵上,炉门是否留缝,乃至火眼是否稍稍错开,各种奥妙简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无论火封得多用心,都顶不了太长时间,所以每晚封火不能太早,亦即无法早睡,除非半夜起来添一回煤。炉子灭了,夜里冻得要命,早上还要笼火,假如赶着上班,就得等下班回来再说,常常为此吃不上晚饭。

平房生火保暖效果往往很差,因为一开门就是冰天雪地。每回来客,家里的人总随口喊一声“关门”,生怕把一点热气放跑了。屋子很脏,到处都落满了煤灰。城市里空气污染得也不轻,夜间,“街上能见度很差,路灯昏黄,天上迷迷蒙蒙,隐约有一弯新月的影子。雾气比白天浓重多了,能分辨出煤烟、灰尘还有别的什么成分,吸到嗓子眼里有股辣味。”(摘自《受命》第四部第四章)
早晨,“街上零零星星有些行人,有的人家在生火,烟筒飘出缕缕白色的煤烟。”(同上)
当时规定单日倒炉灰,双日倒脏土,可谓最早实施的垃圾分类。烧炉子最大的危险是煤气中毒。友人散文家、小说家闻树国君将近20年前即因此罹难。我也中过煤气,是高考第一天晚上,次日勉强去考完了,还好不算严重,整日头痛而已。
提到昔日北京胡同里的生活,有人想象得很写意, 我就记起1980 年代打开电视,时常听见一句“住进楼房多幸福”,一时特有感触;尽管接下来是“美中不足下水堵”——那是一个管道疏通机的广告。我直到快40岁时才搬进楼房,用上暖气。但现在聊聊关于煤与火的回忆,滋味却似乎在甘苦之间。

【编后】
止庵新著长篇小说《受命》(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后,颇受读者关注。
这部作品以1984年至1986年的北京为背景,针脚细密地还原了那个至今还常被人们追念的年代。正如作者所说,“在不超出人物关系与情节的前提下,希望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亦将终老于斯的城市,为已经改变的往昔的生活,记录下一点什么。详细描绘那个年代的城市面貌和人们的生活细节,其实干的是类似舞台布景师和道具师的活儿,布景与道具逼真,可以使虚构的故事与人物显得更可信一些。也就是说,虚构之中不妨有一点非虚构的因素。”止庵是位“老北京”,他对过去生活的详细了解,其实远不限于《受命》中所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