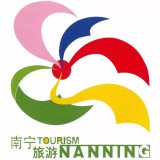我住的这个小区,是一个很大的社区,小区里密密麻麻地戳着十几幢楼,虽然不免嘈杂拥挤,但也因此在生活上十分地方便,各种大大小小的买卖,从理发修车到超市饭店一应俱全。
在小区房前楼后的门脸中,就有一家送水站。以前我很少留意这间狭小的铺面,但因有了饮水机,我和这里好像也有了丝丝缕缕的联系。除了每隔十天半个月会打电话请这儿的人送水外,每每路过这里,我也会不自觉地向里面张望一眼。
送水站里除了老板是一个中年女人外,送水工们清一色的小伙子。这是自然的,送水是个力气活。一桶水十几公斤,而且要搬上搬下的,女人断断干不来。送水工们都是从农村进城来打工的,他们大多无一技之长,就只好靠出卖体力来养家糊口了。
其实,我和送水工们很少说话。虽然天天可以看到他们穿着蓝色制服的身影在各家楼里穿梭,也会时不时地进到我家,但作为一个单身生活的女人,对这些搞不清来路的打工者,心理上难免会保持着一丝戒备。
但有一个人,我却慢慢地开始留意起来。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从来也没问过。我注意他,是因为他个子非常矮小,好像完全不适合做这类力气活。而且他的表情格外阴沉,无论何时遇到,他也不会主动抬头讲上一句话。当然,他不说话最好,如果他真的和我说太多话,也许就会打探出我的底细,这是我万万不希望的。我注意他,实在是他的表情太奇怪了,老是低着头,即使抬着头的时候,脸上也是乌云密布,很像是《智取威虎山》中满怀深仇大恨的李勇奇。
每次他来,总是低着头进我的家门,默默地将我已经喝光的水桶卸下,再默默地将满桶新水换上。最后,是默默地从我手中接过水票,听我说一句“辛苦啦,谢谢你啊。”然后默默地转身出门。
这个人,真是奇怪啊。每次送他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这么一下。怎么他好像永远跟人有仇似的?我摇摇头暗自笑笑。
如果不是那一天的事情,我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听到这个人说话。
按照送水站的规矩,我的饮水机可以每三个月由他们负责免费做一次清洗消毒。因为他们站里有好几个小伙子,每次清洗都是不同的人来的。而这一次就正好赶上了他。
清洗消毒虽然不是很麻烦的工程,但是每次也需要半个小时。当我打开门看到进来的是他时,心里有那么一丝丝的不情愿。和一个不爱言谈,又表情阴冷的人共处半个小时,实在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觉得家里的空气因此而变得压抑起来,令我呼吸有些困难。
小伙子仍是默默地做事,擦饮水机的外壳,用水冲洗桶底内部。
这个过程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然后,他把饮水机接上了一个臭氧消毒装置,通电后,开始消毒。我看到他定的时间是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里难道我们像两个机器人一样不说话吗?
我请他坐在沙发上休息。又问他要不要喝水。
他坐下了。我本以为,他还是不会说话,但是,一抬头,发现他竟然难得地笑了,倒令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我吃了一惊。原来,他也是会笑的。

于是,我开始跟他聊天。我有点没话找话地问到他怎么会做这一行,是从哪里来北京的。他说是四川。呀,我叫了一声。我刚从四川回来呢。听我这么说,他有点高兴起来,问我去了哪里,我说去了成都市,还去了青城山。
青城山吗?小伙子的眼睛亮了一下。那是我的家乡啊。他的表情分明是兴奋的那种。
他问我青城山是不是很好看。我说是,山上有好多的树。可惜我的腰不好,没能爬山。
我问他有多久没有回家了。他刚亮起来的眼睛暗淡了。“四五年了。”他低下头说。我惊奇地问他怎么会这么久不回家。难道家里人不想你,你也不想家里人吗?
他沉默了好久,说:想。
可是,为什么你不回家呢?
小伙子又是沉默。接着,给我讲了他自己的经历。
他其实是出生在成都的。但在他还没有记忆的时侯,他在川剧团工作的父母,遭人冤枉,被赶回了老家。那正是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期。
“你看不出来吧?我都已经三十好几岁了呢。”他问我。是不大看得出来,因为他长得瘦小,好像最多不过二十七八的样子。
很小的时候,大概只有几岁吧,他考上了去他家乡招生的安徽的一个黄梅戏剧团。可是,因为要交一笔培训费,而他的家里没有钱,因此,这个机会错过了。
再后来,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他就跑到北京打工来了。
他知道自己不会永远给人打工,一定有可以出头的那天。靠着在一家饭店给人洗碗开始,慢慢做到配菜工,再到当了大厨。直到有一天,他挣下一笔钱,再加上跟朋友们借的一笔钱,他包下一间一楼一底的饭店,自己当上了老板。
那个消毒机已经转到了头,小伙子站起来,又重新转动按钮,说:“多消一会毒也没事儿。”我知道,他是想跟我说说话。也许他已经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这么多话了。
他的饭店做得挺好,有二十几个员工。楼上还有一个小小歌厅。“就在垂扬柳那一带,你知道吧?”我知道那一带,可是我记不住那么多饭店的名字。
他也并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他的饭店而扫兴,“反正那饭店早已经不在了。”他说。
那时,他没有开饭店的经验,不是说他不会管理一家饭店,而是他不知道开饭店是要跟三教九流的人物都要拉关系的,黑道白道两通才能做得下去买卖。而他不懂,以为靠自己一手做川菜的好手艺就可以赚大钱了。结果,他没有向那一带的地痦流氓们交保护费。于是,终于有一天,那伙人找了个茬把他的饭店给砸了。那一架打得惊动了警察,他的员工们和地痦一道被统统带到了公安局。事后,交了罚款,他的店也开不下去了。因为一楼一底的饭店被砸得面目全非,加上好多公司在那里吃饭欠的账,他赔进去了将近十万块钱。
他的老板当不成了,跑出来给人打工。从那时起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他觉得没有脸见父母。因为刚当上老板时风风光光地回过一次家,现在他不想让家里人觉得他失败了。
消毒机又一次转到了头。他站起身,一边收拾东西,一边下决心似地说:“我不会天天给人送水的,早晚有一天我还要当老板。那时我就可以回家见我爸爸妈妈了。”
小伙子的故事听上去挺离奇,我本可以当他完全是在杜撰。但是,有一个细节让我相信了他的话。当他抬起胳膊时,我看到,在他蓝色制服的里边,是一件雪白的衬衫,袖口一尘不染。这样的讲究,就完全不是一个乡下来的打工仔的作派。而且,我看见他的手上戴了一枚精致的戒指。
他说,他准备还是回到原来那个小区去开一家小吃店。我问他为何不就开在我们这个小区里。他说,这边的人他不熟,而垂扬柳那带有他好多四川老乡,可以相互帮帮忙。
我问他现在每个月挣多少钱,他说可以有差不多一千块钱。其实底薪只有五十块,靠卖饮水机的提成和给人送水的计件工资。
我操心他靠送水什么时候才能挣够开店的钱啊?他说,开家小吃店两万块就能起步了。他原先店里所有的餐具都存在老乡的店里,不用再花钱买了。
他原来抽烟喝酒,可是现在全戒掉了,把每一分钱都存了下来,只为开一个店。而且,三十好几了也还没有结婚。
“哪怕只开上一天,我就能回家了。可以跟我的爸爸妈妈有个交待了。”他表情很凝重地说。
这一回,那个沉默不语的人换作了我。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
看他就要出门了,我忙开了口,“小伙子,你的心愿我很明白,可是你知道你父母的心愿吗?对于做父母的人来说,他们也许并不关心你挣多少钱,他们希望的是你的平安健康。早点回家看看吧。哪怕给你的父母打个电话呢。”
小伙子已经扛起换下的空桶走到了门口,在他出门前那一刻,他回头说:“谢谢你大姐,你的话我记住了,也许那个店开张前,我会先回家看看。”
我倚着门框目送他下楼。脑子里倏乎闪现出一张母亲的脸,那张脸在遥远的青城山,也正倚门而站,眺望着远方。
那是儿子归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