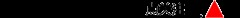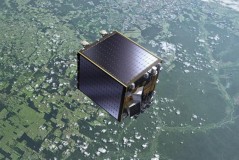〇家里的叫声真热闹
电器多了,叫声多了,家里真热闹。
全自动洗衣机倒是省事,把衣服扔进去,放上洗衣粉,打开水龙头,就呼哧呼哧运转开了;脱水后,会滴滴滴叫,像猫狗唤它的主人,往往这时我就会边跑边喊:“莫叫,来了,来了。”有时,分明听见叫声,忙别的事去了,等到记起,漂洗的衣服已成了皱巴巴的腌菜。
老天冷热过了头,空调会站出来说话。如果说电灯的语言是光明与温暖,冰箱就是冷若冰霜,任你怎么亲近,任你掏心掏肺,横竖不说一句话,它的热情都化作为你提供保鲜的食物了。热水器叫过,我们连五脏六腑都冲洗干净了。
座机电话曾是对外联系的主角。自从一家三口都拥有手机,它受到冷落,就很少出声了。手机是妻的更夫,每天清晨5点,闹铃准时响起,妻开始起床修她的早课:读书,做操,跑步。夜深人静,我的手机铃声比卖老面馒头的老爹还叫得响。“本来睡着了,又被它吵醒了!”习惯早睡的妻抗议。因此,晚上十点以后,我会把铃声设为振动。其实,也不是所有来电都得接听,而有时接与不接又很为难。有一次,人家先后用座机和手机打了我手机若干次,弄得我的手机在手心发抖,我只好把它扔到桌上,跑去门外。
厨房的叫声最频繁。除了解冻、加热,我喜欢用微波炉烤豆子。年过古稀的父亲,依然钟情土地,每年都要收获上百斤豆子,黄豆、乌豆都有,我们做晚辈的坐享其成。回老家的时候,母亲总要给我带好些豆子,一边替我收拾,还一边说,多装点,再装点。微波炉不必时刻守着,豆子熟了,它就叫,三四分钟一次,只消我过去把熟的倒出来,添上生的。几个小时过去,一盆豆子熟了。这时,妻会不失时机地恭维一句:“哟,满屋子香啊!”而豆浆机一叫,妻的早餐就成了。妻吃得比我更简单,一条黄瓜,一只红薯,或半把花生米,加一碗豆浆,就足够。当高压锅发出叫声时,说明菜就要上桌了。
自从矿泉水进屋后,电水壶基本处于离岗状态,只在冬天才偶尔拿出来用一用。有一段时间,妻迷上了卢梭的文字,把他的书读了好多遍。据说卢梭身无分文,仍云游天下,妻受其影响,萌发了旅游的念头。因为手头不宽裕,我担心她真要出去,她说,能听到火车叫就行了。每每这时,我就到厨房去烧一壶水,水沸腾后,壶嘴发出的叫声酷似火车轰鸣。妻听到叫声,开怀地笑,高声喊:“呜呜——呜呜——,我们家的火车出发了!”戏到底做不了多久,妻还是时常念叨火车的叫声。于是,周末,我与妻儿坐上公交车来到火车站。轰隆轰隆,一列列呼啸的火车来了,停了,去了。站牌下,妻频频挥手,激动得跳起来,连声大喊:“火车!火车!”喊得我心里发酸。这些年来,她跟我过着清贫的日子,除蜜月去了一趟张家界,二十年再没一起出过远门,真是惭愧。妻倒没这样深想,那天看了火车后,一家人跑书店,上公园,吃烧烤,在城里玩了大半天,竟然非常开心。
我与妻都是书虫,乐在其中。儿子放学后,电视、电脑就别想睡懒觉了。好在门铃早就拆除,要不,又多一种叫声,多一份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