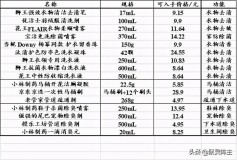这里的故事都不算新鲜。中国互联网几十年发展过程中,风口变幻,高途用很短的时间演示了一家发现蓝海,投身而入的公司又如何被迅速抛下。在它的故事里,可以看到“大佬”的创业情怀,和瑞幸相似的被做空,ofo与摩拜、滴滴与优步“烧钱游戏”的缩影以及政策突变带来的釜底抽薪。当然,也少不了一群坐在财富过山车上的人,所经历的人性的考验和挣扎。
文 | 徐晴
编辑 | 金汤
运营 | Trixy
陈向东终于“震怒”了。
这是“双减”巨雷打在在线教育行业后的第四个月。高途仍在灾后重建,创始人兼董事长陈向东每天都会关注其他同行正在做什么,“老大爷一样碎碎念”。在职员工告诉每日人物,有一次他听说,公司里几位主讲老师正带着高途的学生“出走”,自立门户,尝试直播授课。
陈向东动了气。几个高管更是较起了劲,他们的解决方案是,蹲守在直播间,一看到这几位主讲老师直播,就立刻举报。
原本,一位留在高途的员工观察到,这几个月,陈向东的状态已经从忐忑转向平静,再变成满怀希望。他想了诸多举措应对政策带来的巨大改变。比如做硬件,但又觉得这是重资产,容易积压库存。他也想让高途直播带货,“反正就是不用花太多钱的、有人力就能做的事,他都想尝试一下”。
最近几天,已经有几位主讲老师被拉去试水直播带货。但陈向东又不想效仿俞敏洪,什么都卖,他跟员工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做教育了,我就退休了”。
这位高途的绝对控制人开始变得乐观。近期的一次全员会上,陈向东说“现在是公司最好的时候”,他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调侃自己:“我也经历过股价140多美元的时候”“我也是登上过富豪排行榜的人”……试图告诉现今留在高途的九千六百多位员工,两块多美元的股价和低谷并不可怕,高途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每隔一阵子,高途就会有一次鼓励为主、讲述战略为辅的会议在不同部门召开。有人看到,陈向东的眼睛里多了些红血丝,相较从前,他的头发也白了不少。
去年公司被连续做空的时候,他的朋友圈像一个对外传声的话筒,热闹、激烈。现在,他的朋友圈仅一个月可见,点开只剩一条横线。但至少,陈向东表现出来的振奋和轻快仍然感染了不少员工,他们也振作起来,试图忘记头顶那一片仍未消散的阴霾。
7月24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份被简称为“双减”的意见对教培机构的投融资、业务类型、经营时间都做出了严格限制。高途的股票应声而落,一部分员工被迫离开,大课直播间陆续关停。
这家曾经名为“跟谁学”、后改名“高途”的在线教育公司,是首个抓住在线教育风口的公司之一。它依靠“all in在线直播大班课”而迅速崛起、率先上市,站上了在线教育行业的巅峰。
但很快,蓝海变成红海,更多的公司和金钱滚入行业,靠情怀构筑的美好愿景被拉回到现实,化为一片巷战和肉搏。在尚未分出胜负时,红海变为“死海”,曾经风头无两的行业标杆要重新探索未来。

▲ 陈向东演讲之后,走下讲台。图 / 视觉中国
“把命注入”巨雷在今年8月的一天落下。那一天,陈向东在高途全员会上宣布,全国十三个地方中心只保留三个。每个中心人数过千,裁员涉及上万人。紧接着,所有人都停下了工作。大家漫不经心地坐在工位上玩游戏,办公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timi”。
一周之前的7月24日,“双减”落地,办公室的气氛开始变得不同:电话销售的声音越来越小,从同事工位走过,有人会马上护住屏幕。零星有几位员工手足无措又无所事事地等到晚上——加班已经成为肌肉记忆,11点,他们收拾东西离开公司。
阿明是博彦科技大厦的安保。他记得,办公区没几天就没了人。到了8月底,司机和搬家师傅进入大楼,搬走办公用品。他们彻夜不休,桌椅被搬上车时“叮叮咣咣”。9月2日早上7点,阿明叫醒了一位睡在一层大厅的司机,告诉他,高途与博彦的租约已经在7个小时前正式到期,搬家到此为止。
9月的一个晚上,前员工林一再一次进入了高途在博彦科技大厦的办公室,塑料袋、矿泉水瓶、裸露的电线和一些零散的垃圾散布在各处,还没搬走的椅子像超市的手推车一样堆叠在一起,只有绿色的应急灯阴惨惨地开着。附近安静得可以听见虫鸣。他神色黯然,难以相信高途的寥落。

▲ 高途原办公区的寥落。图 / 徐晴
时间像是被7月24日那一天切割成两块。在这之前,这里总是喧嚣。
网约车司机不喜欢这里。从晚上十点或更早开始,进入这个区域的路会堵得像一锅粥,满处都是车灯的光亮和喇叭的响声。这个由博彦科技大厦、东软北京研发中心、软件园互联网创新中心、文思海辉、中关村新兴产业联盟围成的区域,曾是高途在北京的办公地,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相继被租下。
没人能轻易在这里打到车,滴滴总是显示,前面还有两百多位乘客在排队等待。几栋楼下,永远停留着十几位外卖骑手。由于外卖数量太多,容易丢失,高途允许美团在大楼门口设立了一整面墙的外卖柜。
阿明曾经在大厦一层拦下十几位信用卡推销员,还曾发现数家装修公司员工戴着鸭舌帽、怀揣照相机走进大厦一通拍摄。——这两年,不少中小型在线教育公司会向装修公司提出“按照高途(跟谁学)的风格来”的要求,迫使他们来学习经验。
楼里也是嘈杂的。办公区里,辅导老师们戴着降噪耳机给学生讲题,沸腾得像高三无人看管的自习室。激昂又整齐划一的声音会突然从各个角落里传来——会议室或是走廊的过道。
也许是口号。高级教研杨可经常看到“乌泱泱一堆人进入一个大会议室做(关于)自信的锻炼,一个个站在桌子上说我是最棒的”,“就像传销机构经常做的事”。也许是三次×三下的击掌声。在高途,一旦有家长报名了短期班,小组长会带着辅导老师们“九连拍”来庆祝业绩。
只有一些地方是安静的。比如博彦科技大厦的五层,这里密集地分布着十几个正方形格子间,主讲老师在这里直播。房间门外贴着告示,“禁止在直播间附近喊口号,禁止在直播间走廊开复盘会,谢谢体谅!”但主讲老师镜头的对面,也许是几万人在听大班课,喧哗在别处。

▲ 高途原办公区墙上的标语和告示。图 / 徐晴
主讲老师是这家公司的核心,其他的人员,包括辅导老师、教研组和运营人员都要围绕着他们来。在几年,风头最劲的几家教育培训机构里,高途一直以名师和高价精品课程与其他的公司划分界限。
从2017年年中开始,陈向东就将全部的赌注押在了名师直播大班课上,这是他选择all in的“最小单元点”,后来成为了这家公司迅速崛起的第一把秘钥。——2019年上市之前,跟谁学已经达到了连续四个季度的规模化盈利。
盈利带来了膨胀与扩张,员工这两年越来越多,林一看着企业微信人数从一万变成两万,然后被隐藏。办公桌像没有隔板的大通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一臂,逐渐缩短到不超过两个拳头,伸手打哈欠的时候,能打到旁边人的头。
每隔几个月,林一就听说有新的地方中心建成。合肥中心的板块负责人张淼曾负责英语学科的招聘,“实际上招人的速度是原本设想的三倍”,6个月的时间里,合肥中心的人数从20变成800,狭小的办公室变成三层的办公区。
一座座大厦里的高途人忙碌又骄傲。甚至,不少人发现自己在离职时还有假没休完。比如张淼,还剩28天。对此,他毫无怨言,甚至引以为傲。高途提倡“将心注入,全力以赴”,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和员工开玩笑,“将心注入不行了,我们要将命注入”。
“有情怀的教育家”一个典型的高途员工大概是这样的,学经历不算突出,骨子里有一些自卑,渴望证明自己,当他们遇到公司或是时代提供的机会,会毫不犹豫地抓住,一步步向上爬升。
林一的老家在东北,当地的平均月收入是2000元。他在这家公司做辅导老师,每个月算上奖金可以拿到20000元以上。他的家人一度十分担忧,多次询问:“你到底在北京做什么?”
汪四维在这里工作仅仅一年半,很快升任部门负责人。离开高途后,他跳槽到互联网大厂,直接进入管理层。他惊讶地发现,同级别的同事,每一个都比他大十岁或者更多。
高光和柔光曾经一起打在高途人的身上。林一感慨,“赶上一个风口,可能你本身也不怎么厉害,但是在这个风口上你也飞起来了”。
两年前的6月,一百余位员工站在纽交所的大厅里参加上市敲钟仪式。时间一到,金属圆盘在电路控制下发出有规律的响声,大家一起甩开膀子拍手,在半空中画出尽可能长的弧线。在整个纽交所227年的历史上,那一次参加敲钟仪式的人数排第一。

▲ 跟谁学上市合照。图 / 陈向东微博
想起那个情景,前联合创始人王大强(化名)语速加快,音量跟着提高:“可能是很多人的人生巅峰。”回国后,答谢晚宴在国贸大饭店举办,几个联创跟陈向东坐在一桌,设想未来公司可以达到“千亿市值”,王大强开玩笑:“兄弟们努力推一把,把Larry推到中国福布斯前十!”
现在回想起来,王大强觉得这句话“太狂妄了”。不过在2020年10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上,陈向东已经位列第47位,相比过去一年,他的财富增长662%,是上榜企业家中财富涨幅最大的一位。公司也在随后抵达了顶点,2021年1月,公司股票涨至149.1美元,市值超过380亿美元。
做教育当然不只是钱,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Larry的教育情怀”。
在内部,他们叫陈向东Larry——创业前,43岁的陈向东决心适应互联网风格,第一次给自己取了英文名,自此之后,他说话不再用“我”,只自称Larry,“就像李佳琦称呼自己是佳琦一样。”上海的员工芊芊说。
对于这家公司而言,陈向东是绝对的精神领袖,也是绝对的偶像。有人曾在凌晨一点的公司楼下看到Larry离开的背影,为此专门发了一条微博,纪念这个“奇迹一般的夜晚”。王大强了解Larry,“他不管几点起、几点睡,不管连开多久的会,从来没有见过一次他打瞌睡、打哈欠。睡午觉、打个盹都从来没有过”。
Larry乐于把激情传递给员工,像一个布道者,反复描绘教育和努力对一个人命运的改变。
他曾计划让所有的辅导老师转型为“二讲老师”,不再只承担销售任务,他们也要接受培训,定期考核,考教师资格证。他也说过要做“本地化”,让辅导老师了解当地的政策和教学情况,为学生提供更适配的服务。
这显然是一系列偏离商业、成本高昂的设想。杨可跳槽到跟谁学后,发现Larry情怀的一面要大过商业的一面,“我知道他是带着内心的一些焰火在跟我对话”。直到如今,一位被裁掉的员工仍为Larry辩护:“Larry不是资本家,他是有情怀的教育家!”
如果说直播大班课是跟谁学的第一把秘钥,那么情怀就是第二把。Larry的情怀给疯狂涌入的年轻人们穿上了战衣。他们在公司大声喊着口号,私下读着Larry的《心流》,跟着他去延安、遵义团建。情怀甚至激发出了每个人的隐藏潜能,许多人做出了超出自己责任或者是能力的事。

▲ Larry的《心流》,高途人必备。图 / 受访者提供
一位英语学科的辅导老师,为了让学生感受到高途的服务,把学生没有买课的数学家庭作业一并给检查了;高途一开始技术不完善,辅导老师时不时就要应对系统崩溃:可能是老师正讲着课,直播卡顿了,或者是学生用华为的平板打不出字,家长用苹果的手机用不了优惠券……细小的问题都可以由人去解决,比如给用苹果手机的家长单独生成一个优惠码,一个个发过去,再一个个收钱。
没有人觉得麻烦,也没人觉得难。
2020年年底,在线教育公司学霸君倒闭,许多学生维权无门。当时,陈向东决定,公司免费给这些学生上课。那一阵子,合肥中心的张淼反复向员工强调,“我们要向每个学生负责,这是我们做教育的初心”。他没说的是,公司也要靠这次机会把新客户收入囊中。有的主讲老师一天上三节课,带不同的年级、不同的班型,辅导老师的工作量也猛增好几倍。但转化率还是变成了一个难以相信、极低的数字。
接下来的一期,每个人的压力都极大,复盘会开了一场又一场。最后,有几个主管主动说,“要不我们几个自己带头上?”他们扭头去做辅导老师的工作。张淼说,有一个主管不太会英语,他说可以负责大家的后勤,每天订饭。最终,这期课程取得了800%的增长。

▲ 学霸君因资金链断裂倒闭,这一年,在线教育公司风起风落,倒下的亦有不少。图 / 微博截图
刘小海觉得,高途这些年能做起来和人有很大关系,“真的是非常拼,你在别的公司根本就找不到这么拼的人”。巅峰时期,每个人都7×24小时待命。“如果说一个人是这种工作状态不可怕,团队100多个人全都是这种工作状态,那就非常可怕了。所以大家一直说高途是一家洗脑的公司,这个公司文化确实非常牛。我还没遇到过一家公司是人人都愿意这么玩命工作的。”他说。
王大强说,高途人最常说的口号之一是“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
而且,高途提倡“伙伴文化”,大家资源共享,所有策略、方法、路径一经验证可以立刻复制。林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一季度的销冠站在台上,把自己耗费时间、精力,好不容易才总结出来的销售话术,和盘托出。那次他相信,大家并不是对手,而是并肩作战的“伙伴”。
“你不相信美好吗?”只有一处少了一些“伙伴”的情谊。
直播大班课的方式跑通以后,公司内部有两个部门关注K12(从幼儿园到高三)业务,一个是由阿里中供铁军出身的祁秀平带领的跟谁学好课,包括K12和成人、兴趣课程;另一个是搜狐视频销售中心出身的刘威负责的高途课堂,专做K12。
两个业务线打法有快有慢,但总体来说高途课堂的营收更为可观。当时在跟谁学好课部门的刘小海觉得,好课团队更加关注营利性增长,高途课堂更加关注“生命周期价值”,考虑“长线盈利”。
尽管两边都受重视,但公司给予的资源是完全不同的。刘小海直观的感受是,“一个是亲儿子,一个是干儿子”。亲儿子是高途课堂,无限投入的人力和财力让它成长为一个巨人,尽管营养不良,始终在“战略性亏损”,但它的庞大体量决定了它在公司里的地位。相比高途课堂,好课投入的资源不多,体量增长速度也慢,但却一直在盈利。
“高途课堂和好课的两拨人互相不服。好课的人觉得高途课堂是资源喂大的;高途课堂的人觉得你量这么小,你跟我说话干嘛?”更重要的是,晋升的速度也显著不同,“在好课肯定比不上高途课堂,一些管理层实力相差不大,但有的升到了经理,有的还是主管。”刘小海说。
这也证明了当时的跟谁学,陷入了一场以量取胜的比拼。如今看来,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真正的教育普惠情怀背离,情怀只关乎公司。
当公司有负面信息的时候,无论什么部门,高途人对公司的信任不会减弱分毫。
2020年2月25日,第一簇闪电划破了天空。做空机构灰熊发布报告,指出这家公司的七个经营实体在2018年夸大了74.6%的净利润;跟谁学曾要求入驻的教育机构用虚假账号刷单,平台流量和学生人数严重造假;除此之外,还有关于郑州三座大楼的价格争议,以及大股东和核心员工频繁套现等等。
这之后,从4月开始,针对跟谁学的做空报告如同网络上的连载帖。之后的12个月里,跟谁学被多家机构做空15次。
确实有一些隐而不宣的问题。比如天蝎在2020年5月发布的做空报告中指出,有员工在入职咨询群中表示,主讲老师入职之前不必有教师资格证——这与公开资料相悖;另一位在跟谁学官方介绍中的高级汉语教师李格,她所公示的教师资格证编号显示,所有者是李盼盼,任教学科是音乐。
屡遭做空以及实锤漏洞引来了股价的几次震荡和雪球用户的嘲讽。他们称陈向东为“拉总”,说“拉总的爱好和特长是拉股价”。每逢有负面新闻发布,就会有人在评论区反讽:“你不相信美好吗?”——这是因为陈向东曾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因为信任,所以简单;因为相信,所以美好。您相信了吗?”

▲ 陈向东朋友圈截图。图 / 受访者提供
关于做空,陈向东的回应多是关于他的初心、情怀、理想、格局。比如,有人质疑跟谁学刷单,他解释,跟谁学是一家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公司。再比如,陈向东去年12月接受《晚点LatePost》采访,被问到被做空14次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时,他回答,天大的运气,这创造了世界历史。
作为精神领袖,陈向东的态度直接影响员工的心态。张淼在休息日到北京总部加班,看到陈向东和高管一起开会。前一天晚上,灰熊的做空报告刚上新闻头条,眼前的这些人却有说有笑。他一下子放心了。回到合肥,做空报告已经有了6个版本,新入职的员工问,怎么回事?张淼说,习惯了。
整个公司的情况是,外界越做空,每个人越放松。大家看着股票在震荡中上扬,从40、50、60美元涨到100、120、130、149美元。一句公司内部广为流传的玩笑是,“你不要担心有人做空,你要担心的是你的工资买不起公司的股票”。
那阵子,公司拿着手机计算器算数的人多了起来。休息时间一到,会听到北京的员工们讨论在哪个区买房,他们计划在期权兑现后果断上车,在房价动辄数百万的城市里安家落户。
未来一片光明。只是直到此时,闪电后的惊雷还没有真正落下。
“资深教师”每个高途人都记得一位“老奶奶”。
去年,一个语气权威、短发泛白的“资深教师”,突然出现在4家在线教育的信息流广告里。她的身份一直变化,“40年英语老师”“一辈子小学数学老师”“专家”……广告上方或下方,logo也在变,高途课堂、作业帮、猿辅导、清北网校轮番登场。
显然,这是一位广告演员。在她的背后,正在进行一场在线教育的烧钱大战。

▲ 四家在线教育用同一“老奶奶”。图 / 抖音截图
从2019年开始,K12 直播大班课是一门好生意,成为行业共识。线下元老学而思、新东方,后起之秀猿辅导,还有字节家的新人“大力课堂”都在当年全力投入。毫无疑问,这个过热的行业,一条跑道已经挤不下了,他们最起码需要两条公交道。
等到2020年,2亿学生转到线上,这一年教培行业一共发生了111起融资事件,金额超过500亿元。投资者名单里都是最顶级的机构。
资本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也带来了新的打法。
纵观互联网发展史,每一个风口上都伴随着一场烧钱大战。有的钱“烧”出了基础设施,比如电商的物流和外卖的规模;有的钱直接“烧”成了用户补贴,培养出用户习惯。但在线教育这一次,钱直接“烧”在了营销,让广告商、节目制作方、平台赚得盆满钵满。
把钱“烧”在营销上也并不少见,前有凡客烧钱砸线下广告,后有瑞幸请来汤唯、张震让小蓝杯深入人心。在蓝海里烧钱是为了培育市场,在红海里烧钱是倚赖资本的力量撬动市场份额。
为了市场份额,在线教育的战场选在了2020年暑期。暑假之前,猿辅导、学而思、作业帮、跟谁学的营销推广预算,分别达到了15亿、12亿、10亿、8亿。
在过去,跟谁学曾是战役的旁观者,这家公司的起势一方面是因为专注三四线市场,另一方面对微信流量的运用娴熟,这让跟谁学在前端的获客成本很低,不必烧钱。
也正是因此,2020年年中接受《人物》采访时,陈向东觉得教育不该靠营销。“历史上拼命砸广告做营销的教育公司,后来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他说。
但在2020年的一个全员会上,陈向东宣布“转型去做规模性增长”。刘小海回忆,上市前和上市后公司是两种状态。上市之前跟谁学追求盈利性增长,上市之后要追求在资本市场的估值,大面积的广告也在上市之后的2019年第四季度开始投放,“公司开始对标竞品了”。当时,刘小海负责品牌投放,每天一睁眼就发愁要怎么把上千万的预算花出去。
陈向东不是一个盲从的人,他有自己的坚持。但当他站在山顶,对手们一个个滑下,同行者们的装备已经调试完毕,每个部件都已经润滑到整装待发,他没有喊停的权力,只能跟从。
林一在跟谁学办公楼的电梯里看到了猿辅导的广告。他拍了照片发给同事,同事见怪不怪地笑了笑。陈向东接受《人物》采访时说,跟谁学和竞争对手在同一辆公交车上贴广告,跟谁学在门的正面,对手就在背面。
员工把投放广告当作一种实力的证明。林一记得,去年秋天,负责高途课堂的CEO刘威在公司群里发了消息,“我们在公交站牌都已经投了广告了”。底下接连弹出几十条微信消息,大家刷屏回复,“相信高途!”

▲ 高途课堂、学而思在公交站“烧钱”。图 / 视觉中国
但真实的情况是,巨大的营销带来了巨大的亏损,“烧”走的是自家的盈利和公司的市值。终于,在保持连续8个季度的盈利后,2020年第三季度,跟谁学亏损达9.33亿元,同时,用户面临负增长。
可这个战场,只要踏进就很难退出。
战争还在继续,其中最强有力的烧钱工具是短视频平台。9月初,猿辅导日均投放927万元,跟谁学达到434万。到10月中旬,这两个数字变成1397万和713万。信息流广告采用竞价机制,战争最热的时候,一个有效获客线索从几十、几百变成了1300块——这个价格来自跟谁学。
情怀包裹着的教育平等是一个美好的概念,但掉入竞争的现实,烧钱营销成了跟谁学的第三把秘钥——和任何一个在线教育公司,或者说任何一个风口上的公司没有两样。
负责高途课堂的刘威在此时拍了桌子。他叫来了汪四维和另外几个负责人,说自己感到“痛心”,同时又觉得“可怕”。他留下任务,一天之内,获客成本要降到700块。那个会从前一天晚上开到凌晨,负责人们没有回家。
可获客成本刚降下没多久,当年10月22日,陈向东在一次内部全员会上宣布,高途课堂和跟谁学好课的K12项目将要合并,最主要的原因是营销费用花得太多。前高途师训部门负责人宋新记得他语气严厉,说“我们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合并的决定下来之后直到今年官宣,有人觉得那是刘威最绝望的时候。
在高途,刘威像一个“真正的CEO”,他永远保持着一种严肃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不像陈向东看起来亲切、和善。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从主管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人,刘威无条件听从陈向东的号令。相比舵手,他需要做的是让这艘大船上的每个零件都正常、持续地运行。
在汪四维看来,刘威是“一下子把问题戳破”的人。“他甚至不在乎这个人是谁,他就事论事,也不会给人面子。”
他觉得,刘威“可能会造成内部一些高层的不满意”。汪四维甚至隐隐感到,刘威与Larry之间“会有一些没有那么和谐”。在他看来,刘威在经营公司、孵化人才、搭建公司体系上能力强悍,但这种强悍有时会跟Larry的情怀相抵触。在公司,大家普遍认为“刘威代表了商业的那一面,是实干家,Larry代表了情怀的那一面,是精神领袖”。
此时,“精神领袖”痛心疾首。但对外,他保持着一贯的掌控感。年中一次演讲,陈向东提到:“那些竞争使得我们做出的决策,往往都会是错误的决策。”12月接受《晚点LatePost》采访时,陈向东说:“我到今天也不觉得烧钱做生意是正常的。但市场被重构,资本大量进入,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在战略投入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忍受亏损。”
只是这时候,在线教育的风口已经雷云密布。

▲ 陈向东。图 / 视觉中国
“和你共进退”惶恐和不安开始笼罩这家公司,这个行业。
今年1月,“老奶奶”事件招来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发文批评,跟谁学下架了广告和低价引流课程。
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禁止校外培训机构对学前儿童违规进行培训。5月末,陈向东关停了公司的信息流业务,裁员20%,同时关闭针对学前儿童的小早启蒙业务。
再往后,陈向东表示“不动中台了”。HR小鱼松了一口气,但7月底,“双减”落下,所有人都被高速列车的强大惯性摔在了地上。
陈向东哽咽了。
“双减”之后的全员会上,他的语速放慢了。宣布裁员后,所有人都收到了一封来自陈向东的内部信,3个排比句重复出现了5次:非常非常抱歉,我们不得不做出如此艰难的决策。非常非常难过,我们的不少小伙伴将不得不离开。非常非常伤心,我们必须割舍那么多不得不割舍的情感……

▲ 高途内部信。图 / 脉脉截图
在众多员工眼中,Larry的信情真意切。他们再一次受到感召,在被裁掉后,把“感激Larry,感激高途”设置为内部沟通软件“灵犀”上最后的签名。
办公室的人开始变得稀稀拉拉,HR小鱼在走出办公室时回望,同事们的名牌还摆在桌子上,由于太过密集、工整,远远看过去,她甚至觉得像是一个个纪念他们曾经存在过的墓碑。
林一这些辅导老师,对高途的情绪很复杂,其中最多的是惋惜。陈向东过去的愿景,不管是“二讲”还是本地化,都还没有落地。在以规模性增长为目标的背景下,业绩排在了第一位。
在续班期,辅导老师如果没有达到业绩,就算已经报名教资考试也不允许请假参加;向家长推课的时间,辅导老师只能打电话,不能给学生答疑。为了完成KPI,辅导老师向家长承诺有提分、放解题“大招”,甚至道德绑架,常用话术是“别让你的犹豫耽误孩子进步”。
即便是在“双减”落下的前后,夜里依然有辅导老师留在公司给学生讲题,他们也在调整话术,反复询问家长续课的意向——就像不知道将军的命令已下,还想再冲一把的士兵。一位家长当时接到电话,问对方“不是双减了嘛”,辅导老师叹了口气,挂了电话。
在辅导老师身上,可以看到情怀与商业的博弈。当情怀占上风时,辅导老师更像一位老师;当商业更被看重,辅导老师就成为销售。
亦有人对高途失望。
在“老奶奶”被点名批评之后。公司宣布整改,规范广告,减少信息流投放。但曾经负责师训的宋新发现,广告还在。内部有一个专门的广告词违禁库,成绩、考试相关的词汇都不能出现,相关部门会换着方法修改表述,比如把“提分”改成“怒涨300词”。“还是在钻政策的空子”,他认为公司并没有真正反思。
大愚基金经理、雪球上的认证用户“仓又加错”刘成岗认为,“国内在线教育公司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没有一家公司是利用了互联网,利用了科技,让教育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互联网跟科技只是用来作为获客的工具。”这些公司包括高途。在他看来,“Larry是随着时势去走的,他在这个行业里面没有做出颠覆性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一面讲情怀,一面又把课程价格定得那么高,收割的还是下沉市场的用户?”

▲ 高途公交站广告。图 / 视觉中国
“是伙伴是伙伴”8月下旬,CEO刘威“因为个人原因”离职。后来的员工大会上,陈向东说:“出乎我的意外(料)。”他说自己原本以为大家是依靠做教育的情怀走到一起。“他觉得自己看错了人。”刘小海说。
此时,陈向东也放弃了all in,甚至转向变成了in all。
“双减”之后,陈向东在高途Q2季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上表示,高途将加大投入已有的成人教育业务板块,比如财经、公职,同时拓展新的成人业务板块,例如考研和出国留学,并开始探索智能数字产品和职业教育。
如今,为了直播带货,MCN紧锣密鼓地做起来了,成人业务的素养课和编程课也有了眉目。由于之前裁员裁得太彻底,高途甚至有些缺人,不少部门正在重新招聘,或是让被裁的员工回流。——但显然,如今还看不到这家公司盈利的第二曲线。
现在的高途在北京只有一处办公地,文思海辉大厦的南边五层、北边两层。最近,一位仍在职的员工发现陈向东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成人业务在的那层办公区了,反而是中小学部的员工看见过他许多次。他认为,这是因为成人业务逐渐稳定下来,Larry更多要去操心变化更大的业务。
11月,在“营转非”的压力下,学而思和新东方宣布正式关闭K9业务。高途也紧跟着宣布,将停止K9业务——这是按照规定,每一个在线教育公司该做的事。
但对于陈向东而言,K9仍然要做的。他准备成立一个公司,在符合“营转非”政策要求的情况下申请牌照——在北京,35人以上的大班课每小时价格不能超过政府指导价,有人估算是50元——继续做K9的业务。陈向东相信,只要大班课人数够多,50元“这个价格一定是赚钱的”。
仔细分析过政策之后,陈向东甚至更加乐观了,跟主讲们单独开会的时候说这是“好事”,“巴不得这样”。他相信有了办许可证的要求,许多机构会退出市场,这意味着竞争对手变少,烧钱营销也不存在了。他觉得现在的情况恢复到了2018、2019年的样态,可以“回归教育的本质”。他的目标是,让高途的股价恢复到30美元,是2018年上坡时候的30美元,不是今年跌下来的30美元。
陈向东还是当年那个大佬,只是一年融资5000万美元刷新纪录的风头过了,参与制造的在线教育风口也过了。在各个会上,他评价那些曾经的同行者、在线教育前“大佬”们的努力,“哎呀,怎么能这么搞呢?”“啊,早知道我们也这么做了。”他说,自己不会放弃教育,除非退休。

▲ 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直播卖瓜助农。图 / 抖音截图
做教育是陈向东的梦想与坚持。就像他在农村长大,梦想在北京买大房子,再建一个游泳池。随着财富增长,他的梦想早已实现,但游泳池总是空着,陈向东的妈妈看不过去,说要填上种菜,他不同意。梦想总要实现的,但不一定一切都可以匹配,就像如今,游泳池没有种菜,荒在那里,陈向东至今也没有学会游泳。
离开高途时,汪四维反思了很久,他觉得公司发展太快了,有些“老人”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但实际上已经驾驭不了那个位置。“当一个公司从几个人到两万人,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他说。
有人感受到了变化。在2020年下半年,不少人已然懈怠,但增长可以掩盖很多问题。在全面滑落的当下,有些人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样子。“现在的高途,就是‘冰火两重天’。”走进办公区,可以一眼看出两种人和两种工作状态。有人经历了大起大落,极度悲观,每天在公司里无所事事,一位仍在职的员工觉得,“他们唯一还没离开高途的原因是出去不好找工作,在这里等着,说不定能等来N 1。另一批人还保持着在2017、2018年的那种工作激情”。
这位员工目前负责成人业务,今年的工资只是去年的一半,福利都被取消。他觉得自己在这家公司“经历了K12从单月一百万营收到两个亿的过程,现在正在经历成人业务从单月营收两三百万到一个亿的过程”。“第一次做起来可能是赶上了,如果第二次能做起来,那就是实力”。就像这家公司一样,他憋着一股劲儿,想要证明曾经走上巅峰的原因是实力而不是运气。
在放弃烧钱营销之后,高途正在重新做非标准化投放,一些只有一部分人能看到的广告,比如私域流量。还有一小撮人,如今被派去做最原始的投放——到各大学校门口发传单。
没人再谈论股价了,“都是伤心事,被套的同事太多了”,有人买了40万的股票,现在只剩下3万,他原本想买房,现在房子直接没了。
一个时代终于在迷茫中潦草地结束了。
回望前两年,在线教育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兴奋中,如今,影响超出了一个行业。高途、新东方、好未来股价狂跌时,中概股跟着一起跌。一位高途主讲老师手握公司期权,他的爱人攥着腾讯股票。“双减”那一天,一家人跌没了上百万。如今,高途的股价还在2美元左右徘徊,大盘的涨落在它身上,也不过是几十美分的变化而已。
迷茫的还有那些被裁掉的伙伴。他们的人生曾经被抛上高点,如今要继续适应高点之下的生活。小鱼曾以为找到新工作很容易,可在她休息的几个月里,新东方裁员4万,学而思线下155个教学点只剩下53个,字节教育开启了本年度第二轮大裁员,据媒体报道称,在12月将有近2000人被裁,其中有超过 1000 人来自瓜瓜龙、清北网校,精锐教育、学霸君暴雷……在线教育赛道里涌起的巨浪让数万人才流回了市场。直到现在,小鱼还没有找到新工作。
但高途的烙印还在,他们的生活曾经被真切地改变着。张淼离职之后跟曾经的兄弟们吃了顿饭,他们难免聊起过往,被一个人紧急制止,“如果聊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晚上谁都回不了家”。社交平台上,一个女孩在某个帖子下留言,讲述自己的经历,提到“以前都是将命注入的”,有人立刻回复她“是伙伴吗?”她答,“是伙伴是伙伴”。就像茫茫旷野上两头相遇的小兽,他们依靠气味和暗号识别出了彼此共同的身份。
林一彻底换了个赛道。即便如此,在9月面试时HR还是不经意间提起,最近来面试的人,十个里有八个是高途员工。他的新工作,薪水折半,但工作量超出想象得低,“一周的事情也就相当于高途一天的工作”。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6点,林一走出公司。在高途的几百个日夜,他没有看过一次夕阳,他曾跟同事开玩笑,“我们是星光下的赶路人”。
站在高途已经贴上封条的楼门口,林一看着北京的西边,太阳一点点沉下去,晚霞烧红了半边天,林一说,“离开高途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太阳是会落山的”。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实习生邹雨沁、周鑫雨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侵权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