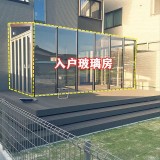余春娇
海德格尔曾用林间两棵毗邻却不相识的树,比拟诗与思想之间的亲缘关系。思想家为“存在”道说,神圣者将从澄明的“存在”中显露出来;而诗人道说神圣者。追溯海德格尔身上的诗哲品格,缘于他的一个句子:“一首诗的伟大正在于,它能够掩盖诗人这个人和诗人的名字。”它被烫金印在了书衣边缘,几乎也要掩盖了海德格尔作为诗人的名字。然而,它也为那些从作品中独立出来、像小行星般绕着作品本身运转的句子求了某种公正。

海德格尔 书衣
动人的句子应当被反复、以多样的形式讲述。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被帕特森写在便条上,获得了新的意义,当我们将它穿在身上,它暗示了普通生活掩盖下、令人怯于承认的诗人属性:
我吃了/冰箱/中的/李子 那也许/是你/为早餐/留下来的 原谅我/它们很可口/又甜/又凉。

威廉斯 T恤
人们的生活复杂,不断向前,句子是某个引起人们兴趣的、凝固的片刻。
佩索阿用仿日记的体裁写下了《惶然录》,在序言中假想了这部日记的作者“伯纳多·索阿雷斯”,这个人总是在“我”常去的那家餐馆观察周围的人,好像被他们所迷惑。他是一个公司的职员,令“我”惊讶的是他属于阅读“我”的作品的少部分人。序言最后“索阿雷斯”自称“没什么事情可干,没什么地方可去,没什么朋友可拜访,也没什么有趣的书可读。”他的人影于“我”的渐渐靠拢,直到每天晚餐后“总是回到租来的房间,用写作打发漫漫长夜”。他的形象完全重叠在了“我”的身上。“索阿雷斯”只是佩索阿异名者序列中的一个,毕竟佩索阿“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他说“我不知道我有多少灵魂”。我们倒是知道其中的72个。他们各有承担、彼此关联或互相评论,“我经过,我停驻,就像宇宙” 的“阿尔伯特·卡埃罗”就被“里卡多·雷耶斯”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落寞地生活,无名地死去。在神秘主义者看来,这是导师的特征。”

佩索阿 耳机套
出生于里斯本的费尔南多·佩索阿,除了随母亲去往南非,很少再去里斯本之外的地方。他生前只有一本葡语诗集出版,始终是位诗人,却从事着文书、会计相关的工作。据说和想象中的朋友通信,佩索阿在六岁时候(也是他父亲病逝不久)就开始了,这倒不算令人称奇,但他将身份裂变的习惯保持下去(且栽培起来)、也把孤独的习惯留了下来。

佩索阿 手机壳

佩索阿 卷尺
或许是这样,催生了“阿尔伯特·卡埃罗”“成为诗人不是我的野心,它只不过是我独处的方式”的自白。“阿尔瓦罗·德·冈波斯”写下的“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 令人顿感莫大的虚无,和由此蔑视起平庸丈量而产生的愉悦。或许也是同样的虚无,给了佩索阿同样的安慰,“在黑暗里,免于身后浩瀚的琐细”。

不可战胜的夏天 黄铜牌
身上不可战胜的夏天已和耸立的衣领一样,和加谬有了象征性的关系。加谬视西蒙娜·薇依为偶像,但不愿像她建议的那样竭力摆脱自己生命的重负,相反,“我要求并且得到的恰恰是某种生命之重负”。读年轻时的加谬更有一种紧迫感,他的字句透着热情和意志,不断鼓励“投入”,投入被动的激情,投入为所有人的反抗。“战斗”的主题将我们——尤其是年轻时的我们——暴露在他正午日晒般的感染力下,连手中的书纸都是烫的。

加缪 战斗便笺

加缪 战斗护书袋
十几年后,加缪自认为它们有些笨拙,同时有更多真实的爱。桑塔格当然会说读加谬能唤起爱。曾在贫穷与光明交织的世界中长期生活,加缪对光明有本能的忠诚,这种光明让人类学会在痛苦中也欢呼生命,因为热爱包容荒诞。“我总是被即将到来的事被今天或明天所吸引。”

加缪 帆布袋
在一个十二月,加缪到蒂巴萨的废墟旧地重游。十五年前,他“一整个上午都在废墟徜徉,闻苦艾的气味,靠着石头取暖,寻找小小的玫瑰花……入夜,睁着眼睛躺在繁星密布的天空下” 。那时,“我是在生活”。而现在,废墟被围上了铁丝网,夜间散步也被禁止。想要重获难以忘怀的自由不可能,想要重现爱过、享受过却骤然消失的面貌不可能。皱纹和创伤下,世界“一下子老了,我们也一样”。但因为是加缪,回忆不会只是供他凭吊的时间标本,回忆成为最后的依靠,这依靠也是火种,使他在不可逆的现实中免于绝望。“必须在自己身上保留一种新鲜和一股快乐的源泉”,投入战斗时,“必须怀着这种争来的光明”去战斗。 正是在此时,他明白了。“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加缪 书袋

加缪 手机壳
兰波写诗,像一连做了几年着魔的梦,固定下种种晕眩,所有人都尾随他、见证他梦中的奇观。他要创造一种进化的语言,“这种语言将从灵魂通达灵魂,概述一切,芳香、声音、色彩、思想与思想相互勾连,并引出思想。”《元音》的诞生就可能与这种想法有关,他为元音做了彩画。“我自以为以本能的节奏发明了一种诗性的语言。” 它终将通达所有感官,也只有兰波自己能翻译它,一旦这种不寻常的,被接纳成为正常的,他就完成了进步的繁殖:
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
终有一天我要道破你们隐秘的身世;
A,苍蝇身上的黑绒背心,
围绕着腐臭嗡嗡地不已;
阴暗的海湾;
E,汽船和乌篷的天真,
巍巍冰山的尖顶,白袍皇帝,伞形花的颤动;
I,殷红,咳出的鲜血,美人嗔怒
或频饮罚酒时朱唇上的笑容;
U,圆圈,青绿海水神圣的激荡,
散布牛羊的牧场的宁静,炼金术士
宽阔的额头上的智者的皱纹。
O,奇异而尖锐的末日号角,
穿越星球与天使的寂寥:
——噢,奥米茄眼里那紫色的柔光!

兰波 元音尺
然而,通灵要打乱所有感官、抵达不可知的痛苦。企图成为通灵诗人,就要尽可能地探索自己,尝尽所有形式的爱、痛苦和疯狂。即使真的抵达了不可知,他已是最伟大的病人、罪人和受诅咒者。兰波在一封书信中写道:“这样的痛苦令人生畏,但必须强大,必须是个天生的诗人,而我自以为是诗人。” 读兰波的年表,仿佛在一张复杂地图上追踪一簇跳动的谜团。他不停地出走、返回、再次出走。记录一个人某时在某地,竟然需要大量的证据。“有人见到他” “借阅图书卡”等推测拼凑出令人将信将疑的行踪。

明信片 魏尔伦给兰波的画像,以及兰波的情诗《感觉》手稿
在魏尔伦之后,兰波弃绝了诗人身份,开始了孤独、疲惫又不断重复的跋涉。他学会了钢琴、加入过军团、当了逃兵、跳槽了几间商行、牵着骆驼去卖武器,同时还可能给报纸写过一些蓄意杜撰的戏谑报导。偶尔也在家务农,通常是为了养病。他自知自己的堕落和睡意,面临健康的威胁和失语状态的恐惧,为国家不悦、为气候烦躁、为职业劳顿,为生活荒诞。虽说已与过去永别,剩下的十几年也像一场继续探索痛苦的漫长自我流放。“要么一切,要么全无”,他饯行了自己彻底的选择。

兰波 纪念套装明信片
句子无法代替阅读本身,但确实折射出阅读的力量。它们从各自的语境中来,带着普世的安慰:

海明威 裁纸刀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人尽可被毁灭, 但不可被打败。

狄更斯 帆布包
像牡蛎一样神秘,自给自足,而且孤独。
而独孤既然是作家的宿命,也是读者从阅读中求得的共情。毛姆对阅读本身的情结,给予了随身携带书籍的人们身份的认同和自足的陪伴:

毛姆 漫游者书袋
阅读是我们戒不掉的瘾。

毛姆 黄铜尺书签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
责任编辑:方晓燕
校对: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