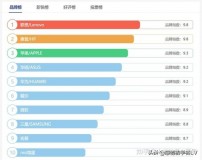澎湃新闻 湃客
眼光工作室
摄影并文 | 杜立安编辑 | 周双玲
提起三和人才市场,人们通常会想到那个由所谓“三和大神”定义的奇异之地。“三和大神”,开始于三和打工者的自我调侃,进而发酵于网络,成为三和的代名词。
本文作者为寻找典型而来,却发现那些人数更多的,更为典型的是驻留此地的底层劳动者们,然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无视和消音。以一具劳工的身体,更深入地观察这些劳工,他开始了自己的为期一周的“身体打卡”之旅。打卡第一站停靠在电子厂,以下是他作为一个流水线工人的自述。
▍日结:僧多粥少
八月份,在做了些准备之后,我(又)来到了深圳三和。
为了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扎眼,我在网上买了最便宜的黑色衬衣和黑胶鞋,翻出了从本科之后就再也没穿过的放了十年的牛仔裤。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感觉有了几分劳动者的样子,并对此次“身体打卡”之旅有了点信心。
为了保证重体力劳动后的休息,犹豫再三,我还是订了附近的酒店,没有像预想的露宿街头或者在网吧刷夜。
一夜安眠,次日清晨,我来到“海信大酒店”前的小广场,等着抢日结。早上五点一刻,天还没亮,这里已经人群聚集,在昏暗晃动的灯光中低语着。间或下着小雨,人群躲进两旁的屋檐下,黑沉而拥挤。即使是这样的天气,工头和中介也很快如期而至。

首先出现的是给工地招人的,直着嗓子喊了几声“工地杂工!”,也不说多少钱,具体干什么工作。但这无关紧要,很快就有一堆人围了上去,递上身份证作为干活的凭证。没几分钟就收了厚厚一摞,大约三十多张。
“人够了,走了走了。”工头喊了几声,带着一队人马离去。
没有应聘的人群则开始在旁边议论这份工作的各种细节,有做过的人说他们工作太重,钱少不值得。而旁边一堆人也附和,下雨了,在工地上干个毛。不一会,又来了一个满脸戾气的打着伞的黑衣人。当人群围上去询问时,他板着脸不耐烦地说:“不要不要,我只要熟人。后面大把招工的。你们等着去。”拨开人群,他似乎看到跟着自己做过工的人,便指着一边对他们说:到那边等我。
这波招工最终只有寥寥数人。“够了够了。走吧。”他们也迅速地乘车离去。没找到工作的人们不满于他的态度,纷纷嗤之以鼻:“他就是要卖菊花的。”
屋檐下的人群越来越多,有点超现实的味道。大家都在说着下雨不好干了,来招人的也少。零星出现的几个工头很快就招够了人离开,围观者也随之一哄而散。“挂逼喽,挂逼喽。”周围的人都在喊。
突然,有两个人发生了口角,甚至快打起来了。一个说要挂逼了,给多少钱都做,另一个人不干了,说三和大神要有原则,不能卖命。于是两人在起哄人群的围观下直着嗓子对骂。
事实上,工价的确低得发指。普遍是在一天一百出头的价格,即使那些最重的体力活,也都没有什么超过两百块钱的工作。即便这样,大部分的工头也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招到工,而务工者们则几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可能性。
我在一旁听着,思考着到底去应征什么工作,但往往是一犹豫,工头就招够人并离开了。僧多粥少,好的工作根本抢不到,不好的也不缺应征者。
逐渐地,天亮起来。广场上仍然还剩着几百个没找到工作的人。卖西瓜的来了,周围的人群开始陆续散开,或者坐在墙边发呆。
▍现在,我真的是个流水线工人了
在第一波工地招工的人消失之后,逐渐开始有些奇怪的工作机会出现了。
先是来了个招挖沟工人的,说要挖三米深的沟,一天一百八。招献血浆的也出现了,白胖中介用嘲讽的语气喊着献成分血不累钱多,有三百块钱,下午就能回来。还有人招往六楼搬床的,说有八十张床,不管多长时间,搬完就给三百。甚至还有帮人换驾驶证的,说是去代体检,不用干活,但只有四十块。
这些招工者都是收身份证走人。我拿着身份证走来走去,一脸焦虑。快七点的时候,我终于下定决心抓住机会,找到一份在电子厂流水线上螺丝的工作。
深圳的工厂实际上都不是很远,分散在从深圳湾到龙岗、龙华一带附近。我们这些在各个招工集散地的日结工们被工头雇来的小巴运往各个工厂。七点四十,我和另外十几位工友们挤在一辆拆除了座位的小车里如沙丁鱼般被送到了电子工厂。
透过贴黑的车窗向外看去,这一路似乎都在宽阔而熙攘的街道上穿行,从未离开过城市的范围。

我们目的工厂在一个工业园区的二楼,到达时还没到八点半的上班时间,于是我们全都蹲坐在楼下等待开工,目睹着穿着工服的正式工们陆续谈笑着走进厂房——此刻距离我起床找工作已经三个多小时了。
八点半,列队,训话,干活。我被分配在一条流水线开始的岗位上,这意味着若非手脚麻利,我将影响到整条生产线的效率。
手头的工作比想象中还简单:上紧三颗螺钉,把电线固定在转接盒里。从上到下依次是蓝线、黄线和棕线。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经过几分钟熟悉就能不过脑子地做,毫无技术含量:毕竟是给日结工做的活,需要随时上手,同时也随时能够被替换。
在我干活之前,已经有人在这里干了一整夜了。我之前一班是个妹子,明显疲惫而无精打采。在领班的要求下,她没好气地教了我一遍如何使用紧螺丝的电动起,如何连接三条线:“蓝线,黄线,咖啡色的线,顺序不能错,错了要返工。”
我试着做了一个给她看,她说:“电线往里太深了,现在压着胶皮,没压着芯,重做。”第二次做时我便掌握了关窍,她看了看没说什么,和领班打了个招呼扬长而去。
接下来便是十几个小时工作的开始,在几次简短的尝试后,我很快进入了加速的工作状态。

工作本身真的很简单,简单到整个流程没有太多可以推敲和优化的地方:要接的三条线中,黄线是根独立的短线,而蓝线和棕线则是连接在一块集成电路板上。我在台面上排开五个接线盒,先上黄线,再依次蓝线和棕线,然后拉拉看有没有紧,便把它放在旁边的纸板上,十二个作一版,进入流水线的下一级。黄线,蓝线,棕线,拉拉,放一边。我就这样机械地做下去。
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还暗暗想着自己的身份,并为成功的“混进”工人阶级队伍而暗自窃喜。在这种轻微错位中,我似乎有着某种表演感,并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分裂感:身体上在机械重复而加速,脑海中则在想着自己这次打工试图处理的问题,想着那些理论框架,比如布迪厄的象征资本和由此而来的区分,或者这段时间正在读的朗西埃对于无产阶级感性的判断。
然而这样的状态却没持续多久,我的脑子很快就因为手上单调重复动作而进入了放空状态。
“象征资本包括着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蓝线,哎我好像接错了,得把黄线退出来……趣味实际上是结构性的身份区隔……啊呀接线盒不够用了,刚才她说多余的放在哪里来着?……政治是使不可见者变得可见,是制造无分者之分……工头又来了,他怎么在旁边看着我?是我太慢了吗?哎呀怎么插不进去,要被骂了吗……”
很快,那些来自布迪厄和朗西埃的片段便被三条电线彻底打败了,而脑子里便只剩下三种颜色的线和白色的小接线盒,并时不时被消耗光的材料打个岔,而在补充后又继续重复这个过程。黄线,蓝线,棕线,拉拉,放一边。现在,我真的是个流水线工人了。
▍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才一个小时?),我才开始能够再注意到周围的事情和人。

用余光瞟瞟,正对面是一位穿红色衣服的小伙,他和我做着同样的活。左前方是流水线下一级的大姐,她把我们做好的原件组装到一个白色盒子里去,给到我左边的大叔,他需要为盒子上四个螺丝,然后放在旁边的传送带上,进入流水线的再下一级。
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充斥了我的脑海:我们做的是什么呢?说它是灯的一部分而又有点不像,难道是某种烟雾报警器吗?
我边想着,边重复着手上的活计,边感受着某种与劳动相分离的无产阶级化的真实处境:我们已经不再理解自己的劳动,并和这个劳动的结果相分离,只是在操作一个黑箱,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由一个具体的人化约为一个抽象的以时间计的劳动力。
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此刻似乎变成了我生命的某种终极问题,我想忍住不问,看能否从蛛丝马迹中判断出来,但却只能寻得各种似是而非的东西。
终于忍不住,我和对面的工友搭讪,结果他也不知道。不知什么时候,一位衣着靓丽戴着耳环的小厂妹替代了旁边的大叔,我搭讪问她,咱们做的是什么呀?她燦然一笑,说“xx灯。”
隔着工厂风扇和传送带的巨大噪声,我没听清,便回问“什么?高压灯吗?”“蓝牙灯。”我终于听清了,而这个答案似乎又什么都不是,只是把我丢回到之前的重复劳动中去。
▍加速,加速,加速
日渐当午,我手心和身上开始出汗。于是再多解开一颗纽扣。当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在做的事情上之后,我发现拧螺丝的活计并不容易。因为是一字螺丝,电起子需要以一个平行于螺口的角度进入,但拧完螺丝后的起子头却总是一个随机的角度,无法直接对准螺口,从而每次都需要调整一个不同的角度才能顺利进行下去。这种细微的偏差被时间逐渐放大,让我精神紧张而焦躁。

同时被放大的还有我身体上原本微不足道的感觉。紧张的背部变得更加紧张而至于痉挛,腰椎似乎开始承受不了我上半身的重量开始刺痛,尤其是左手大拇指和食指尖:由于需要用来扶住电路板,它们被电路板的轻微起伏磨损而开始红肿。
这些小的细节伴随着不断重复的肉体单调动作将我推到了某种特殊的紧张状态之中,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加速,加速,加速,似乎想要在将这种动作推到极限处而冲破牢笼。
每个在流水线中的人都在进行着类似的加速运动,整条流水线便越来越快地运转起来。并不存在什么极限之处,仿佛这种加速是一个自动完成的指令,身处其中的肉体在这样的结构中被规训,被刨除思考和行动的可能,只剩下一个不断重复而加速的动作。
时间变得无限缓慢,注意力则被扩张到整个身体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消费已经变得具有了某种注意力经济的特征,生产端也伴随着类似改变。如何占据时间,如何更有效率地占据内在于肉体的时间并将之用于生产,是这个系统的要求。
▍120块,这是我赚得最困难的一笔钱
十二点,午休铃声响起。流水线轰然而止。所有人放下手中做了一半的活计,没有丝毫不舍。

下午,一个半小时的午休后,我们继续回到流水线工作。时间开始缓慢地持续着。我盼着今天的十二小时工作迅速结束,但每次看表时它却只是过了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这种煎熬让我想起了曾经的军训——从对身体的规训角度而言,此二者的确有着共同的来源。
终于,晚上十点半,下工的铃声响起。我迅速停下手中的活计,此刻已经毫无念想甚至毫无感觉,只是一片空白和空虚感。
从早上不到5点起床,到此刻已经过了十七个半小时。最终,当我拿到了今天工作所得的一百二十块钱时,突然意识到,这是我迄今赚到的最困难的一笔钱。
本期见习编辑 周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