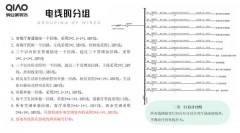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音乐人柳爽创作的歌曲《漠河舞厅》近来很火。它以1987年漠河火灾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凄怆的爱情故事,打动了许多人。但这场火灾给人们留下的远不止于此。2019年,澎湃新闻记者曾探访大兴安岭森林中的着火点,拜访了森林消防支队、护林员及防火办等,还去参观了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以下即为当时刊发的“以何救火”中的漠河部分。

2017年,东北大兴安岭,一处常见的游乐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森林消防队伍的沿革,可追溯到1987年5月6日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些信息。大火刚起时,5月7日的电报文字说:“部队上300人,一定要强调安全,要有地方人作向导,因为部队勇敢,但缺少扑火知识。”
不过,在长达28天的连续扑救中,冲在一线的还是大量军人。仅森林警察,就有3000余名官兵奋战28个昼夜,转战54个火场,扑灭火线1200余公里,点烧隔离带322公里。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消防支队漠河大队十四中队荣誉室中的一张照片。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批示:“森林警察在扑火中,起到了尖兵和突击队作用,森林警察确实非常必要。”此役成为森林部队发展史上重要转折点。
在这场举世震惊的森林大火中,宫凤岐是前去支援的内蒙古森林警察部队的一员。漠河火灾后,被烧成麻花状的铁轨、结成冰溜子的玻璃窗,这些场景令他难以释怀。现在,他在深圳从事森林消防工作,带队扑火时刻要求队员“注意安全”。
我们观摩了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消防支队漠河大队十四中队指战员们扑打火线的演习。热浪卷着烟袭来,要靠近打火,就得用面罩遮挡;黑灰纷纷扬扬,掉在我们的羽绒服上,烧出几个小洞。我这才真切意识到,火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打火为何需要听指挥进行战术排布,实战时如何以火灭火,风力灭火器等要带的装备究竟多重,蓄水池、帐篷等要如何搭建,炊事员又是如何在山上做饭。


十多年来,宫凤岐没再去过东北,只记得那些硕大的树。大兴安岭地势平坦,常见树种格外易燃。参与过大兴安岭打火的打火队员说,这里烧起来便是火烧连营。
顺着他们的话,可以想像:林子里本来无风,一粒火星掉在干燥的蒲公英上,点燃熊熊的烟与风,风助火势,火壮风威,伴随着火车汽笛般的响声,小火球成片地从山上滚下来,热浪和林子一起翻滚。
最先发现着火的,可能是附近巡逻的护林员。在我去到的东北大兴安岭林区,护林员要看护山林里的野生动植物,防止有人盗猎,并每天撰写日志。防火更是重要工作。
秋季的大兴安岭满眼是斑斓而深沉的大树和灌木,风刮过松枝,窸窣作响。除了松鼠、飞鸟和虫蚁,少见其他活物。直到山货成熟时,才有人进山采集。这时已是防火季。大兴安岭一年都要防火,只在冬季稍许放松。

前哨林场的一处管护站。
我们看到,护林员把家安在山路边,方便骑上助动车,按几条固定路线巡逻。他们的家就是管护站。一个站长加上七个成员,管一万零两百零三公顷的林地。管护站对“入山不带火”负责。入山人员和车辆要登记,严禁带火种入山。红色储水桶摆在岗哨边,写着“防火专用”。旁边架着五条二号工具。按规定,站长负责唯一的“一盒火”。护林员若发现有人吸烟,要没收火种,发现火情更要及时报告。
大兴安岭林区,最高的设施大概是防火瞭望塔。这意味着一份全职工作。漠河市有39座24米高的防火瞭望塔,分布在70余万公顷的大山中,所处海拔800-1200米不等。每座瞭望塔有两名瞭望员,3月防火期上山,直到11月初大雪封山时才下山。按规定,他们需轮流上塔值班,每一两个小时向林业局防火办汇报是否有火情。如发现烟点,要观察和测量,然后马上报告。

漠河地区的瞭望塔。
带我去寻访瞭望塔的,是漠河市防火办的工作人员。瞭望塔在深山之中,车子从山路岔道处开到林里,我们下车走了十五分钟,才见到瞭望员的小屋。想来,路口并无特殊标记,周边树木看起来都差不多,我诧异于司机竟能找到准确路线。
这里少有人来。瞭望员见到我们,十分亲切。这间砖砌的小屋只够一两个人住,偶尔有家属探亲。厨房与卧室连通,旱厕在屋外。二号工具、钉耙(防火耙)、铲子(防火锹)、防火镐、三齿子,都在院里的工具架上。这是生活所需,也是规定配置。

瞭望员的住处。
可能是考虑温差,窗户用塑料布代替玻璃。房里堆着干粮和油。墙上挂了外套、水壶和做菜吃的蘑菇。虽然地里种了一些菜,但食物还是需要被送上山。蔬菜主要是豆角番茄,更容易储存。北地往往饮酒取暖,但这份工作日常禁酒,免得误事。同行的工作人员带了些豆皮和鸭腿等熟食,算是难得的美味。
房里贴了各级森林防火规定,条款密密麻麻。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我跟着瞭望员上塔。钢架微微发颤,越往上,离地越远,振幅越大,便越发想念坚实的地面。上到顶端,呆上几个小时,期间汇报林里的状况,再与另一人轮换,这是每日值班的任务。他们说,冬天金属会结冰打滑,要格外小心。上面的棚厦并不保暖。

瞭望塔上。

瞭望塔中。
秋日光影映出塔台通体斑驳。金属骨架遍布红色的锈。无论瞭望塔的塔名、塔呼号,还是所在施业区,经纬度坐标,全部讲求数字和源头追溯,否则无法精确防范该区域的突发风险。
虽然信息技术发达,漠河已用上了可监测烟点的设备,但人力仍不可或缺。防火办工作人员说,机器可能误报漏报,而此事万不能疏漏。要防范森林火灾,还需两厢结合。
在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讲解员马景春与打火队员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五·六大火的两个起火点。其中一处树了石碑,另一处并无标记。对此熟悉的人,才知道这些地点的所在。

五·六火灾起火点纪念碑。
马景春指给我们看发黑的树桩。只见烧黑的木头横在地上,上面附着泥巴、枯枝与青苔。当年,一个肇事者在此吸烟,不慎点燃树枝。原本大家以为已经扑灭,但又不幸复燃,延烧为满城的惨剧。
在满是针叶松的林地里,这一处与那一处似乎并无不同。经历过大火的城市早已焕然一新,而这里只有无人打扰的、日积月累的时间。

林地上烧过的树木,已长出苔藓。
由于工作原因,马景春常带着参观者来到起火点,讲述自己经历过的火海。1987年5月,马景春只有14岁。她说,漠河不大,左右都是亲戚邻居。前一天还与自己打羽毛球的女孩,最终没能逃出火海,在家中蜷缩成一团,差点被饿肚子的人当做狗吃掉。真是令闻者落泪的人间惨剧。

过火后的漠河县城。

2019年的漠河县城。
作为讲解员,在馆内烧红的天、泛灰的地之间,马景春一再向人讲述,那些亲朋好友是如何身故,每次讲起便会动情。她说,讲述这些灰暗和惨痛,对自己是种排解;而更多人听到这些,多少懂得求生方法,可避免惨剧再现。她还自学了心理学,在反复沉浸于悲剧之时,也可保全内心的健康。或许,这就是事件对人的淬练。
整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从大兴安岭的地理状况讲起,讲到当初的火魔降临,后来的军民抗灾,再到日后的灾后重建,还有如今以森林资源发展旅游、推广特产的愿景。其中可见的资料,包括当年的新闻联播视频、电报文件、历史照片,都一一作了整理和陈列。馆内甚至制作了模拟火灾场景的环幕影像。
不过,作为一名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我无法不留意到,以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为写作对象、被视为中国灾难报道里程碑的那组被称作“三色报道”的稿子——《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在纪念馆内全无踪迹。
这组报道因没有把灾难变成颂歌,并为公众贡献了火灾完整过程的叙述,从而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我所在的新闻学院的老师对我说,是因当年读过“三色报道”,才对记者这一行燃起理想主义的向往,继而报考新闻学院。而我采访的参与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支援的军人,在总结当年教训时,也对我说到:当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领导懒政,工作落实不到位,同时也有装备落后的问题。他的这些话,也佐证着“三色报道”的意义。

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中的警句。
那些直指弊病的文字,与扑火救灾的精神一道,留在了一代人的心里。这是火所烧不尽的。
我又想到那两个起火点。防火人人有责。因自身疏忽留下火星,最终化为燎原之火,个体责任无可推卸。但一场大火蔓延成灾,内中必定有诸多不得力之处,仅记下肇事者的责任,可能有失公允。倘若对此缺乏公正书写,也对不住那些理应被称颂的火场军民英雄。

防火第一是林区人的共识。漠河一处洗车店门口,挂着标语。
人们之所以组织起来,成为社会、国家,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抵抗风险。在哪怕是小概率的潜在灾难面前,人们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组织完善、信息通达的基础上。这正是“三色报道”的出发点,也是它能够影响一代人、至今仍在新闻学院课堂上被提起的重要原因。
漠河以前有很多松树,1987年森林大火之后,成片白桦取而代之。因为后者长得更快,生命力强。从漠河机场到市区的路上,一排排耀眼的白桦,正是火后长起。而漠河则变成一座新城,几乎看不出原先的样子。大量的房子是火后援建的。纪念馆附近的松苑公园,是幸免于火的一片丛林。不远处便是县政府、图书馆等公共设施。人们或许会感叹,老百姓的活力生生不息,各方人道主义援助起了重要作用,国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员能力更是极其强大。

过火后的漠河县城,剩下一小片树林。

2019年的漠河县城,小树林被辟为松苑公园。
但关于社会、自然与人的记录,仍然较为稀缺。走访东北、东南和西南这三个区域的五个省份后,我们讲述了以上这些故事,希望让人不光意识到防火要从我做起,也能更明白森林火灾是怎么回事,相关管理者和从业者是怎样的面貌,又存在哪些现实的需求和困难。
正如那三句话所说,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
责任编辑:吴英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