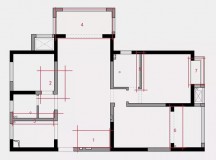《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 夏晓虹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戊戌之后的女学氛围
在近代妇女史上,对女性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新式女子教育。今天学者一般将1898年创建的“中国女学会书塾”(又称“中国女学堂”、“经正女学”)视为国人自办的社会化女子教育的起点。作为维新运动的产物,“中国女学会书塾”亦因政治斗争而终:1900年,经元善通电反对“己亥立储”,遭清廷通缉,逃亡海外,女学堂主事无人,只得关闭。此后新式女学的命运,成为晚清士人关注女性问题时的重点。
可以确定的是,新式女子教育并没有随昙花一现的“中国女学会书塾”而终止。经元善在1902年的演说中便引用佛偈,对此前提倡、主持女学的同道予以“播种者”的身份追认,认为当年是“下第一粒粟之萌芽”,对后来者的跟进,他非常乐观。而此年《大公报》对女学堂在南方四处开花的描绘,更让人兴奋:“南方通商口岸,自上海开通女学后,经莲珊太守首倡捐建女学堂之议,自是而苏而浙、而无锡、而武昌相继踵起,又膨月张而至于湘粤。女子无不发愤自强,日以讲学为事。”现今碍于所见,文中提到的各女学堂之情状已难考索。

目前可知的在“中国女学会书塾”之后、“癸卯学制”颁行前创办的女学,较著名的有兰陵女学(苏州,1901)、严氏女塾(天津,1902)、务本女学(上海,1902)、爱国女学(上海,1902)、城东女学(上海,1903)、宗孟女学(上海,1903)、湖南第一女学堂(长沙,1903)等,多由士绅自发自为倡建。民间有志兴学而持观望态度者当不在少数,则此时政府上层对于女学堂之态度至为重要。而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女学堂的普及情况对全国也具有表率意义。
慈禧与“毓坤会”
1902年的北京,仅有教会女校贝满女学堂、长老会女校、慕贞女书院,并无自办女学堂。当年曾有满族官员禀请庆亲王奕劻设立八旗女学堂,“庆邸然之。后以见阻于八旗各都统,遂罢是议”。这是我所见到的关于国人在北京自办女学的最早报导。今天看来,北京风气远不如南方开化,京中官员反需借上海出版的《女报》来改变其对“开女智、兴女学”的成见。
也是在同一年,《大公报》刊登热心读者的白话来稿,建议自上而下推广女学:太后先在宫中创设女学堂,再明降谕旨,令京中王公大臣、各省文武官员,每家设立女学。不出五年,风气必然大开,女学堂遍及全国。在此文中,最让我留意的是对宫廷女学堂的设想:
皇太后先在宫里,立一座女学堂,考选几位中国女教习。也不必炫异矜奇,只要通文识字、举止安详的,就算合格。皇太后、皇后,也不必言定入学,就求随时振作鼓励着点,那风气自然就开的快了。宫里的宫娥秀女,共有若干名,开一个清册,分为几班,除去当差侍奉的时候,得工夫就按班入学。
就晚清女子教育的实践来看,地方开明士绅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因而此文对兴女学路径的想象显得不合实际。不过,作者将推广女学的起点定位于慈禧太后,也并非全无因由。就现在能看到的材料而言,慈禧对女报、女学等时新潮流,是以一个开明者的形象出现的。如《大公报》称由于京官转呈,慈禧在宫中能够读到在上海出版的陈撷芬主编的《女报》(1903年更名为《女学报》)。再加上其自身的性别因素,很容易被设想成为新式女子教育的赞助者、推动者。而《女学报》透露出来的消息,确实可以坐实这种猜想:
太后为轸念中国女学之不振,乃将平日所览之《女报》,谕令大公主等各阅一分,并有设立女学堂意,命大公主主其事。俟新建之大学堂工竣,即以现在马神庙公主府之大学堂作为女学堂。八旗中有志入学者,准来堂肄习。此事原因,实由去年日本内田公使夫人力陈东洋女学之兴,故有感慈意云。
报导中的公使夫人即日本驻华大使内田康哉妻子内田政子,与慈禧关系亲密。1902年8月17日日本《报知新闻》曾称:“今日在北京政界而生擒西太后者谁乎?内田夫人也。”大约1902年慈禧在接见内田政子时,对方谈及日本女学之盛,引起了慈禧对于国内女学蔽锢的感触,因而有意在京城兴建女学堂,收录八旗女子入学,追步日本女学。而在同年,慈禧亦同意了湖北巡抚端方的开女学堂之请,“有饬令鄂省试办之说”。这当是次年开办的湖北幼稚园附设女学堂的最早缘起。
至1903年,京城里已经有了朝廷即将兴办女学堂的传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曾经回忆,当年内务府大臣诚璋出面请服部宇之吉起草兴女学计划。此举很可能是出于慈禧的旨意。因为涉及到从日本聘请女教师的问题,这一计划并未马上实施。而在近代女子教育史上,于京师大学堂校址上创建女学堂的设想并无下文,此处很可能是慈禧心血来潮的冲动。不过,步武日本女学的意趣和视恭亲王奕䜣长女荣寿公主(即报导中的“大公主”)为女学主事人的安排,已然为后来的“贵胄女学堂”之提议埋下了伏笔。
所谓“贵胄女学堂”,指由皇公贵族开办,对女性亲属、族裔或秀女、婢女实施教育的学校。宫廷或皇室内的女子教育古已有之,如班昭就曾入宫担任过后妃的教师,又如宋若昭被唐穆宗封为“尚宫”,“后妃与诸王、主率以师礼见”。
但皇室创办较大规模的学校推行女子教育,在晚清之前未见记载。进入20世纪后,在“兴女学”潮流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创办的毓正女学堂与肃亲王善耆创办的和育女学堂。毓正女学堂于1903年12月开办,1909年停办。由于地处僻远,其影响基本仅限于蒙古地区。而据服部宇之吉主编的《北京志》,和育女学堂于1905年开办。奇怪的是,京城内外的报刊似乎都忽视了该校的存在,就我所见,对此竟无任何记载。彼时被多家报刊跟踪报导的皇族女学,唯有1905年起倡建的“贵胄女学堂”。而此前倡议的“毓坤会”,则可看作是“贵胄女学堂”兴起的先声。

1904年10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宫廷将设毓坤总学会的消息:
皇太后命裕朗西之女公子在三海中择一处开设毓坤文会,并准在外设立分会一节,已见他报。兹据内侍传说,该文会设在中海,名为“毓坤总学会”,每日讲习浅近文法及各国语言文字。凡王公大臣之福晋、夫人及五品以上之命妇、女子均准入总学会听讲。其分会则官绅商民之妇女,凡身家清白,不论已学未学,均可入会听讲云云。果尔,则女学之兴盛当不远也。
1904年初颁行的“癸卯学制”中,唯《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稍带提及女子教育,但态度十分保守,认为“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其意“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
《大公报》消息中的“毓坤文会”虽然是学会名义,有人也认为其“仅仅研究语言文字,以备赐宴各国公使夫人之时为之通译,似于立会之宗旨,犹未窥见其大者也”,但实质显然是皇族女学,放在其时其地,已算难能可贵。消息详细记载了学会创办人、开设地点、授课内容、学员资格,这都暗示出毓坤文会开办在即。在“总会”之外设立“分会”、允许民籍妇女入学的设想,显示出主办者的宏大气魄。如能以慈禧为首自上而下地推广女学,北京女界的沉寂现状又何愁不能打破?《大公报》难掩兴奋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稍后,上海的《时报》对“毓坤会”的消息进行了后续报导,云:
探闻近日皇太后因从裕朗西京卿之女公子奏请,拟在南海之内创设女学,赐名毓坤会。凡王公贝勒之福晋、格格,及京员三品以上之命妇、女子均着报名入会,学习东西文。已奉懿旨,特派裕女公子经理其事云。
毓坤会主办者和授课内容均没变动,唯有开办地点已具体选定了“三海”(南海、北海、中海)中的南海,汉族女性的入学门槛也由“五品命妇”提升至“三品命妇”。课程中开设“各国语言文字”,大异于传统宫廷女学,颇具有现代意味,其实是与主办者的个人趣味有关。1903年的《大公报》称,“裕朗西之女公子,颇得皇太后欢心,不时入内,二人皆衣洋装”。二人即是容菱(1882-1973)和德菱(1886-1944),通英、法语,曾在清宫中担任翻译,颇为慈禧宠爱。而且,在议设毓坤会后不久,容菱、德菱及其母亲又拟设八旗女学,“专收旗民幼女,以期培植女才”。以德菱姊妹主持毓坤会,可谓无二之选。
就在北京女界和报界翘首期盼中,毓坤会却迟迟未见下文。直到次年初,据《警钟日报》透露出来的消息,毓坤会之所以停滞不前,乃是因为慈禧对女学的看法出现了变化:
湖南革命狱始兴,学界骤为之暗;上海谋刺案继起,政界大为之惊。京师则尤甚,有无关系者均视作密切问题。俄使更番警告,联派党咸有戒心。连日枢府与管学大臣互谒密商,颇耸观德[听]。各学堂学生骄态锐减,有失其常度者。星期出游,亦甚寥寥。西后因学堂迭现怪象,意滋不悦。前拟设毓坤会兴女学,亦中止矣。
消息中所涉先后事件,指1903年春开始兴起的“拒俄运动”、1904年秋冬在长沙流产的华兴会起义以及当年11月上海发生的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前两事,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学生都充当了中坚力量,因而清政府对在校学生的日常活动极为警惕,极易产生过度反应。再加上近臣对当前男女学堂的大小“流弊”的渲染,动摇了慈禧对于女学的热忱,毓坤会之事也就意兴阑珊了。
1905年5月《大公报》又有“毓坤会”的消息,但记者语气已经十分犹疑,在按语中言,“上年即有此等传说,究竟不知确否”。事实上,德菱在两月前赴上海照看病重的父亲,离开了清宫。从此在《大公报》上,再无毓坤会的消息。
“贵胄女学堂”考详
创设毓坤会的倡议就此消歇,但慈禧对女学堂的兴趣不久之后又再度高涨,此时不能不提的人物即是端方。1905年7月,端方被任命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在逗留北京期间,利用面见“慈圣”谢恩的机会,端方大力强调女学堂的重要性,颇得慈禧称允。在致湖北女学生的电报中,他提到自己曾四次晋谒慈禧,“即女学亦经面奏,慈圣亦以为然”。
在两人的会面中,端方可能还提及皇族女学之事。《大公报》的社论透露,端方“力陈以兴办华族女学校为要”,虽然“群疑众谤”,但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慈圣于此事垂注尤殷,将由内廷拨款,以为天下倡”。稍后的《顺天时报》也记载,慈禧对端方之奏请“极为垂意,已饬内务府筹拨经费若干,以为开办华族女学校之用”。
此华族女学校并未立即兴办,但不久后慈禧授意,“特准将西山旃檀寺改为女学,无论华族编闾皆可就学”。此旨一出,令民间有志入学的女性倍感鼓舞,“太后于今立意,要想倡兴女学,正是要使我们中国人要人人发愤,人人好学”。
1905年12月10日晚,《南方报》记者从北京发来电报,称“两宫面谕庆邸(按:即庆亲王奕劻),仿贵胄学堂例筹办皇族女学”。可见皇族女学之筹设,前有端方之意见,近则有陆军贵胄学堂之激刺。慈禧要求仿办女学,显有示教育平等之意。而《大公报》1906年初的报导则更加详细:
闻内廷人云,日前召见军机大臣时,两宫垂询贵胄学堂规模,催饬赶紧开办。并云外洋重女学,而中国此等风气未开,拟俟贵胄学堂办有成效,再设皇族女学堂,专收王公府第郡主、格格入学肄习,以期输入文明,咸知爱国等谕云云。
消息中“专收王公府第郡主、格格”的学员标准,正与毓坤会一脉相承。另据直隶《教育杂志》转录《津报》的消息,参与筹办皇族女学的尚有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夫人、荣寿公主及陆伯英侍郎之夫人等。而消息所用“贵胄女学堂”的名字,最终为该学堂定名。

在此后关于皇室女学的报道中,慈禧太后一直是最有力的推动者。她在召见学部官员时,便难掩迫切之情:
闻学部尚书曾于日前面奉懿旨,以中国女学尚未发达,亟宜设法推广,以期家庭教育日渐讲求云云。故华族女学之章程近又复提议也。
此条消息中提及的女学名称——“华族女学”,较前文中的“皇族女学”略有不同。事实上,“华族女学”即为日本皇室女学之名。1885年11月从日本“学习院”独立出来的华族女学校,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久即成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女子学校,“日本女学校,当以此为翘楚”。华族女学校因此成为中国朝野考察日本教育时必不可少的去处,其学监下田歌子也成为中国女子教育界的知名人物。清宫倡议皇室女学而拟以“华族女学”名之,可能寓有向其取镜之意。
更值得关注的是慈禧对端方考察女学报告的反应。1905年12月,端方与戴鸿慈一行出洋考察宪政时,慈禧即命其考察东西洋各国女学,随时报告。途中学部又奉旨再次电谕其考察女学。1906年4月,《顺天时报》有报道,称:“闻日前端、戴二大臣来有电奏,系陈明美国女学校之章程及一切内容,最为完备,中国女学亟宜仿行。两宫览奏,颇为欣悦。现已拨内帑十万两,派肃邸之姊葆淑舫夫人先行组织师范女学一所。”
此消息被多次转载,影响颇大。《申报》读者即乐观地预想此举之效应:“登高而呼,众山皆应。女界光明之发现,将普照于中国全境。”联系到此前关于皇族女学的报导,在一般读者看来,慈禧的慷慨很可能是因皇族女学而发。如徐锡麟在写给党人的信中,提及“皇太后现捐银十万,开贵胄女学堂”,作为其在满洲人中“可谓通晓时务者”的证据。
次月,庆亲王奕劻也有“贵胄女学堂”之奏请,“以便饬令各王府之郡君、格格及满汉二、三品各大员之女子入学肄业”。而最重要的契机则来自考察宪政归来的端方。据夏晓虹先生考证,1906年8月13日,慈禧单独召见归国不久的端方。端方在召对时,肯定有关于女学数事,因为据几天后《大公报》报道:“考政大臣端午帅于前日面奏两宫,请饬学部速立女学堂章程规则,兴办女学,以开风气。闻已奉旨饬学部妥拟一切矣。”
趁此次朝见机会,端方很可能还递呈了一份重要奏折——《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这份由梁启超捉刀的奏章,其中心议题是:“于京师设立中央女学院,以开全国之风气,而为各省之模范。”该办法想必与慈禧此前对于皇族女学的提倡一拍即合,因此很快宫廷中即有“贵胄女学”的消息传出:
闻学部人云:本部近日会议设立贵胄女学,所有一切章程均仿照日本华族女学,量为增减。并闻此事之发起,庆邸、泽公及午帅均极赞成,不日当可具折奏请。
前本报纪端午帅奏请举办女学一事,业与荣大军机商议一切规则,名为贵胄女学堂,其学生以三品以上之大员幼女为合格云。
经过商议,端方与荣庆最终将其命名为“贵胄女学堂”。以源远流长的“贵胄”一词代替“皇族”和“华族”为皇室女学定名,既对应了已经开办的“陆军贵胄学堂”,也与日本的“华族女学校”区别开来。关于学生资格,“三品以上之大员幼女”的规定则与前次开设未成之“毓坤会”遥相呼应。
虽然端方对于美国的女学颇有好感,但比较日本和欧美各国的女学情形之后,议设中的贵胄女学堂还是预备借鉴日本的华族女学校。日本华族女学校规模宏大,学制健全,为“天皇及王公大臣,凡华族之女子肄业之所。分为初等小学、高高[等]小学、初等中学、高等中学,凡四科,各三年,以一年为一级,满六岁以上、十八岁以下者得入学。”
作为楷模的华族女学校,为拟想中的贵胄女学堂铺设了美好的前景。而据端方在9月30日外城女学传习所开学典礼上的演讲透露:“皇太后屡次询及女学,拟开办一高等之学堂。诸生在此毕业后,即可升入,为皇太后门生,何等体面!”言辞中的“高等女学堂”,因其学生是“皇太后门生”,很可能即指将来的贵胄女学堂——也就是说,预设中的贵胄女学堂除了提供初等教育之外,还会为皇族及平民女子开设高等教育,可见此时慈禧对贵胄女学堂所寄期望之深切。
虽然在朝廷内有慈禧太后、庆亲王奕劻和学部尚书荣庆的支持,在地方有端方等大员的倡议,贵胄女学堂的成立却并不顺利。最先遇到的阻力,即来自湖广总督张之洞。1907年初,他即致电学部,表明他对兴办女学的谨慎态度:“张香帅热心学务,人所公认。独于女学雅不谓然,以为中国人民程度尚低,此时倡兴女学,未免稍早。闻于日前有电达学部,详陈此时兴办女学之流弊。未知枢密诸公亦表同情否?”张之洞电文并未直接针对声势渐涨的贵胄女学堂,但作为朝廷重臣,其意见不容忽视,此番议论对贵胄女学堂的影响也近乎立竿见影:
闻内廷人云:两宫每于召见学部堂官时,必垂询推广女学办法,实注意设立贵胄女学之举。近因某督臣奏陈女学之弊,是以犹疑。日前荣尚书召见时,两宫与之讨论良久,谕以中国风气尚未大开,欲兴女学,必须先订完善章程,然后再行试办,逐渐推广。事宜缓而不宜急,以昭慎重。是以开办贵胄女学之说已从缓议。
在1906年学部成立之前,张之洞对新式教育相当积极,是倡导改造传统教育、肯定和推广新式教育的前驱与重镇,但在科举停废后,面对新、旧学乾坤颠倒的时事,他的办学方略的主导倾向也从倡行新学转而为旧学卫道。对于创兴女学堂之事,此前的《南方报》称其“素不注意”。不久之后,慈禧接见某位贤王,问及女学章程和官立女学时,“皇太后黯然不答,恐有不满意于女学”。
贵胄女学暂缓兴办,可能是慈禧因为张之洞等人的反对而出现了动摇,或是因为朝野舆论而做出的策略性让步。好在女学堂章程奏定已于时不远——3月2日,《大公报》登载女学章程“业经议妥,将于开印后入奏”。六天之后,《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颁布实施。而在同一天,《大公报》上刊载的消息,令关心贵胄女学堂的读者欣喜不已:
贵胄女学堂事,政府已会同学部妥议,约于春间即可开办。闻荣寿公主已面奉皇太后慈旨,充当贵胄女学堂总监督。
1904年的癸卯学制中,女学“流弊甚多,断不相宜”,而此时则认为“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基”,“欲求贤母,须有完全之女学”,贵胄女学堂的兴办自是名正言顺。
被慈禧指派为总监督的荣寿公主是恭亲王奕䜣长女,幼年颇得咸丰皇帝喜爱,与志端婚后五年即守寡,长侍于慈禧身边,“恭谨持正,终身得太后之宠,有时进谏,太后亦多采纳之”。有趣的是,类似于容菱、德菱姊妹,荣寿公主对英文亦有兴趣。但其任贵胄女学堂总监督一职并未成为定议。不久之后,《申报》刊载消息,透露此事引起了北洋亲贵袁世凯的注意,而他密保推荐的人选,则是京津女界中享有大名的吕碧城。袁氏认为吕“才优品卓,堪充贵胄女学堂总办之选”。
吕碧城荣膺贵胄女学堂监督之职的最大资本,不为才华出众,而是她主持北洋女子公学的经历。北洋女子公学成立于1904年初冬,吕碧城为创始人之一,并主持全校教务。1907年夏,日本国民新闻社社长德富苏峰参观天津公立女学堂时,曾对吕碧城大加赞扬。北京报界则称其为“近日女界中独一无二的名家”。而且北洋女子公学的学生大多为官宦闺秀,与筹议中的贵胄女学堂性质相似,吕氏自己就曾认为女子公学“有日本华族女学之概”,时人也将其比于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袁世凯对吕碧城的推重,自然不足为奇。
本文选自《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中的《“贵胄女学堂”与晚清北京女子教育》一文,文章作者为黄湘金,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黄湘金
摘编丨何也
编辑丨青青子
导语校对丨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