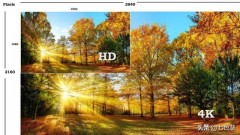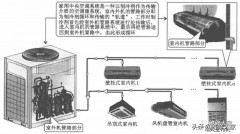孔德罡
因新冠疫情推迟到2021年10月上映的007系列第25部正传《无暇赴死》,既是第六任“詹姆斯·邦德”丹尼尔·克雷格的谢幕之作,更算是提前庆祝“007系列”的六十年庆。一个甲子的时间,本身就意味着这个大众商业电影系列的延续性和生命力是惊人的:从1962年的《诺博士》算起,近60年来历经六任邦德,25部大投资大制作并收获高票房的电影(不含两部外传),“007号詹姆斯·邦德”这一英国特工的经典形象始终经久不衰。这一在流行文化领域的辉煌成就,自带古典主义式的“经典性”,甚至超越时代:在以速朽、瞬间为特色的现代性文化商品橱窗,有一个角色不仅能“名声大噪十五分钟”,能拍到25部并且还将继续拍下去,能将角色寿命拉长到半个世纪直指百年,俨然保留着某种“永恒”的特质:007系列毫无疑问是现代神话学领域中的不可多得的奇迹。

《无暇赴死》海报
这是文学的胜利吗?至少不是原著作者伊恩·弗莱明的胜利。作为冷战时期非常著名,但也比比皆是,毫无出众之处的流行间谍小说,弗莱明的原著在文学价值上基本属于看完就忘、感官刺激的范畴,哪怕007电影再火也没有听说弗莱明的原著被热捧为经典文学。
可是,这好像也不是电影艺术的胜利。最早拍摄《诺博士》的制片方,似乎没有想过他们将开启一个延续近60年的伟大电影系列,大概只是存着把大众流行小说改成一部好卖的商业电影赚笔快钱的心思。相较于后来饰演邦德的演员所拥有的崇高江湖地位,后来凭借艺术片领域的成就驰名的首任邦德肖恩·康纳利,一段时间内甚至把演邦德这种“B级片”当作纯粹养家糊口的手段,演了五年就心生退意,心想“正经演员不该拍这种东西”。
007系列拍了这么多年,一直到第六任邦德丹尼尔·克雷格时期,在导演萨姆·门德斯的改造下,才好像有了一丝“艺术片追求”;历史上的007系列,就是无脑商业电影、视觉炸弹、感官刺激的代名词:弱智的正邪对抗剧情(永恒的苏联反派),每部必换、彻底物化为性感符号的邦女郎,各种前沿高端间谍科技,枪战,爆炸,大场面,007最终得胜的永恒英雄主义——你可以说,商业电影吸引观众的方式数十年来一贯如此,可如果哪怕《星球大战》这样的伟大系列都限制在三部曲的框架下,《哈利·波特》这样伴随一代人的电影连续剧也在第八部完结,如何解释观众偏偏对007这一个系列和一个人物,几十年拍了25部却依然毫无厌倦?“詹姆斯·邦德”究竟有什么独特的,无可取代的魔力?
詹姆斯·邦德不是一个角色,是代表“最好”的符号
其实,上世纪下半叶流行文化和波普艺术给美学带来的最大启示恐怕是:哪怕所指无比空虚孱弱,能指武器也绝非不堪一击。007系列是现代神话的重要范本:因为也许说到底,人们对“007”的迷恋完全可以剥离开对文本、对电影能指的期待和感受,只关注被不断加深的符号印象,只关注先验的、已然不可更改的惯例,直到在50年庆典时,英国人自发身着正装、宛若出席歌剧现场般去看《天幕坠落》的首映——60年来的詹姆斯·邦德的存在,完全是一种社会习惯,一个被不断的能指运作所加强并彻底固化的“风俗”:这种风俗对时间的抗击能力,能够穿越一切阻碍;所指看起来已然破碎,但能指自我生产繁殖的力量,崇高而颠扑不破。

《天幕坠落》剧照
25部邦德电影,观众究竟记得了哪些东西?当然不会是每一部的剧情:和很多商业电影系列不同的是,007系列好像并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性的粉丝群体,真正看完25部电影并对情节人物如数家珍的粉丝基本难寻,粉丝群体内部常见的“x学”“lore研究”对邦德系列来说并不存在,007系列面向的基本就是听说过邦德大名的路人观众。这很难怪罪粉丝们:作为前后情节基本无涉,没有延续性,角色不存在成长性的“单元剧”,每部007电影的具体剧情如何真的重要吗?不仅英美观众都很少看过全系列,从八九十年代才开始接触到007系列中国观众,在电视屏幕上甚至连邦德的“迭代”都体验不到,电视台基本是无视系列顺序随便乱放的,作为“单元剧”它们彼此独立,演员走马灯乱换,反正是“铁金刚占士邦”就行。
况且,在弗莱明的原著小说被改编完毕后,007系列的剧情很早就处于“没有原著,编剧硬写”的阶段了,尤其到第三任邦德罗杰·摩尔时期,007系列的剧本写作流水线生产、重复性堪比罐头的问题已经开始危及系列存续了,可不仅演员、制片方不在乎,大多数观众也只是在乎这次007又去了哪里,找了什么样的新邦女郎,用了什么新的高科技武器——至少在丹尼尔·克雷格之前,没有人从“人物塑造”的角度在乎詹姆斯·邦德这个角色。
这大概是个“反文学史”的颠覆性现象:观众为什么会如此热爱一个根本没什么人物塑造的“工具人”角色?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观众热爱的,恰好就是“詹姆斯·邦德”这个名字,这个符号,以及他背后所意味的一切。邦德不是肖恩·康纳利,不是罗杰·摩尔,哪怕是乔治·拉赞贝也没什么问题,丹尼尔·克雷格一头金发长得像普京最终也能满堂彩,只要他叫做詹姆斯·邦德,他身后所有的符号运作能够成立,那么所有的存在就能成立:因为詹姆斯·邦德的符号化形象并非是黑发、苏格兰血统、海军出身、绅士风度这些弗莱明和康纳利一起创造的“初始人设”,而是:大英帝国、战无不胜、风度翩翩的特工,仅此而已。
邦德是个筐,是个英国人,是个有绅士风度的冷战英雄,然后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弗莱明原著本身角色塑造的孱弱(包括邦德的苏格兰血统,都是因为康纳利出演而临时修改的)和早期007电影毫无掩饰的商业B级片不考虑艺术的属性,赋予了邦德形象一个无比空泛,但因此发挥空间极大,无比自由的能指操演区域。可是,这么空泛而不具体的人物形象,难道不会被细化的市场需求所击溃吗?然而仿佛天命所归似的,007正是大银幕上涌现的第一个英国特工,并从此以非凡的商业成功和资本运作垄断了“英国特工”形象的解释权——邦德既是“先来”的,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还是最具有包容性,最有发挥空间的:事实证明,“有容乃大”的詹姆斯·邦德,让所有英国乃至美国的间谍电影长时间内都无路可走,直到丹尼尔·克雷格自己走出了细化的新路。
一个产品占据先发优势,并且拥有垄断的权力:双层加持之下,“詹姆斯·邦德”与人们对英美阵营乃至整个“自由世界”阵营的特工英雄的印象直接画上了等号——当这个符号足够包容和宏大,就意味着他的自我生产和增殖能力是无限的,邦德就是英伦绅士、当代男性英雄的同义词,因此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摆脱文本的人设限制,纵情拥抱时代变迁:60年来六任邦德不追求延续性和“相像”,因时代审美流变而带来的不同,赋予观众的只有“新意”所带来的刺激。各任邦德在西装穿搭、手表品味、座驾、饮酒选择、恋爱观念、度假地区乃至一切“男士”的生活方式和品味上,都成为时代的先驱和引领者。
由此,邦德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永恒时尚符号。没有人能说清邦德具体是什么样的:但他一定是观众对男性的审美印象中,那个“最好”的。而“最好”的,自然是永恒的。
英国人的性格:当“伪传统”被强化为“习俗”
根据能指符号的操演原理,既然“邦德”的所指在不断流变甚至通往虚空,他的人设本质上是空无的,只是人们对“最好的英伦男性英雄”的一种期盼,这样的符号操演则面临一种本体论危机:即“为什么一定是你?”如果邦德仅仅意味着“最好的英国特工”,那么是不是任何一部拍摄的比007系列好的英美特工片,就可以取代邦德“最好”的地位了呢?因此,尽管邦德的“所指”(人物形象)可以随意改变,但同时还需要“能指”对邦德的符号地位做出不断强化——即运用各种“先验”的,“从来就是如此”的,不经意间的现代神话学手段,潜移默化地让观众对之前产生的“等号”(邦德=最好的英伦男性英雄)进行持续的心理重复,直至成为思想钢印。

《诺博士》中的詹姆斯·邦德
很难说是一种自觉还是巧合,六十年来的007系列电影单从外观上,就拥有任何一个商业电影系列都难以企及的,堪称登峰造极的对自我特征的强大延续性,令哪怕是再路人的观众,都可以迅速地、轻而易举地分辨出“这是部007电影”:第一部《诺博士》中那些本来仅是为制作单部电影而做出的不少“能指”(外观)设计,都被一种可能来自英国人性格内核中的“尊重习俗与传统”的本性所延续下来,25部邦德电影都严格地遵循从第一部《诺博士》开始的某些传统,这也是很多影迷都如数家珍的细节发现:因为我们很难在其他商业电影系列中,找到如此坚韧、能够延续近60年,25部电影少有例外的“传统”和“情怀”,以至于,它们彻底成为了一种不能被打破的“习惯”与“风俗”。比如:
五个圆形图案转化为镜头内的詹姆斯·邦德,他走进画面,突然转身朝你开枪,接着画面被鲜血覆盖:要么在开头,要么放片尾,这一枪不开,观众甚至都不承认这是007电影;
电影片名出来后,必须伴随完整的主题歌和演职人员名单,画面则配上电脑设计的,以女性黑色剪影为主要视觉符号的动画,25部绝无例外(除了《俄罗斯之恋》配的是主题音乐,主题歌因为剧情需要放在片尾),007系列如今甚至是唯一将完整的主题歌放在正片中的商业电影系列,每部电影开头的演职员名单动画,甚至已经成为每个时代平面设计审美和成就的最高展示殿堂,无一不是教科书级别的经典;
《诺博士》中大放异彩的音乐主题《The James Bond Theme》不仅在25部电影中都被沿用,成为世人皆知的音乐符号,而更令人惊叹的是,《The James Bond Theme》的主旋律动机,三个音符“G,#G,A”,甚至成为邦德系列电影的“音乐DNA”,之后每部电影的主题歌都是基于这一动机写作的,这导致大家熟悉的《Skyfall》《Writing’s on the Wall》《The World is not Enough》《Another Way to Die》,包括此次“碧梨”创作演唱的《No Time to Die》,不仅都是制作精良,代表当时欧美歌坛最高水准的经典单曲,更因为主动机的存在,“一听就知道是007”——相比于某些续作都不愿意使用前作经典配乐的“系列”,007系列的音乐延续性如至化境。

007电影片头
尽管反派、邦女郎都在变,但邦德的团队:上司M,技术助手Q博士和对接工作的军情六处秘书钱班霓小姐(Moneypenny)三个角色始终陪在邦德身边;其中M历经伯纳德·李、朱迪·丹奇再到拉尔夫·费因斯,已成为英国演员“国宝”的地位代号;历次参演007的英国演员也都藏龙卧虎,007系列电影甚至有“英国春晚”的名声。
至于像每次邦德点酒都会说的“Martini, Shaken, not stirred”,每部影片结束时会显示的“James Bond will return”,时不时呼应前作的豪车座驾、经典剧情等类似的小细节,一两次还可以被称为是“情怀”“小心思”,一旦贯穿25部,则就成为难以割舍的“传统”和“习俗”,是007系列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平心而论,类似邦德转身开枪来介绍角色,主题歌配动画MV放在电影片头等习惯,都是60、70年代英美商业电影的惯例,是为了时刻提醒观众作品的系列属性,其实并不稀奇;但007系列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在80年代之后,英美商业电影拍摄风格和包装方式都产生转变的时代潮流下,尽管接受好莱坞投资成为美国电影,007系列却一直坚守英国人骨子里尤其重视的对“传统”的尊重和延续,将无条件的“复古”做到极致——哪怕007系列中这些“传统”其实也不过是1962年拍摄《诺博士》时随意为之,是并没有多少深意的“伪传统”,很多也看似无关紧要,不影响电影的具体内容,而且这些传统(比如五个圆圈的古早平面设计、数码时代早期简陋的剪影动画、将两三分钟的主题歌插入节奏和时长都很紧张的正片)其实也并不一定符合当今观众的观影习惯,但60年、25部电影始终将这些“能指”传统延续下来的行为本身,在当今续作都不一定和前作有什么关系的商业电影范畴内,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以至于,能指的肆虐已然为其争夺到了相对的独立性,现在的观众看完一部007电影,可能也并不记得剧情和人物,但一定记得开场邦德开枪的动作,记得主题歌和动画场景,记得《The James Bond Theme》的经典动机,并且期待下一部007电影中继续看到这些——这样的观众为数众多;他们可能并没有真的喜欢或者看得进去007电影,但他们知道,他们在看007,而“007”的特色是一眼便知的——B站一些收集25部的邦德开枪画面、主题歌MV的视频点击量,超过一部分007电影正片。
在这些数十年来被不断的能指运作所加强并彻底固化的“风俗”下,“邦德”等于“最好的英伦男性英雄”的符号操演,创造了无可争议的007神话。大多数007系列电影也许在艺术质量上只不过是流水线生产的粗劣工业品,但它先验地被带到观众面前,自带一个“世界”的逻辑,进行无限的“自我致敬”,随着时间的流逝,借助“传统”和“习俗”的力量,垄断并统治了观众的认知,超越时代的考验,终成不可磨灭的流行文化图腾——随之而然的,它也终将成为这种符号神话和流行文化的一曲挽歌。
萨姆·门德斯是升华了,还是毁掉了007系列?
2002年,系列第20部《择日而亡》上映,第五任邦德皮尔斯·布鲁斯南卸任。布鲁斯南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完美的邦德诠释者之一,代表着传统邦德形象,以及007电影作为纯粹的商业电影这一定位所能达到的巅峰——面对已经解体不再能够提供反派的苏联,面对以《谍影重重》为代表的更加真实、冷冽、现代的特工电影潮流,面对观众对纯粹爆米花商业电影的厌倦,四十年来长盛不衰的007系列,似乎第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或者说,至少在制片方和创作者们看来,到了需要变革的时候。

《择日而亡》海报
其实,变革一定是必须的吗?之前提到的对于邦德电影传奇性的符号运作失效了吗?并没有。《择日而亡》依旧大卖,谁是新任007依然是电影界的头号话题,邀请导演第一部布鲁斯南版007的马丁·坎贝尔回归导演的丹尼尔·克雷格第一部邦德电影《皇家赌场》,延续了“改变邦德形象但延续007电影传统风格”的路线,依旧大获成功——人们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人设上和原著以及前任几位詹姆斯·邦德“不能说一模一样,至少是毫无关系”的新邦德,毕竟冷酷不苟言笑、肌肉健硕出手凶狠,风格凛冽不花里胡哨,正是21世纪对“最好”的男性英雄形象的全新需要;而抛开丹尼尔·克雷格的全新演绎,《皇家赌场》依然是一部味道不能再纯正了的007电影,至今广受观众欢迎和怀念。
然而,从《量子危机》开始,以英国导演萨姆·门德斯开始掌镜007系列为高潮,邦德系列电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自我革新:“单元剧”的剧情形式被彻底抛弃,丹尼尔·克雷格的五部007电影是一个完整的个人传记故事——因此,剧本深入到詹姆斯·邦德的内心,这个本身是虚无的大英帝国男性英雄特工符号形象,开始被不断“人化”,被赋予来自过去的伤痛和情感,被赋予了不再虚无,非常具体,却也开始失去“共性”的独特人设:丹尼尔·克雷格某种意义上,是第一个“扮演”了詹姆斯·邦德这一“人物”的演员。

《量子危机》海报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萨姆·门德斯的作者情怀加持下,007系列那些传统的能指表达,被精良的制作水准所“高雅”化,在摄影、音乐、动画等技术部门的协助下,门德斯赋予了007电影前所未有的艺术电影氛围和歌剧般的华美气质,从《天幕坠落》开始,第23-25部的邦德电影无论从影像质感还是艺术审美上,质量都比前面22部高出一截——007系列似乎第一次走向“深刻”,走向真正意义的艺术性——有得必有失,这三部007电影节奏缓慢,内心戏和文戏比重较大,纯粹的视觉和感官刺激大幅度减少,“粗糙”的,不修边幅的邦德也不再代表前沿的男性时尚形象,甚至连战斗时的“科技含量”也降低了:《天幕坠落》结尾邦德与反派在天幕庄园的决战,虽然在情感和气氛调动上堪称系列经典,但论其战术和武器技术含量,被戏称为“小鬼当家”,片子似乎不够“商业”,“不够好看”了。
然而这些变革都只是表面功夫(哪怕是对邦德人物形象的认真塑造),萨姆·门德斯真正意义上对007系列的颠覆和改造在于,他在试图维护“邦德”与“最好的英伦男性英雄”之间的等号的时候,采取的不是“先验”地“不言而喻”,而是真诚却又力不从心的“证明”。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詹姆斯·邦德也并不是神通广大的,并非一开始就是完美的英伦男性英雄范本,而和其他普通的角色一样,需要成长,犯过错误,经过历练,越过心魔,才能够达到完美——尽管所有观众都认可丹尼尔·克雷格对角色的诠释做到了这种“完美”,但实际上,单是这样的“证明过程”的存在,即意味着对007系列前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先验”式等号的不信任:本来,“邦德是最好的”是根本不需要证明的事情,而一旦我们需要证明“邦德是最好的”,无论丹尼尔·克雷格证明得多么好,这都说明:那个延续了几十年的对007形象的符号能指运作,开始动摇了。当我们为《天幕坠落》流泪,意识到詹姆斯·邦德这个角色第一次是“感动”而不是“帅”到我们的时候,邦德“无需自证”的神话也就破灭了;门德斯试图维护这个等号的努力,其实是彻底毁掉了这个等号。
而这能怪萨姆·门德斯吗?当然不能。因为尽管《皇家赌场》也很成功,但我们都知道这可能是暂时的,是数十年来邦德传奇的余晖,能有门德斯这样的导演主动进行改革实乃系列之幸——因为这个能指运作的最基本前提,也就是能够让这一“先验判断”、这一“等号”成立的前提,在于“英国=最好的”。当大英帝国的辉煌随着时代变迁风吹雨打去的时候,其实真正要证明自己的是詹姆斯·邦德吗?是丹尼尔·克雷格塑造的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吗?不,真正要证明自己的,是大英帝国自己。
旧时光,新时代。过时的再辉煌也该退出,但却值得一个㶷烂而体面的离开。萨姆·门德斯的《天幕坠落》,只是在说一个这样的故事。邦德们过时了,这曾经的一切都过时了,间谍行动,军情六处,快意恩仇,大英帝国曾经的傲慢与荣光,都在无数不可挽回的灾难中化作尘埃。《天幕坠落》实际上就是一场体面的离开,一曲带着微笑的挽歌,就像朱迪·丹奇饰演的M朗诵丁尼生的《尤利西斯》那样,他们有高贵的骄傲,有不羁的内心,懂得坚持,懂得固守,哪怕在外人看来如此顽固,无可救药。《天幕坠落》丝毫不是邦德电影,相反的,在气质上近似于《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近似于约翰·勒卡雷的冷战间谍哀歌。
曾经说过“我绝对不会去导演007电影”的萨姆·门德斯,抓住了007系列电影最本质的内在矛盾:与时代的现实矛盾。他借助对一个“人化”的邦德自我证明的过程的内心书写,彻底从时代性上,从现实主义范畴升华了007系列电影的内核,007电影第一次如此切近时代,切近人心,成为帝国永恒的墓志铭——大英帝国的落日余晖已然越发黯淡,黯淡到连区区邦德电影诞生的五十年,都显得如此遥远如此漫长。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门德斯固然在邦德系列的五十年庆上,祭出了历史上最为深刻的一部007电影,却也釜底抽薪,因为其刻骨的现实主义关切,彻底毁掉了007系列的地基。难道大英帝国是在2012年《天幕坠落》上映时才衰落的吗?难道1962年《诺博士》上映时,大英帝国还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吗?不,邦德系列电影的能指运作一开始就和现实无关,它从一开始就想更积极浪漫地,大男子主义、少年感地,而不是勒卡雷式现实主义地来展现间谍传奇,它是一场在意识形态优势庇护之下的空想与幻梦,它是电影“造梦”本质的情感抒发,它本身就是大英帝国对现实、对时代哀怨的不屈服或者说“自欺”;而门德斯的“升华”,一方面将007纳入到严肃艺术的轨道,一方面却又让其面对“出生”时的不义和荒谬,最后彻底无法自处。

《幽灵党》海报
在堪称伟大的《天幕坠落》之后,门德斯本人继续导演的《幽灵党》,和延续制作思路、审美依旧卓绝的《无暇赴死》,显然都不如人意。《幽灵党》在《天幕坠落》创造的盛大落幕后试图“重启”邦德故事,粗劣地再次回到模仿《皇家赌场》式老邦德电影的路线,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叙事矛盾和美学冲突;而《无暇赴死》作为丹尼尔·克雷格的谢幕之作,又成了《天幕坠落》的拙劣复制,把《天幕坠落》对大英帝国的挽歌又老调重弹地唱了一遍,这样的东施效颦,连把邦德这个角色写死,都无法再调动起观众心头的任何涟漪——
而也许对这个系列来说更加迷茫的事情是,那个即将到来的第七任邦德,未来可以看到的新007电影,将如何面对《天幕坠落》对经典的邦德神话所撕开的这道血淋淋的伤口?新的邦德会无视、能够无视这些吗?新的邦德会重新制造“邦德=最好的英伦男性英雄”的幻梦吗?在知晓了真相之后,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都还能够回到曾经的晶莹泡沫之中吗?
朱迪·丹奇的M,丹尼尔·克雷格的邦德,可尽最后残存的所有力量去缅怀,去追忆,去回归,为了最后体面和绚烂的终结,然后坦然承认年岁已变,时代穿梭,隐退在后,那么未来的M,未来的邦德,未来的军情六处,未来的007电影,未来的大英帝国呢?他们还可以像丁尼生《尤利西斯》笔下所写的那样吗?甚至,哪怕他们可以勉力做到,但是他们不再“毫不费力”的样貌,是否就意味着邦德神话的彻底破灭呢?
詹姆斯·邦德和007系列的下一个十年,我满怀悲伤地抱有疑虑。
We are not now that strength which in old days
虽然我们的力量已不如当初
Moved earth and heaven; that which we are, we are;
已远非昔日移天动地的雄姿
One equal temper of heroic hearts,
但我们仍是我们,英雄的心
Made weak by time and fate, but strong in will
尽管被时间消磨,被命运削弱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奋斗、探索、寻求,而不屈服
——丁尼生《尤利西斯》,《天幕坠落》中M台词中引用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