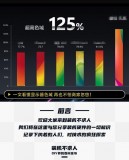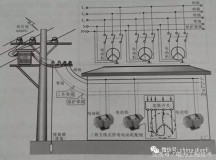长沙纺织厂原名经华纱厂,1912年由湖南都督府参议吴作霖创设,始为官商合办,厂址在长沙银盆岭。1913年改为湖南第一纺织厂。1933年达到鼎盛时期,仅这一年就生产棉纱2.7万件。
抗战爆发后,湖南第一纺织厂迁至安江,继续生产。
抗战胜利后,1948年,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在银盆岭原湖南第一纺织厂旧址复厂,第二年元旦正式投产,改名为裕湘纱厂。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裕湘纱厂被长沙市政府接收,更名国营长沙纺织厂。
新中国成立后,长沙纺织厂分别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和“双轨制”时代。至1990年,工厂进入鼎盛期。也就是这一年,师范毕业的刘婷进了长沙纺织厂,做了一名挡车工。这次她来跟我们聊聊在长沙纺织厂工作的青春过往。

◀刘婷画的裕湘纱厂(曾是长沙纺织厂)大门。
进厂就是正式工,我为此感到骄傲
1990年,我师范毕业进入长沙纺织厂。因为我是师范生,又带有国营指标,所以是由副厂长亲自带我去车间报到的。我进厂就是正式工,与我同一批进厂的小姐妹都是临时工,她们需要经过考核才有可能转为正式工。几十年过去了,这依然是我骄傲的地方。副厂长当时为了让我安心工作,介绍说:车间有空调,冬暖夏凉。正式工作后才知道他的话是骗人的,哪里是空调!不过是用风管,将防空洞里的冷气,输送到车间。
纺织厂的工作是三班倒,机器不停人不停。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年轻人瞌睡大,做晚夜班时,双眼皮直打架。老工人就告诉我们,把原料装到机器上,估算好时间,这个中间就可以躲进装废棉花的车里睡觉。我们偷偷去睡觉时,整个车间不见人影,只剩下纺织机的轰鸣声。当我们躲在暖暖的棉花车里睡得迷迷瞪瞪时,常常会被工长揪出来。
有时候,我们为了逃避繁重的劳动,就装病,跑到厂职工医院开病假条,不是每次都能得逞。装得像的,跟医生关系好的,就能开到病假条。职工医院是我们偷懒的避风港。
我们青工也有愉快的时候。
那时很多电影和电视剧,都喜欢在我们厂里取景拍摄,还在我们纺织工人里挑选群众演员。被选中去做群众演员的,一个个开心死了,因为既可以在荧幕露脸,还能领到剧组发放的劳务费。没有被选中,也不会失落。我们常常利用中午四十五分钟的吃饭时间,一大帮年轻纺织女工,人手一个饭盒,围观影视剧拍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拍摄,我记忆最为深刻,当时主要在北厂门拍摄。北门口有个百步台阶,直通湘江,是天然的江景亲水平台。白天,工作间隙看拍电视剧,到了夜晚,我们纺织女工一群群地坐在台阶上乘凉,伴着头顶的星星,听清波拍岸,享受晚风轻拂。

1966年,行驶于长沙纺织厂车间旁的公交车。 图/陈先枢
全厂职工被动员销售积压产品,很多人赚了钱
上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全市很多国营工厂出现产品积压现象,为了解决这种窘境,企业纷纷动员职工搞全员销售。长沙纺织厂也积压了很多内衣产品,也动员全厂职工参加销售,并出台了鼓励性质的规定。规定内容包括:去销货的,只要去仓库登记领的品种和数量,不要交钱就可以拿货;售价自定;领了货又没有销售出去的,只要产品整箱未开封,还可以退回长沙纺织厂;货销出去了的,只要按厂里定的价格将货款上交,剩下的归自己。
此招一出,职工积极参加。因为长沙纺织厂的产品质量可靠,不到一周存货就销售一空,参加了销售的人,都不同程度的发了一笔小财。那时我刚进厂不久,不熟悉情况,不敢贸然参加销售,错过了发财机会,今天说起来还十分后悔呢。
那时长沙纺织厂有一支时装模特队,在长沙市都非常有名。模特队由厂团委组织,成员都是我们一线挡车工。队员们身材好,气质佳,真是美女帅哥云集。长沙纺织厂经常与其他市州的纺织厂联合演出,出尽了风头。我作为时装模特队的主持人,多次代表长沙纺织厂参加省市演讲比赛,并多次荣获一等奖。与我搭档的男主持,后来调到了长沙电视台做主持人。
挡车工做久了,我有些倦怠。我就重拾读师范时练就的技能,在挡车工工作的间隙,承包了厂里的黑板报。黑板报的版式设计、美术装饰、板书都是我一个人。我希望我的黑板报,能得到领导们的认可,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逃离纺织机。
付出就会有回报。后来领导见到我有其他方面的才华,也知道我不安心于做挡车工,就把我调到机关实验室。实验室也是三班倒,日常工作需要打算盘,计算棉花实验结果,整合实验数据。那时整个社会已普及计算器,但我们依然还要求算盘计算,每周还要进行珠算比赛,搞得我每天晚上练珠算,练到深夜一点多。

刘婷:52岁,1990年进长沙纺织厂,先后任职挡车工、实验员,2018年退休。
厂后街是我们纺织工人的“堕落街”
婚后,我怀孕了,厂里安排我们从宿舍住进妈妈间。妈妈间有一线长长的走道,终年阴暗,更离谱的是房门和窗户全部是水泥结构。厚重的水泥门,推动时发出吱吱声。房间四面也是水泥原色,没有任何粉刷。我们青工都在走道做饭,日子虽然清苦,但一大帮年轻人住在一起,倒也快活。
晚饭后,我们经常结伴去厂后街潇洒。长沙纺织厂的厂后街是我们纺织工人的“堕落街”。这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街巷两边店铺全是卖各种小吃的,有甜酒冲蛋、葱油粑粑、荷兰粉、白粒圆、猪血汤、臭干子、卤猪脚、兰花干子。街上小店两人一桌的,那是小情侣;三五人一桌的,那是小聚的好朋友们。也有刚刚散工的纺织女工,她们还没有脱去工装,头戴白帽子,腰系围裙,十分容易识别。七八个人拼桌而坐,吃着小吃,喝着啤酒,一天的疲劳就在推杯换盏中丢到了九霄云外。
街角的桌球室,是年轻满哥快活的地方。他们光着膀子,玩兴正浓。有人进球了,对手总是高喊一句:你杆子蛮准啊!进球者高举球杆,对着排档食客高喊:来搞一盘噻。他们这么大声,不知道是说给男工友听呢,还是给我们女工友听。反正我们只是笑笑,懒得理他。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我从厂后街吃排档的女孩,变成退休老工人了。有空时,我常去家门口的被列为文物的长沙纺织厂老门楼转转。过往的青春记忆,与眼前的红男绿女重叠,那一刻,内心温暖,唯愿这盛世美景常在。
文/陈波
【来源:潇湘晨报】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