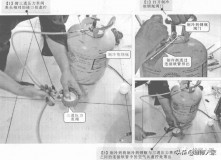【文/观察者网 马雪】
“刚入朝,我们没经验,一个女同志,炸碎了,在河沟里捞上来她两个辫子,姓戴,高中生,非常漂亮,我们的白毛女,第一炮就没了,辫子梢上都是碎肉。”
正在上映的抗美援朝老兵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开场便惊心动魄。
大荧幕上,26位平均年龄88岁的老战士,打开深埋的记忆,在你面前讲述他们的战火青春。

虽然豆瓣评分高达9.0,但受影片题材、类型、前期点映因疫情取消等因素影响,排片和上座率不佳。上映16天,票房仅有600多万。
影片导演宋坤儒在接受观察者网专访时表示,坚持院线的原因在于想保持他的执念——“他们必须得被仰视”。他说,压力不在票房,当初就跟所有片方拍了桌子,说这事90%会赔钱,也确实有片方退出。
“所有人看完都说好,然后没有人看。这事本身就特荒诞。它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电影,类似于《黑炮事件》。”
也有一些人质疑他,宋导演感慨,“我不明白现在有一些人是哪出了问题,为什么一提到英雄,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对。”

但与此同时,《1950他们正年轻》也成为继《二十二》之后,中国影史上又一部出现大量“自来水”的纪录电影。
很多观众通过打电话给影院、包场、赠票的方式希望更多人能去看,一些影院积极回应,后续排片也有所提升。
“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们的片子能有‘自来水’,我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们的片子要靠‘自来水’。能有这么多人来帮助,特别的感谢。”
宋导演说,“我们的目标是能扛一天是一天。哪怕全国就剩下100场,剩下10场,剩下一场,我们都得坚持。只要有场次开就会有人看,有人看就会有人帮我们传播。因为我们已经没子弹了,我们自己的子弹已经全打光了。”

“但凡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兵,身上全是故事”
观察者网:您能简单介绍下拍摄这部片子的缘起吗?
宋坤儒导演:2018年,我阴差阳错拍了一部跟老兵相关的公益广告,意外地认识了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转场聊天时,觉得他们说的话很有意思,跟史料、教科书上的宏大英雄故事不一样,都是非常细碎、特别打动人的小故事。
当时有个老兵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叫叶发坤,腰特别笔直,一头白发,带个金丝边的眼镜。实际拍摄的时候才发现,他没有双腿,膝盖以下全是假肢。一个带着假肢的人,努力把身体站得那么直,当时我就是心“砰”了一下。
第二天去他家,发现墙上挂了一张特别奇怪的照片。一个年轻战士,肩膀上有一只手,但旁边却没有人。叶老跟我们解释,旁边的人是他跟他关系最好的战友,上战场前俩人拍了张合影。但他战友牺牲了,他不想再看到战友的样子,就把照片折了过去。这个事又让我的内心“砰”了一下。

叶发坤家墙上的照片
当时也没想拍成电影。但有一天深夜,回家路上,突然想起这个老人把照片折叠过去的时候,我就在想,他究竟在想什么。那一刻,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的直觉,我觉得这些老人背后有故事。所以我就在想以后有没有机会可以采录一下他们的小故事。就是特单纯的一个想法,然后就这么干了。
观察者网:您在拍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宋坤儒导演:从大困难来说,第一肯定是时间。我们经常说我们这是“抢救式的采访”,有两层含义:一是抢救老人留下来的故事,另一个是我们要抢在时间夺走老人的记忆之前。有些老人他的生命还在延续,但记忆被夺走了。
还有个困难是,有一些老兵不会轻易跟你敞开他的心扉。伤痛也好,记忆也好,对每个人的内心留下的是不一样的。
比如“小北京”任红举,他本身是文艺兵出身,比较开朗,会用幽默、讲故事的方式来消解他的惨痛。他经历的故事非常惨烈,比如说大辫子……但他描述的时候还能保持一个清晰的思路。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记住啊,宋导演,但凡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兵,身上全是故事”。尤其像他们文艺兵,他不是在一个部队,文艺人才毕竟不多,要反复到不同的部队宣传演出,所以他经历和看到的故事比较多。上甘岭那个著名的孤胆英雄——胡修道(一级战斗英雄,上甘岭战役中带领战友共击退敌人40余次进攻、毙伤敌280余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任红举是第一个采访的。当时阵地上就剩了他一个人,17岁的任红举把胡修道背了下来,还根据胡修道的事迹写了山东快书《金星英雄》,演遍全军。

任红举,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31师文工团队员(图片由宋坤儒导演提供)
跟任爷爷聊了之后,颠覆了我的一些印象,我才知道文艺兵并不仅是唱唱跳跳。朝鲜战场上的文艺兵有三重身份,他们叫“大三元”。第一个就是本职工作——宣传员,将战地真人真事迅速改编成快板、口号、歌曲、独幕剧,演出给战士;第二,卫生员,要担负战场上的救护工作;第三更超乎我想象的是,他们还要肩负战斗任务,配枪,战斗惨烈的时候他们也要参战。
观察者网:刘素谦奶奶说“你来的正是好时候,来的再晚我可能就没有了”,片尾列表上有几位接受采访的老兵名字带上了白框,好像也有她?
宋坤儒导演:刘素谦奶奶是今年5月份离开我们的。她特别爱唱歌,我们去拍的那时,她每天去公园唱一个小时的歌,是公园里年龄最大的。看她年轻时候照片,有点像周冬雨那个感觉。
她当时是司令部的秘书,敌军轰炸建筑物时,她为了保护机密文件,抱着公文包就从三楼还是四楼直接跳了下去。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上面是飞机在轰炸,下面是“铛铛铛”的炸弹,一个女孩子破窗而出。当时那会儿三四楼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冬天还有积雪、帐篷什么的遮挡。但她跟我们说,当时啥都没想,就是觉得这个文件比自己的生命重要。我们特别想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但正式拍摄的时候,老人却忘了。她不仅忘了这件事,她连自己参军的年份都忘了。
她女儿说,上了92岁之后,她的思维就时好时坏。很不巧,我们拍摄那天她的思维变得不好了,就停留在她当时喜欢照相,来来回回地重复这个话。我试图顺着她的话题往下问,这也是有些观众在评论里质疑说,我为什么只关心女孩子爱不爱照相。其实不是我关心,作为采访者,我希望被采访者最大限度地主动去说。当天老人的思维就停留在照片相关的,所以我只能顺着她问照片相关的问题。但她也接不住我的问题,还是回到原点。
就在我们已经准备放弃的时候,给我们介绍她的熊朝瑞奶奶来了,刘素谦一回头就看见熊朝瑞。我在她对面,看到她那个眼神跟刚才不一样了。我就问了她一个问题,我说您看看这是谁啊。她一下就把我这个问题接住了,说“这是我战友,熊朝瑞”,那一瞬间我觉得老人的思维就回来了,特别的奇妙,就是一瞬间就回来了。她还开玩笑,说熊奶奶现在漂亮什么的,我们大家就开始很放松了,说老人知道开玩笑了挺好,证明她情绪正常了。
我们就打算先把熊奶奶请出去再接着问,结果一转头,真的就一秒钟,刘素谦的脸就变得悲伤了,说“我现在已经这么老了,你们才来,你们再不来我可能就走了”。当时她抓着熊奶奶的手,让我觉得没有办法把她们分开,那就索性两个人一块拍,就是全片当中唯一一段双人画面。

全片唯一一段双人画面
老人对死是不畏惧的,一个怕死的人,是不会说出来“我知道我这个身体随时都会走”的话。她是向死而生的,包括她也很清楚她的照片,他们的历史会在更大的历史当中随风而去。其实有的时候历史对于我们普通的人而言,可能就是一张照片,撕吧撕吧这段历史就没了,曾经的长辈的这种过往可能就灰飞烟灭了。
我觉得我很问心无愧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至少为我们所有采访的这些老兵的家族,保留了一段完整的家族长辈口述史,我们片子里面虽然用到的少,但是每一家每一个老兵,我们都把完整的声画资料做了一个硬盘,送给了每一个老兵的家属。
观察者网:有的爷爷说不愿意想过去,一直回避这个事,一个爷爷甚至说他没给孩子讲过自己抗美援朝的事,是不是有的老兵不是那么容易开口?
宋坤儒导演:对。比如说上海的谈学贤,谈学贤经历过上甘岭的马鞍山战斗。他当时是是7班班长,有22个人,这个班比正常的班人数多,最后就剩了两个人,20个战士全部牺牲了,其实是一场相当惨烈的战斗。我就一直问爷爷,我说您跟我说说您马鞍山呗,咱们怎么打的,老头就绕,说我们不去说这些,说这些就不是一个很积极的思想,我们当时跟朝鲜老百姓的纪律可好了,路过苹果地都不摘苹果,然后就说了一个多小时。
他听力不好,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同志说就大声跟他说“谈老,说说战斗情况”。然后谈老又开始说,“我当时是7班长谈学贤,跟朝鲜老百姓打交道……”。后来我就知道只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他不想说,第二种原因就是他非常不想说。我们就结束采访。有一些老人我们打不开,我们跟这些老人都不是见一次面,最少见两次以上,而且不是采访环境,就是私下,所以有些老人是不愿意提的。
包括像你刚才说的包月禄,包月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英雄的原型。有个电影叫《奇袭》,京剧叫《奇袭白虎团》,那里面就有一个人物叫包月禄,那个包月禄就是生活中的包月禄。当时他们13个人奇袭白虎团,也是算世界军事史的一个奇迹了,无一伤亡,还把人团旗给扯了。就充满了一种年轻小伙子那种愣劲儿,管他什么旗,我就扯下来,就给缠腰上,现在这面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保管。
他们年轻的时候,估计对他们的儿女也说,但是儿女可能听多了,就觉得我爸又说这些事。到了第三代,比如说孙子孙女辈的,说了可能也听不懂,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跟他们的距离太远了。他们能够知道的可能就是教科书上说我们有抗美援朝,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最可爱的人》,仅此而已。
但是从情感上来说,我觉得老人其实还是很渴望讲述他们的故事。所有的老人,在跟我说起他们曾经经历的时候,我都有两个感觉,第一他们回到了少年,坐在我面前的一定不是老头。像任红举,他一边跟我说,我就一边在想,这老爷子年轻得多“猴儿”,他真的是那种上蹿下跳,最调皮、最捣蛋、最“招人恨”的。用他的话讲,就是因为我年龄最小,就最“招人恨”。
像包月禄,他一直跟我说,我没觉得我多么的英雄,我就是觉得稀里糊涂挺幸运的。当时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连长说走、就走。我还问他,我说您当时明知道这个任务很危险,有没有写过什么血书,电影里不是都这么演吗。他说当时打仗哪有这个闲工夫,天天都打仗,每次打仗之前都写一份血书,那血就没了。我说也是,所以很多电影里描述的,其实都是我们这些创作者臆想的片段。
包月禄跟我说,他觉得自己真的特别幸运。这些爷爷奶奶入朝的时候都是新兵,都是“生瓜蛋子”。到战场,特别怕的就是枪响,枪一响他们就赶紧躲起来,但是他们发现老兵根本就不怕,老兵说枪不可怕,炮才可怕。就是说“新兵怕枪、老兵怕炮”,因为炮一轰轰一片,你不知道哪片弹片就轰到你了,枪其实它就是单向的。
包月禄刚入朝的时候,跟他的新兵部队打散了。打散了之后也是一阵阵轰炸,他就跑,然后跟另外一群打散的新兵汇到一块了。他胆儿最大,说我们还是得找到一支部队,不找的话,咱就不就成散兵了吗,手里也没有武器。晚上,这群人就跟着他睡在一个炸弹坑里,大约有10来个人。早上起来天亮了,他觉得肚子疼,就从炸弹坑里出来,去小树林解手。飞机一颗炸弹,这一坑的人没了,除了他,因为他上厕所去了。这个事里,他一点都不英勇,但这个事就让你觉得战争的残酷和无常,一个人一个特别不经意的选择,可能就改变了他的一生。
说回这个问题的原点,就是我不觉得他们是老人,我觉得他们都是少年。第二,就是他们在讲述少年故事时,呈现出来的是两个状态:一个是骄傲,觉得他们年轻时候做的这些事儿很骄傲,他说出来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都带着那种自豪感;第二,感觉他们挺落寂的,很多老人,比如薛英杰、周有春、任红举,刘素谦等等,都没怎么接受过采访,甚至说就没接受过采访。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周有春,在他军休所的家里,5楼没有电梯,我爬上去的。老人给我们开门,特别热情地欢迎进他家狭小的客厅,给我们倒水。我问老人第一句话就是“有记者采访过您吗”,老人说“没有”,“从来没有”。他的回答一出来,我突然觉得特别的惭愧。我觉得这个老人身后,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因为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哭了,他的哭一定是带着某种心酸或委屈。

周有春,中国人民志愿军23军67师炮兵营话务员
《二十二》后,又一部出现大量“自来水”的纪录电影
观察者网:纪录电影通过前期点映来发酵口碑很重要。2018年纪录电影票房冠军《二十二》上映前点映了两个月,《1950他们正年轻》的点映却因为疫情大部分都取消了,这对后期上映会不会有很大影响?
宋坤儒导演:刚才没有说到,这个片子其实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一直在跟疫情做赛跑。片子最终决定去整体采的时候,定下来是2020年2月份,春节一结束我们就立刻走,计划5月份拍完,拍完就是两个多月,结果2月份疫情来了,出不去了,北京成了灾区了。
后期上映,为什么上座率和口碑没有发酵出来,其实看过的人都会被感动,但是为什么现在的票房跟上座率这么低,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原因还是疫情。
我们原计划是一个月差不多15个城市的路演,第一站从沈阳开启,8月1号建军节,我们沈阳的点映首场海报物料,所有的一切包括邀请老兵、跟烈士陵园的支持联动,沈阳的各种媒体都安排好了。突然,南京出现疫情,然后沈阳就出现疫情。原来是南京是一重站,后来扬州,上海、成都、重庆、沈阳、广州都去不了。最后我们所有的活动全部被迫取消,大学又在放假,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钱。最后我们在北京提前上映一周,做了4次点映。所以很多观众后来会说,其实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电影的存在。
当我们把点映全部取消的时候,就已经基本判断,它的上映会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发行也曾经发行过《二十二》,这个发行公司对纪录片的发行非常的熟悉。纪录片一定是先有口碑,如果片子足够好的话,再上院线。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尴尬,就是没有口碑发酵的过程。我们只能等待上映过程当中,这些观影的人去帮我们发酵。
有的观众说,继《二十二》之后,《1950他们正年轻》是中国影史上又一部出现大量“自来水”的纪录电影。特别感谢这些人,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们的片子能有“自来水”,我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们的片子要靠“自来水”。
对我而言,是两种特别复杂的情感。首先感谢,其次觉得悲伤。原因就在于,我经常自己开解自己,其实电影跟人一样,每个电影都有每个电影的命,这个电影从他酝酿、出生到成长,就面临着各种先天性不足,不是说它不够好,而是说背后能给到它的东西太少了。
我们确实也尽力了,我们没有钱,很多人说你们去找大V给你们宣传,如果按正常的费用的话,我们一家都找不起。一些善良的大V,都是他们主动发声的。我真的是觉得,能有这么多人来帮助,特别的感谢。

知名CG画家@乌合麒麟 无偿为影片设计的海报
观察者网:当院线下映后,会上线网络版或电视版吗?
宋坤儒导演:很多人都在问我说会不会有网络版,特别真实的告诉大家,目前没有,但是如果说,未来更多人想看到网络版,一定可能是会有的。
但是有一点,网络版跟院线版一定不一样,因为院线版是完全针对院线这个环境打造的。首先,网络版一定会做大量的删减,现在的片子是98分钟,根据网络的特性和现代人独自观影习惯,一定会把这片子做得很短,可能有大量你在院线看到的东西,在网络版就看不到了。
第二,可能会更改一个新结构。在院线,我们给观众呈现的是一个浸入式的感觉。在网络版的情况下,你独自观影,很难用一个巨大的声音跟影像的魅力,让你沉浸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变方式了。院线里面我们有很多留白,很多情绪的疏解,很多打断的镜头,我们就可以这样做,长时间沉默让人感受到背后力量。但如果在网络上,假设我们用一个手机,他会觉得手机坏了,手稍一滑就过去了。那种镜头对网络是没有用的,我们就要大量的改,可能这场戏整个拿掉,你看不到这个人了。
现在电影里面这26位老人,其实我就想做一件事,我要把他们变成一个人,这26位老人所有的故事,其实在我的脑海里,就是让他们变成一个人——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坚守住院线的阵地。我们不甘心,说白了就是不甘心。前几天他们说,导演要不你也跪一下,跪一下票房,跪一下观众。我说首先我尊重观众,其次,我身后站的这些爷爷奶奶,71年前他们都没有跪过,我不可能跪。别的片子有可能我作为导演,真的会下跪,这片子我不能跪。如果我今天跪了,有一天他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就是化成鬼也不会原谅我。我身上背负的是他们的嘱托,我不可能带着他们的嘱托下跪,不管这个跪是跪什么,不可能。我一定得站着,哪怕我内心特别想跪着,为了他们,我现在也得站着。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提到英雄,有些人就觉得不对”
观察者网:您接下来还会继续拍纪录电影吗?
宋坤儒导演:我觉得纪录电影的未来会很好,但有没有可能我再去参与,就不好说了。我真的觉得做纪录电影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电影再怎么说,我有明星。任何随便一个烂故事片卖得都比我们好。我们那天在群里说,我们观影人数终于达到10万人了,对我们来说是特别不容易的一步,有10万人看过这部电影了。但是你在灯塔、猫眼专业版随便一划拉,一个烂故事片,随随便便几万人就冲过去了。
如果一定让我说实话,我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来讲述这些爷爷奶奶的故事,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继续来讲述。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你如果想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所谓的私欲的话,拍故事片肯定更合适。我们前前后后也差不多4年,上映很惨淡,观影人数也很少,社会效应、口碑也没有。我两年就可以拍一个故事片,剧本写好,3个月周期拍摄,6个月周期后期,就可以上映了。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现在我都觉得我们挺愚蠢的。第一个愚蠢是太过于自信,第二个愚蠢是把所有判断和思考的权利都交给了观众。很多人都说这个片子,整个的剪辑弄得那么淡,也没什么导演观点。甚至有的观众说,这不就是一堆采访放一块了,当然,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作品里面解读出他们想看的东西。我只是想说,纪录电影需要导演,也需要编剧,如果没有导演和编剧,你们看到的就全是素材,而素材是没有情绪的。
还有观众说,你就不应该剪,每个爷爷奶奶就应该让他们说,我说那样恐怕你在这部电影里面只能看到两个人。每个老人的讲述都两个多小时,我一个人剪一刀,正好俩人俩电影就凑齐了。当然我们不去跟观众计较这些问题。
反正我干这么一事,第一我自己问心无愧,第二我对这些爷爷奶奶问心无愧。以后干不干再说,反正这事儿哥们已经干了,干了就干了。我也不后悔,赔钱我也认。其实片方会比较的惨,就现在的票房情况,连宣发费用都收不回来,就更不用提之前那些正常的制作投资了。
你不知道,虽然我们片子小,但其实每天我们宣传的小伙伴、发行的小伙伴,包括片方,我们每天深夜都在开会,都在想明天怎么办,我们的目标是能扛一天是一天。我后来鼓励他们说,我说哪怕说全国我们就剩下100场,剩下10场,剩下一场,我们都得坚持,因为只要有场次开就会有人看,只要有人看就会有人帮我们传播。因为我们已经没子弹了,我们自己的子弹已经全打光了。
我在电影学院上学时,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有国际生,一个特别年轻的乌克兰的学生,十八九岁,跟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学汉语。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就聊起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说当说有讲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电影。那女孩是一个挺漂亮的乌克兰姑娘。说着说着就哭了,一直在哭,说我们真的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们后来的生活,我们必须要铭记先烈。当时我觉得有点震惊,觉得特别像政治老师,但她真的是特别的真切。我不明白现在有一些人是哪出了问题,为什么一提到英雄,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对。
当然这次2020年的抗疫,很多90后00后冲到了第一线,我觉得特别高兴,包括这些老兵在采访的时候也说,现在的年轻人其实跟我们当年一样,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冲到前线。

但是我不能同意的是,很多人说纪录片为什么不免费看,猫眼上还有人说,这个东西还买票,那不看了。还有人在豆瓣给我留言,说你干这个事儿就应该学柴静,你就应该倾家荡产干,让所有的人免费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我没回,但是我很生气,我说第一你怎么知道我没倾家荡产?第二你怎么知道她倾家荡产了?第三为什么做好事就得倾家荡产?难道做公益就得死是吗?我不明白到底哪出了问题,其实我也挺痛苦的。
这几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看完都说好,然后没有人看。这事本身就特荒诞。如果我做导演的话,它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电影,类似于《黑炮事件》。所有人都觉得很好,但没有人去看。你不觉得很荒诞吗?
我的压力不是票房,我根本就不care票房,干这个事的时候,我就跟所有片方拍了桌子,就说这事儿90%、95%必须赔钱。在过程当中也有片方退出,就觉得这事干不了了,投资就撤了。不是所有的片方都很坚定,现在留下来的片方是一直很坚定的,也有不坚定的片方。但是我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这事你不能逼别人。
首先我个人就特别讨厌“道德绑架”,所以为什么在整个宣传过程,从来不会用所谓“道德绑架”的方式。其实之前有一些片子,确实有道德绑架的嫌疑,“不看就不是中国人”,为什么不看一个电影就不是中国人,我都不知道这些论调是怎么来的。
我还是想保持我那个执念,我觉得他们必须得被仰视。我还是不能够接受,我们以一个特别随便的态度去观看他们。当然这可能确实是我的执念。
如果我们把他们想象成自己的爷爷奶奶,我经常把他们想成我自己的爷爷奶奶。就像我们片子里,有一个老兵叫薛英杰,我们都叫他“姥爷”。薛英杰是跟我接触时间最长的一个老兵,差不多持续了3年,我真的把他当成姥爷。

薛英杰,中国人民志愿军47军司令部军医
今年4月份做调色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薛英杰外孙女打来的,说姥爷昨天走了,我现在得赶回邯郸,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我们当时特别想一起去,但因为后期也有别的工作,所以把我们的时间排得很死。我们又不是什么大片,只能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我说现在去不了,还很平静地就挂断了。挂完之后,片子正好又出现了薛英杰的画面,那个时候你再看到他,怎么说,特别的奇怪,就是你刚知道这个人已经不在了,这个人就在一个巨大的屏幕面前,还在跟你诉说着他的故事。我跟我搭档两个人就都哭了,哭得特别伤心。调色师说导演我们要不要停一下,我说不用停。那一天,我真的觉得特别自责。
自责的原因是,薛英杰在住院之前,一直跟他的外孙女说,能不能让我们把片子给他看一看,他想看一看自己的故事。因为对姥爷的情感太深了,我一直跟小欧说,我说我一定给姥爷剪好,现在还是一个特毛的样子,音乐字幕啥啥都没有,颜色乱七八糟。我说你再给我几天,你再给我三周,我把它剪立整了,我给姥爷看一完整的,到时候我们拿着电脑带着音箱过去。我就老想做一个特别好的东西,这可能是性格里面一个缺陷,追求一种不太现实的极致。所以薛英杰最后就没有看到过现在这些画面,这事让我觉得特别的难过。
看过电影大家都知道,薛英杰把战友埋葬,想着有一天打回来再把战友带走,但谁想到战事变化,部队调动,他就没再回来,成为一生的遗憾。这件事其实在他心里锁了挺多年的,但现在我又亏欠了他一个承诺。
坦白说,这个电影的价值,一定超越票房。今年是2021年,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年,我们现在老人最小86岁,最大98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2030年,也就是80周年的时候,很可能就不在了。你们想听到亲历者的声音,去哪找呢?所以它已经超越了一个常规的商业电影的逻辑了。
对票房我们一点都不纠结。你一定要说我是因为票房、排片失望,好吧。但其实我内心真的不是这么想的。我内心真的是觉得,我们一定是哪出了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它可能也不是电影的问题。
我那天特别愤慨的一件事,我们被迫、躺枪上了一一段热搜,是源于说我们上映了多少天,票房是100多万,好像有粉丝去筹款一个小时,人家就筹到了200多万。
我特别讨厌这种比较,我觉得首先这种比较特别不尊重我们的老兵。粉丝行为,我不去讨论它正确与否,谁还没年轻过,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我的偶像,他们现在对他们偶像的这种推崇,没有任何的不好,当然好不好我说了也不算,都是有爹妈的人。我只是觉得,把我们这两件事并在一块的人挺讨厌的。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很多观众都想问一下孙德山爷爷自己办的纪念馆,具体位置在哪?
宋坤儒导演:在辽宁沈阳浑南区高坎镇旧站村。
如果你有机会见到这个爷爷,就会发现他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老人特别的憨,憨厚的憨,也就代表了他特别的直,特别的倔。他今年93岁了,为了说给他展馆买几个那种三四块钱的照片,他可以卖一车垃圾,然后从沈阳北站走回他自己的家,可能要走30多公里。
你会觉得这老兵挺傻的,为啥呀?他儿子闺女、老伴都跟他说你别弄了,90多岁了,你就四世同堂安享晚年得了是吧。不行,老人说只要我活着我就得弄。我对于他的理解是,他人回来了,但他把自己的某一个部分永远留在了那个时空里。他做这些事儿,是为自己吗?他是免费的。老头不管在屋里面穿什么衣服,只要有人进他院里,就立刻穿上军服戴上军帽,从头给你讲一遍,抗美援朝怎么回事,几次战役……

工作照,右二为孙德山
他那屋可热了,等于把他的院子上面盖了一个盆,不通风,连空调都没有。我们2020年去拍的时候,太热了,就凑了3000块钱,我说我们来不及了,要来得及,我就立刻下单给你买个空调。我们得走了,我说您务必装个空调,至少能够凉快一点。在外人看来,就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他为了什么呢?我对这个问题一直在思索。就是每个老兵,面对他们过往的方式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去回溯这段历史。
有人看了电影后说,看到一个老人在田间骑着自行车,感觉特别的凄惨,我说是吗?我不这么认为。一个93岁的老人还能够骑自行车,代表他得有多么的顽强和硬朗。有的画面没拍,就是他每天要抡一个很大的实心铁锤,从里面砸出钢条,能卖个两三块钱。93岁的老人,不染发,头发是黑的,牙没有掉。我能够想象他十七八岁的时候什么样子,他的兵种是通讯员。就是在战地交通被破坏后,他要一个人上路,比如说从中线去东线送信,可能两三百公里,这一路他要么就搭车,要么就靠走,中途也有特务,他就一个人上路,所以这爷爷胆子特别大,特别硬。
他说我无所谓,我都这么大岁数,我就是想我们这些战友。这些老人普遍都藏着一个心理,就是说他们认为活着不是自己的事儿,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活,另外一方面他们觉得要活就得要把战友的命都给活出来,每一个人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