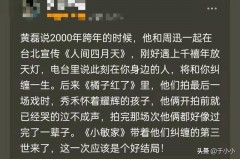原著 / 罗杰·金堡、翻译 / 秦兆凯
译者序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的艺术写作日益趋向晦涩且过度理论化的学院作风。相比之下,罗杰·金堡(Roger Kimball)的文字中却透露出一种与约翰逊博士、罗斯金、威尔逊、格林伯格和克莱默的写作中所体现的清晰、简明、观点鲜明特点一脉相承的传统。金堡的文风清晰、犀利、洒脱,充满讥讽色彩,并且直指要害,读来酣畅淋漓,常常让人不禁拍案叫绝。希望读者能从这里译出的《错误的转向》间接地感受到金堡文字的风采。
文中,作者用犀利且充满幽默的笔调,借画廊清洁工将达米安·赫斯特的一件所谓“艺术作品”误认作垃圾而扔掉的事件,试图揭示造成此种荒谬现象的内在原因:艺术在20世纪中所做的一次次错误的转向——轻浮和偏离审美的艺术态度。在金堡看来,几乎所有艺术上的错误转向,都起源于20世纪的头几十年。其肇事者首当其冲的就属杜尚。随着达达、超现实主义和杜尚的出现而开始的精英式的沉溺,到了20世纪60年代已经演变为一种全面的消遣。这时,错误的转向遂形成主流,一场罕见的灾难得以泛滥。
接下来,金堡通过对2001年在惠特尼美国艺术馆举办的“启示:美国艺术中的投射影像1964—1977”展的回顾,向读者揭示了这些错误的转向形成的过程。惠特尼的新闻稿将《启示》说成是“一个对艺术具有转变性影响的作品的重要展览”。但金堡认为,虽然展览中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作品的确对艺术产生了转变性的影响。但是,“它不是一种具有审美趣味的影响。展览中共有19个装置。没有一个具有哪怕一丁点儿的艺术趣味”。金堡不禁讽刺道:但“作为一种个案研究,《启示》是一个给人以启发的事件。它的价值是教育性质的,而不是审美的。就像一次到疯人院或医院病房的旅行,它有助于我们成为更好的流行病学家,为我们提供了某个地方可怕地出了问题的样本。”
金堡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个被解释为“显示了瑙曼对使用重复和模糊来创造一种新的雕塑语言的兴趣的”《旋转的球体》的作品,“同雕塑或雕塑语言没有丝毫的关系”。在很多展出的作品中,金堡感觉到,最显著的问题是艺术实践的界限或常规或语言正在被“重新界定”“被质疑”“被跨界”或“被挑战”的伪装。他不无讥讽地感叹道:“从众多的被赋予重新定义他们艺术的常规荣誉的艺术家来看,你会认为完成如此的转变仅仅是分分钟的事。”而事实上,“重新定义或创造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是一个世纪才发生一次的事情。”金堡总结说:《启示》中所纪念的作品有助于将一种对待艺术和文化的“轻浮”态度固定为法典,这一态度在达米安·赫斯特以及所有其他邪恶的轻浮党羽中找到了当代的增补版本。
通过剖析一个个具体的实例,金堡对当代艺术中常见的用故弄玄虚和晦涩掩盖其内在空洞的做法,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在越来越多的艺术写作者对西方当代“学院化”艺术写作亦步亦趋的今天,金堡的写作无疑使我们眼前一亮。
达达是对绘画物质一面的极端抗议……它是一种我依然非常同情的虚无主义。
——马歇尔·杜尚,1946年
Inane:形容词、缺乏意义或内容;空洞。
——《美国传统词典》
一
本年度艺术界最脍炙人口的新闻发生在10月份,承蒙英国广播公司提供的消息。在《保洁员扔掉赫斯特的装置作品》的悦人标题下,世人读到:
一名伦敦画廊的保洁员把达米安·赫斯特的一件装置误认为垃圾而清除。伊曼纽·阿萨里(Emmanuel Asare)于星期三早上在视觉风暴画廊无意中发现一堆啤酒瓶、咖啡杯和溢出的烟灰缸,于是将其扔掉。
我希望阿萨里先生立即得到大幅的加薪。一个能够犯如此错误的人是身边极其有用之才。其实,我愿意特此建议他被一些著名的伦敦报纸雇佣——比方说,《泰晤士报》,或《每日电讯报》——作为艺术评论家。军队通常拥有特种和秘密部队,为何批评界不呢?作为简洁和有效的典范,阿萨里先生精干利落的批判性介入几乎无人能及。
可惜,他的漂亮活儿不久就被抵消了。据报道,赫斯特先生觉得这个小小的插曲“歇斯底里地好笑”。为什么不呢?这家画廊的主人——可能受到作品期待售得的六位数字的激励——马上着手将赫斯特的作品恢复。谢天谢地,他们有“作品是什么样的记录”。不然的话,设想一下世界文化的损失吧!实际上,我怀疑重新恢复作品的任务并非那么费力。这毕竟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一经损坏就无法修复的东西。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刊登了一张该作品的照片,(原始的?还是复原的?也许我们将永远不会得知。)看上去同作品的本来面貌一模一样:一托盘“啤酒瓶、咖啡杯和溢出的烟灰缸”。这个描述可以说不能再恰当了。让我们暂停片刻来回想一下“六位数字”这句话的涵义:这意味着至少十万英镑或大约十五万美元,仅仅为了一托盘的“啤酒瓶、咖啡杯和溢出的烟灰缸”。就我来讲,我并不责怪赫斯特先生觉得整件事“歇斯底里地好笑”。无疑,他的银行顾问也会这么觉得的。
画廊的一位发言人建议,阿萨里先生有益健康的秩序感有可能带来“一个积极的结果,可以鼓励一场关于什么是艺术与什么不是艺术的讨论,这永远是有益的”。这是我的另一个建议:立即中止关于“什么是艺术与什么不是艺术的讨论。”远非是有益的,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弱智举动之一。它并非一场讨论,而是一条死胡同。当评论家感染上“什么是艺术与什么不是艺术”的病菌,你知道他们会对艺术感到十足的厌烦。当艺术家染上那个病菌,你会清楚地理解为什么评论家会感到厌倦。
二
达米安·赫斯特或“扔垃圾事件”的正面意义是——除了它的娱乐价值以外——它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中艺术所做的一个重要的错误转向。赫斯特并未引起那个错误的转向。远非如此。他仅仅是那段弯路的主要受害者——或,取决于个人的观点,受益者——中的一员。
目前我们容忍的几乎所有艺术上的错误转向,都起源于20世纪的头几十年。但是随着达达、超现实主义和杜尚的出现而开始的精英式的沉溺,到了20世纪60年代已经演变为一种全面的消遣。就在那个时候,错误的转向成为高速公路,此时,一场罕见的灾难得以泛滥。
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肇事者无疑是安迪·沃霍尔。是沃霍尔——在罗伯特·劳申伯格和贾思帕·约翰斯这样的人物的教唆下——向艺术中注入了一种使波普艺术及其分支成为如此诡异、具有两个面孔的邪恶的轻浮:一面全是微笑和坎贝尔汤罐头,另一面则是吸毒、性侵和虚无主义自恋的冷酷下流社会。波普艺术之所以赢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它的实践者设法将他们艺术中的对立因素结合起来:在毒药丸周围加上一层糖衣。对于容易受影响的灵魂——他们的数量众多——这是一种使人上瘾的组合。
像达米安·赫斯特以及今天占据着艺术界的其他职业违规者,是沃霍尔邪恶的轻浮的继承者。没有一个认真的透纳大奖竞争者可以缺少它。惠特尼双年展中也充满了这种轻浮。而且过去几十年中几乎所有的大牌明星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赋予了那种破坏性的感染力。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而不是艺术的天赋,然而对这些能力的故意融合或混淆一直是当代艺术界最时髦的区域的特征之一。
任何对观察使达米安·赫斯特那样的艺术家成为可能的感性具体形成过程感兴趣的人,应该顺便到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逛一逛“启示:美国艺术中的投射影像1964—1977”这个展览(展览于2001年10月18日在纽约的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出持续到2002年1月6日。展览的图录,由克里希·艾尔斯编辑,已由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出版,共184页)。我想,没有几个人会觉得那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经历。电影和录像装置几乎从定义上就是自命不凡的乏味的典范。即使按照这一领域的严格标准,“启示”在制造令人恼火的无价值氛围方面也是佼佼者。
惠特尼的新闻稿将“启示”说成是“一个对艺术具有转变性影响的作品的重要展览”。那只说对了一半。展览中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时期的作品的确对艺术产生了转变性的影响。但是它不是一种具有审美趣味的影响。惠特尼新闻稿称那个时期是“一个产生了一些至今最有意义的移动影像装置的黄金时期”。事实上,那是一个颓废和崩溃的年代,正如将会对任何重访那段历史的人显而易见那样。展览中共有十九个装置。没有一个具有哪怕一丁点儿的艺术趣味。但是作为一种个案研究,“启示”是一个给人以启发的事件。它的价值是教育性的,而不是审美的。就像一次到疯人院或医院病房的旅行,它有助于我们成为更好的流行病学家,为我们提供了某个地方可怕地出了问题的样本——有些很残忍,有些则仅仅是可怜。
将达米安·赫斯特这样的艺术家与电影和录像展联系在一起可能有点奇怪。就我所知,赫斯特从未侵入这个艺术类型。但是尽管“启示”全部由电影和录像作品组成,它的意义在于其体现的艺术和文化态度。这是一种赫斯特与他的同行深切认同的态度。
三
理解这种态度的最好方式是认真思考展览目录中某些对展出的作品的描述。例如,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的《旋转的球体》(1970年),被描述为“动摇观众对物理空间感知”的尝试。作品大概分为两个部分:令人钦佩地精确说明,以及荒谬至极的解释。
四台电影放映机显示着一个小小的钢球,置于白盒子中玻璃板上并被极具放大,快速地旋转三分钟。每次这个球体停下来的时候,一个白色方块的形象能够隐约可见,并反映在旋转球体的表面。被放大的、抽象的表面模糊了一切尺度感,产生一种令人晕眩的涡流,将观众推向外边,回到画廊空间。《旋转的球体》显示出瑙曼对使用重复和模糊来创造一种新的雕塑语言的兴趣。在这种语言中,视知觉通过变更物理空间的参数得以探索。
有没有必要指出,瑙曼的作品同雕塑或“雕塑语言”没有丝毫的关系?仅仅是重复不同于对重复的现象感兴趣(或深刻的洞察)?拍摄一个旋转的球体算不上“探索”视知觉?
恼怒是在这个展览中得到充分锻炼的情绪。这是展览图录中对小野洋子(Yoko Ono)的《天空电视》所说的:一台摄像机放在画廊外的墙壁或屋顶,镜头对着天空。实时的天空图像被传递至画廊内的电视屏幕上,将外部世界投射到内部空间……意味深长的是,摄像机不是瞄准观众,而是天空,暗示着关注自我和商业电视催眠作用以外无穷世界的必要性。
再一次,本人不得不称赞这个说明不带情感的精确——小野的作品的确只是一个天空的影片——紧随其后的解释只是一派胡言。展览图录中的大部分描述都遵循这样的模式。它们不带感情色彩地开始,然后渐渐变得古怪。当读到下面关于威廉·阿纳斯塔西(William Anastasi)的《自由意志》的文字,我们就清楚了自己的所在。
一个引起对画廊空间关注的录像雕塑,聚焦在它的一个最寻常、最被忽视的面貌:它的角落。一台固定在显示器顶部的摄像机对准了一个角落,这个角落的图像被实时传递到显示器的屏幕上。
一个角落的录像。妙极了。我肯定你能想象得出来。它正好支持策展人关于探索“自闭症概念的内涵”的说辞。不过,这个语法上有毛病的句子呢:“这一自我指涉将唤起佛教关于个人寻找外在答案以及审视内在自我的重要性的告诫。”
当然是彻头彻尾的废话,并且对佛教的解释也不准确。但是你仍然可以钦佩这种用更高意义的支撑掩盖咄咄逼人的平庸所做的努力。事实上,那是一个若要想在艺术影像界出头的人必须精通的步骤。让我们看看彼得·坎帕斯(Peter Campus)的《网络》(1977年)吧。你走进一个黑暗的空间,什么都看不见,直到你转过身来,面对一台电视显示器,上面播放着你自己颠倒的图像。当你路过一家装有对准过路人摄像机的电器商店,也许已经上百次地看到过类似的情景了。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仅仅是被录像了。在惠特尼的隐蔽处,你发现《网络》“属于一组具有开创性的闭路录像装置……坎帕斯幽暗的投影一方面作为空间、表面和尺度上的形式探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幽灵般的夜的映像,将我们带入与内在自我的存在主义冲突。”
四
“启示”中展出的大部分装置具有小学生科研课题的外表。但是,与其搞清楚和说明某种自然现象,它们得意于崩溃、无效或单纯的空洞。在安东尼·麦考尔(Anthony McCall)的《描绘圆锥体的线》(1973年)中,
一部显示一个大大的圆圈被绘制的过程的影片被投射到一个黑暗空间的墙壁上。接着一缕细细的喷雾被引入这个空间里,使得放映机的光束显现出来,同时这个图形渐渐地从一根线条发展成一个大的圆锥形,于是描绘的圆圈完成了。
这大概就像观看青草生长一样扣人心弦。我们被告知,在《快门互动》(1975年)中,保罗·舍里兹(Paul Sharits)“对胶片的物质属性以及电影机制的严格分析进行了探索”。然而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却是三个在墙上颤动和闪烁的彩色长方形,同时某种不可辨别的杂音(“抽象的配音”)传送进来。观众被警告这种“闪动效果可能对癫痫病患者有害”。但是那些对用半消化的、科学术语碎片装扮的傲慢的、伪艺术的乱搞有过敏症的人呢?对那个明显危险的健康警告又在哪儿?
这些装置中很多都含有政治的成分。譬如,在维托·阿康齐(Vito Acconci)的《第二种视野的另一种声音》(1974年)里,本人听到这个艺术家广播“一连串来自像切·格瓦拉、佛朗兹·法农和埃比·霍夫曼这样的20世纪的左翼革命家的公报,用以表述他以及其他艺术家感到的发生在越南战争期间的方向和正直的丧失”。当然在那段时间确实曾有过方向和正直的丧失,但那是一种并非由阿康齐发现,而是由像他这样的艺术家所代表的丧失。
虽然政治潜流在《启示》这样的展览中极易察觉,更为显著的是艺术实践的界限或常规或语言正在被“重新界定”“被质疑”“被跨界”或“被挑战”的伪装。我们已经看到布鲁斯·瑙曼愚蠢的电影如何被说成“创造了一种新的雕塑和电影语言”。同样的情形在这个展览中几乎每隔一件作品就发生一次。琼·乔纳斯(Joan Jonas)的《环境》(1976/2001)据称“重新界定了雕塑的和电影的界限”。西蒙·福尔蒂(Simone Forti)被赋予创造了“定义一种新的运动语言的标志性作品”的荣誉。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同其他人”被说成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语言,其中我们对作品的感知成为它的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安迪·沃霍尔的双屏幕电影据说“废除了线性的电影时间”等。从众多的被赋予重新定义了他们艺术的常规荣誉的艺术家来看,你会认为完成如此的转变仅仅是分分钟的事。事实上,重新定义或创造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是一个世纪才发生一次的事情,假使真的发生的话。
“启示”在传播这种自命不凡的无稽之谈方面算不上是绝无仅有。相反,它完全代表了当代艺术界的主流。如此多的艺术成功地质疑自己常规的想法部分地是将言与行混淆的结果。说“我正在重新定义我的艺术并创造一种新的雕塑语言”是一回事,实际上这么做是另一回事。天性憎恶空洞。面临惊人空洞的工作,人类的聪明才智以意义的借口来占据这个空白。当代艺术界一个有益的经验法则是,自负的水平与艺术成就的水平成反比。因此,人们可以期待“启示”的自负程度极高。人们果然没有失望。在展览的图录中,托马斯·祖默(学者、作家、策展人和艺术家)以一篇名叫《投射与体现/分离:虚拟的系谱》的文章收尾。文章观察到再三地,一个德勒兹的“纯粹重复”的承诺体系,被它自身持续的反复所阻塞,不时打断媒介的空间,塑造着构成作品的现象与附带现象之间的互动。指示延伸的观念——身体进入空间、穿越时间、进入其他空间、穿越代际——以及身体的延迟始终是媒介中恒定的变量。在因而发生的无知中,身体被看到停止了片刻,一切都被揭示,背景转变为图像中的图像(mise-en-abyme)。因此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的确不是。
像祖默先生这样的文章是一个确定无疑的预警信号:什么地方可怕地出了问题。好比沿着胳膊的阵痛,它应该促使我们寻求紧急救援。这就是像阿萨里这样靠谱的人士可能极有用武之地的原因,要是有足够这样的人就好了。“启示”中所纪念的作品协助将一种对待艺术和文化的态度固定为法典,这一态度在达米安·赫斯特以及所有其他邪恶的轻浮党羽中找到了当代的增补版本。安迪·沃霍尔在使那个错误的转向流行上不比任何人做得少。但是那场大灾难的起源发生在更早的时候。在其为展览图录撰写的文章中,克里希·艾尔斯(Chrissie Iles)提到杜尚的次数比任何其他艺术家都要多。这完全恰当。因为如果沃霍尔是艺术界邪恶的轻浮之父,杜尚则是其祖父,是真正的家长。杜尚的精神是艺术界如此持久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不禁忘了杜尚并非试图对艺术进行革命,他要做的是消灭艺术。没有人比杜尚本人对把达达吸收进艺术的经典更感到吃惊了。“我将瓶子架和小便池扔到他们面前作为一种挑战”,他轻蔑地记录道:“而如今他们却欣赏其中艺术的美。”我曾经以为杜尚的继承者根本地曲解他了,他们,尽管以怪诞和变态的形式,恰恰在使一种杜尚着手毁灭的艺术活动永久化了。不过,像达米安·赫斯特这样的艺术家同“启示”这样的展览使我不得不三思。
有很多毁灭一个制度的方式。杜尚选择了野蛮的戏仿后放弃艺术。(当一个人可以下棋的时候为什么要做艺术呢?)他的继承者则不那么小心谨慎。但是也许他们同样有效。空洞,经不懈的自负的发酵,无疑造成了损害。
五
当我终于小心翼翼地走尽“启示”的幽暗回廊,我决定使用楼梯而不是电梯从四层下去。下到三层时我看到一条长凳,在这条长凳上——蜷缩并且明显熟睡着的——是一位年轻女子。她看起来似乎如此小心地摆好了姿势,以至于我突然停下来:这是……这可能是……一件艺术作品吗?一个行为作品,也许,用以图解资本主义父权的巨大力量对女性的毁灭性影响?尽管极大的诱惑,我忍住没有将睡眠者叫醒问个究竟,并继续向下走。当我下到二层并发现,蜷缩并且明显熟睡着,一个简直就是三层的睡美人的双胞胎,想象一下我的惊奇吧。这肯定是“一件装置”,我想,并且远比我在四层遇见的任何东西都更加动人。它甚至让我想到这也许是对“启示”的一个讽刺性的评注,用来强调这是一个旨在将观众推到睡神怀抱的展览的事实。我急忙下楼并问一名保安是否熟睡者是一个展览的一部分。他一脸茫然。接着我问一名路过的管理人员。她显出忧虑的表情并向保安询问究竟。然后她们开始一起上楼去弄个究竟。我则走到了外边。我为打扰了那么多睡眠而感到歉意。但至少,我这么想,惠特尼没有雇佣伊曼纽·阿萨里:谁知道他会把什么给打扫了呢?(本文译自Roger Kimball, “Wrong Turns,” Mew Criterion, december issue, 2001.)
秦兆凯 旅美学者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