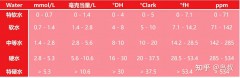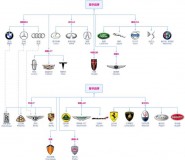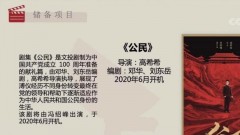在中日两国历史、文化诸多要素的制约之下,“东洋”概念几经移转,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在日本,明治以降“东洋”所指的地理空间扩大,成为与意指欧洲的“西洋”一词相对应的概念,还意指包括日本、中国、朝鲜在内的“东方亚细亚”。在中国,“东洋”在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成为专指日本的地理概念。将模糊而多义的“东洋”概念从与“西洋”相对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放回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可以为思考欧洲以外地区之“现代性”问题提供一个有用的视角。
引言
在近代日本,“东洋”一词往往含有日本引领亚洲其它国家对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意味,诸如“东洋之盟主”“东洋之霸主”等等;而到了二战前后,其语境则往往与建立在家长制基础上的“东洋式专制”(即汉语中的“东方专制主义”之意)相关联,表征着亚洲的落后性[1]。近年来,“东洋”与“亚洲”“东亚”等词一样,又作为东方主义的象征而受到批判[2]。这些议论尽管立场迥异,但无论是以近代欧洲社会为理念模型来批判“东洋”的“落后性”,抑或是从东方主义视角抨击欧洲中心主义,二者都将“东洋”(亚洲)与“西洋”(欧洲)置于对立地位,并不约而同地以“西洋”(Occident)为前提来谈论“东洋”(Orient)。人们似乎忽视了一点,即“东洋”一词在东西方接触之前就早已出现于汉字文化圈,在复杂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几经变化,最终才演变为目前含义模糊的“东洋”概念。
Asia(中文书写为“亚细亚”“亚洲”;日文书写为“亜細亜”“アジア”)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在距今约4个世纪前,由耶稣会士利玛窦的《万国坤舆图》而传入中国[3]。与此不同,“东洋”和“西洋”在中国语境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分别意指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与印度洋一带。在19世纪,“东洋”一词在使用中出现了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亦指位于该海域的日本;其二则指包含中国、日本等在内的亚洲地区,与意指欧洲的“西洋”一词相对。
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宫崎市定曾经在《南洋を東西洋に分つ根拠に就いて》一文的结尾部分指出,在明治以后日本东洋史学者们的努力下,“东洋”一词所涵盖的地理范围扩大到亚洲全境,成为与意指欧洲的“西洋”一词相对立的概念。不仅如此,“东洋”概念还“与东洋史一同输入中国,沿用至今。中国本以中华自诩,自居(地球之)中央,将其以南之海域分为东西两洋。及至我国优秀的东洋学建立后,中国自身亦被纳入东洋范畴之中”[4]。宫崎撰写《南洋を東西洋に分つ根拠に就いて》一文,是就汉语文献中“东洋”一词的词源及其语义变化与山本达郎进行论争[5],前面的引用与原文的主旨关联并不大。但是,宫崎在此却提出了有关“东洋”概念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他注意到,“东洋”作为地理概念,在空间上扩展到整个亚洲,“东洋”和“西洋”分别成为对应亚洲和欧洲的地理概念,导致这一变化的是日本的东洋史学。第二,着眼于“东洋”概念在不同文化间的移动,即,意指整个亚洲的新的“东洋”概念随着日本的东洋史著作而传入中国,最终改变了中国人自古使用的“东洋”概念。
本文以宫崎提出的上述问题为线索,通过分析明治时期和清末民初时期中日两国东洋史教科书中有关“东洋”的记述,探讨中日两国“东洋”概念之历史变迁及其相互关系。首先,笔者将对中日两国文献中的“东洋”概念进行简单梳理,继而考察明治以后日本东洋史教科书中“东洋”所指的地理范围,以及将中国纳入其中的新的“东洋”概念大致在什么时候、通过何种途径传入中国,最后,笔者还将探讨自日本传入的新的“东洋”概念是否取代了中国以往的“东洋”概念。以东洋史教科书为主要史料,乃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第一,在近代日本,先有甲午战争后出现的中学“东洋史”课程,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作为学术分支的东洋史学。关于“东洋”历史的官方知识,通过日本文部省审定的中学东洋史教科书而得以普及。东洋史教科书是“东洋史”一词在日本社会定型的滥觞。第二,宫崎市定所称“传入中国的东洋史”亦非日本的东洋史学术著作,而是指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大日本图书,1898年)等明治时期出版的中学东洋史教科书[6] 。
一、两个“东洋”
“东洋”一词,原指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后来成为专指日本的地理概念。宫崎市定认为,在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成书于雍正八年,1830年)中,元代以后书籍中屡屡出现的“小东洋”(婆罗洲西北海域,明代指台湾、澎湖)的“小”字消失,变为“东洋”,“与大、小西洋相对,日本遂被称为东洋”[7]。王尔敏也指出,《海国闻见录》中“东洋独成篇章,专之日本”[8]。
然而,仔细阅读《海国闻见录》的自序不难发现,陈伦炯所说的“东洋”并非专指日本。陈伦炯在自序中提到,清康熙年间,其父曾在施琅的指挥下参加征台之役,此后又“奉施将军令,出入东西洋,招访郑氏有无遁匿遗人,凡五载”。从行文看,陈父身负搜寻郑氏余党的使命数次出入“东西洋”(即“东洋”与“西洋”的合称),其中的“东洋”应当包含澎湖、琉球诸岛在内,并非仅指日本[9]。而且该书《东洋记》一篇记载了日本与琉球的风俗、物产,以及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航线和所需日数等[10]。由此可见,《海国闻见录》中的“东洋”意为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具体指东海中的日本与琉球诸岛。其后,在徐继畲《瀛寰志略》(成书于道光28年,1848年)的《东洋二国》一节中,有如下两段文字:“汪洋之水及至亚墨利加以西,数万里间无大陆。近中国者唯日本与琉球两国”;“琉球,在萨山司马(萨摩)之南,东洋小国也”[11]。与《海国闻见录》一样,此处的“东洋”也指日本与琉球两国。由此可以推知,直到19世纪中期,“东洋”一词仍然指中国东面的大海,具体指日本与琉球两个国家。“东洋”成为专指日本的地理概念,当在19世纪中期以后。
这一传统的“东洋”概念,通过中国人撰写的地理著作、以及欧美传教士在华刊行的地理书籍传入日本。例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地理全志》一书的日译本(刊行于安政六年,即1859年)中有《东洋群岛志》一节,其开篇即称“东洋,又称北平洋,在亚西亚之东,直抵亚墨利加之西。岛屿罗列,附近中华。最大者,曰日本国”[12]。此处的“东洋”并不指日本,而是指“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即太平洋,而日本只是“东洋”诸岛中面积最大的一国而已。此外,在文久元年(1861年)刊行的《瀛寰志略》日译本的地球全图中,原著中的“日本”“大东洋”分别被替换为“大日本”与“大洋海即东洋大海”字样[13]。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大东洋”还是“东洋大海”,都沿用了“东洋”一词的本意,即“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这些书籍在幕末时期的日本拥有众多读者,不难推测,中国传统的“东洋”概念当时在日本也是众所周知的。
加藤祐三在论及日本的“东洋”和“西洋”概念时指出:“在幕末以前的日本,汉学是学问的主流,因此几乎完全接受了汉学中的地理名称”,他认为江户时代日本人所说的“东洋”,与中国的“东洋”概念是同一个概念[14]。佐藤亨在《幕末、明治时期汉语辞典》中,列举了“东洋”一词在明治以前文献中的两则用例。一为“浮舟七艘于东海,渡东洋海二千五百余里”(司马江汉宽政八年〈1796年〉《和兰天说》凡例);二为“亚弗利加大洲极南之地有港曰喝叺,停船于此,考风波之情状,由此赴东洋”(大槻玄泽口授,有马元晃笔录,宽政十一年〈1799年〉《兰说弁惑》下)[15]。前者的“东洋海”与后者的“东洋”,指的都是太平洋这一地理概念,中国与日本并不在其范畴之中。
在江户时代的文献中,以中国为“中”,以位于中国以东的日本为“东”的用例不胜枚举。例如,新井白石在《东雅》(享保二年,即1717年)一书的《总论》部分中,比较日本、中国与欧洲语言之音韵,认为:“东方之音乃新莺。中土之音乃乔迁之莺也。西方之音乃为流莺。”[16]这种以中国为“中”、以日本为“东”的用法,并没有因明治维新而中断。明治十一年(1878年),原高崎藩主大河内辉声在与黄遵宪的笔谈中写道:“东洋鄙人,何与中华雅客相斗乎?宜师事而受教也。”[17]他还对何如璋说:“东洋地小,不足以慰中华人,惟以情谊不变幸为好。”[18]在此处,大河内原封不动地援用中国的“东洋”概念,称日本为“东洋”,与“中华”相对应,来表达对中国的敬仰之意。
然而,在江户时代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了包含中国和日本的“东洋”用法。最著名的是佐久间象山的诗句“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省侃录》,1854年),这句诗赋予了“东洋”“西洋”二词完全不同的文化含义。佐久间认为,“东洋”(包含中日两国)与“西洋”(欧洲)各有所长,前者长于道德,后者长于技术。正如津田左右吉所言,其原因在于自江户时代中期起,日本人越来越多地接触有关欧洲的知识,“西洋”一词便主要用来指称泰西诸国,而“东洋”一词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指包括中国和中国文化影响所及之地区的总称[19]。当然,这一新的“东洋”概念在日本得以普及,还是明治时期以后的事。
明治维新后不久,“东洋”一词就出现在明治新政府的正式公文中。在明治政府于1871年(明治四年)颁布的《美欧使节派遣事由书》一文中,有“东洋诸国与西洋列国,其国体政俗相异,无需赘述”一句[20]。明治政府派遣的岩仓使节团副使伊藤博文,也在一则文书中称:“天皇陛下以为,我东洋诸州所行之政治风俗,不足尽我国之善美。何故?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我东洋也。”[21]在这段文字里,日本、中国等国都被视为“东洋诸国”或“我东洋诸州”“我东洋”的一部分,与“西洋列国”“欧美各国”相对应。
明治十年以降,以日本为“东洋之盟主”、抵抗欧美列强入侵的亚洲主义思想逐渐抬头。在此背景下,“东洋”一词的使用也急剧增多。例如,由民权左派植木枝盛等于1881年起草的私拟宪法《东洋大日本国国宪按》、由樽井藤吉于1882年创立的东洋社会党、由大井宪太郎等于1892年组建的东洋自由党、由涩泽荣一等于1895年创刊的《东洋经济新报》,等等。作为东洋史学前身的中学东洋史科目,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那么,明治时期政府与舆论界所使用的“东洋”概念,对应的是什么样的地理范围呢?荒野泰典在分析资料集《日本近代思想体系12 对外观》(芝原拓自等编,东京:岩波书店,1988年)中“东洋”与“亚细亚”(“アジア”)的用例后指出,二者所指的地理范围有着明显的区别。“亚细亚”用于指称现在的亚洲全境,而“东洋”则指“亚细亚”的东方,即“东方亚细亚”或“亚细亚之东边”,多用于指称涵盖中国、朝鲜、日本在内的整个地区[22]。这与后文所述的近代日本东洋史教科书中的“东洋”一词,在空间范围上基本相同。
据笔者所见,在汉语文献中,将“东洋”作为包含中国在内的地理概念而使用的最初用例,见于洪仁玕(1822-1864)于1859年向天王洪秀全呈交的《资政新篇》。洪仁玕在这篇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章中称:“中国从前不能为东洋之冠冕,暂为失色,良可叹也。”[2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洪仁玕笔下的“东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也不是位于其中的日本和琉球,而是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更为宽泛的地理概念。洪仁玕使用这一新的“东洋”概念,与他曾在香港接受洗礼,并通过传教士的出版物学习欧美近代知识的特殊经历不无关系。
当时在中国国内,“东洋”概念的此种用例尚属罕见。直到19世纪末,“东洋”仍然被用来指称日本。例如,张之洞继派遣青年学子赴海外留学之后,于1903年上奏清廷,建议鼓励现职或候补官员出国游历。他建议以游历“东西洋各国”三年以上者为第一等,游历欧美二洲之一、二国或三、四国两年以上者为第二等,“仅至东洋游历,往返在一年以上者”为第三等,分别予以奖励,“无论东西洋其游历在一年以内者无奖”[24]。张之洞所说的“东西洋”,乃是“东洋”与“西洋”的合称,分别指日本与欧美,而“东洋”则专指日本,其中并不包含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在20世纪初大批士子赴日留学的浪潮之下,“东洋”更成为日本的专称。一时间“东游”“游东”“留东”(指游历日本、留学日本)和“东文”“东语”(指日语)等词汇十分流行。
与此同时,已在日语中得到普及的新“东洋”概念、即包含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洋”一词,也经梁启超等流亡日本的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之手传入中国。1900年,在梁启超赴日后创办的《清议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今之论者每以日本拟英国。曰日本者东洋之英国也。虽然,不察两国之情势与人口之多寡而比较之。妄为拟议。”[25]杨度也在《游学译篇》(1902年)的发刊词中称:“我中国者,以东洋文明之固有,而得老大之名;以西洋文明之将来,而得幼稚之名。乘此迎新去旧之时,而善用其老大与幼稚,则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夫岂难耶?”[26]这一时期,此类新的“东洋”字眼频繁出现于报章。清末士人之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日语中接受新的“东洋”概念,自然与中日两国同样使用汉字有很大关联。但更为重要的是,新“东洋”概念回流中国这一现象,反映出在甲午战争失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指流亡日本者与留日学生)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传统世界观出现了动摇。
不难想象,新旧两种“东洋”之并存,必然导致概念上的混乱。为此,维新派在上海创办的杂志《时务报》特意对“东洋”一词作了如下说明:“东洋指东方亚洲而言,非指日本也。中国在亚洲,是亦居东洋之中也。人每误以日本为东洋,故附辨焉。”[27]在《新民丛报》所载蒋智由(号观云)《华年阁物语》一文中,也有类似说明。蒋称:“由来东洋人者,爱自然景物之天性,过于西洋人。见鸟之美丽而乐,闻虫之啼音而喜,饲育鱼类,以为娱乐,中国人与日本人(东洋人者兼中国日本言,我国俗说指日本为东洋,其说非是),皆同有此风习也。”[28]在此处的引文中,两次出现“东洋人”一词,第一次系相对“西洋人”而言,第二次则指中国人与日本人。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确定“东洋”的地理范围,而在于强调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于“西洋人”,彼此在文化上具有某种共性。
二、日本东洋史教科书中的“东洋”
1894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主持召开的中学教育改革会议上,该校教授那珂通世提议将“支那史”(中国历史)改为“东洋历史”[29],以与“西洋历史”相呼应。那珂的提议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不久得到了文部省的认可。那珂也由此被称为日本“东洋史之父”。按照那珂的构想,东洋史“以支那为中心,论东洋诸国治乱兴亡之大势,与西洋历史相对,成世界历史之半壁”。以往的“支那史”承继江户时代藩校儒学教育的影响,侧重于讲述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亡;而东洋史既“论东洋诸国之兴亡,亦论及支那种、突厥种、女真种、女真、蒙古等之盛衰消长”[30]。从同年11月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草拟的《寻常中学校历史教科要项》中“主授国史,亦授世界史……世界史分为东洋史、西洋史,东洋史中特以支那史为详”一句看,那珂中学教育改革会议上的提议得到了采纳。应当留意的是,尽管根据那珂的提议,东洋史与西洋史一样被定位为“世界史之半壁”,但是,“东洋”的地理范围只包括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并非涵盖亚洲全境。在中学设立东洋史课程之前,已有日本史课程,由于此次中学教育改革没有涉及日本史,因此,虽然从常识上说日本史理应包括在“东洋史”之内,但实际上无论是中学东洋史还是后来形成的东洋史学术领域,日本史都不在其研究范围之内。由于在东洋史以外另设有日本史科目,包括桑原的东洋史教科书在内,二战前的东洋史教科书基本都不涉及日本史的内容[31]。
就“东洋”概念所涵盖的对象区域而言,明治时期的东洋史教科书大致可分为两类[32]。一类基于“东洋即亚洲全域”之认识,将东洋史理解为包括中国史、印度史、西亚史的区域史学(本文称之为“多元中心论”)[33];另一类则基于“东洋史即东方亚细亚之历史”之认识,主要叙述中国中原王朝与周边的关系(本文称之为“单一中心论”)。概言之,持“单一中心论”者占压倒性多数。其理由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江户时代以来汉学教育传统的影响。江户时代的汉学教育主要是学习以《六经》为主的儒家经典,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历史被视为对圣人教诲的实践,同样,在江户日本的藩校教育中,历史也备受重视[34]。在近代引入西方的学校制度后,这一传统也得到了继承。早期东洋史教科书的撰写者大多出身于江户时代的武士阶层,曾在藩校或私塾学习儒学(如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等),还有他们的学生藤田丰八、桑原骘藏等明治维新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后者之中不乏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1889年设立)或此后的支那史学科(1904年设立)、东洋史学科(1910年设立)的毕业生。可以说,尽管“支那史”科目改成了“东洋史”,但由内容观之,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连续性。
第二,对东洋史教育之现实意义的重视。1895年1月,那珂通世在大日本教育会进行发表题为《东洋地理历史讲义》的演讲时表示,日军之所以能在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原因在于参谋本部深入研究了“东洋之地理”,因而使日本人甚至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地理。那珂认为,日本人不仅应当熟悉中国和朝鲜的地理,还应当广泛了解作为欧洲殖民地的西伯利亚、越南、印度等地的地理。这样方能“握东洋之霸权,为文明之先导者,合东洋诸国以当欧罗巴人之势”。同样,那珂也强调研究东洋史的重要性,因为“我东洋人应先研究东洋之历史,其后再研究西洋之历史,方能谓穷究世界之历史也” [35]。可见,这位“东洋史之父”,在提议创设东洋史之初就强烈地意识到,东洋史可以为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军事扩张提供有用的知识。在这一点上,中学东洋史课程与此后发展成为独立学术领域的日本东洋史学是一脉相通的。
第三,欧洲近代史学的影响。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新设的史学科迎来了年仅26岁的德国人R.里斯(1861-1928),担任世界史讲座,由此揭开了日本近代史学的帷幕。里斯毕业于柏林大学,专攻史学,深受兰克史学的影响。他赴任后,创办了日本第一个史学研究刊物《史学会杂志》。他在刊物上撰文批评当时日本的史学界轻视史料考据,提倡在严密的史料批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36],由此奠定了近代日本学院派史学的基础。与此同时,里斯还将兰克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引入了日本,即以民族为单位的历史研究。兰克批判英法启蒙史学抽象地从整体上概括人类的历史,忽视了人类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下的活动,强调应该重视“民族共同体”由弱小的民族集团演变为民族国家之历史。从里斯在东京大学的讲义看,他通过讲授日耳曼等欧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以及向欧洲以外地区扩张势力的历史,强调民族国家在历史叙述中的重要性,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通过揭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由不同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37]。
在1880年代末,随着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确立,民族主义史学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关于大和王朝起源的神话传说、以及江户时代具有神话色彩的国学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以天皇谱系为中心的皇国史叙述。
欧洲近代史学对日本的东洋史领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9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汉学科的藤田丰八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东洋诸国)尚未形成历史团体。……蒙古人种建立之日本、支那、朝鲜及其附近数国稍成一历史团体,稍有历史性之关联,文化与西洋相异。近时所谓东洋史者,即此团体之历史,东方亚细亚局部之历史而已。”[38]藤田关于“历史团体”的认识,来自从柏林大学、维也纳大学留学归来的坪井九马三(1859-1936)。坪井于1891年归国后,在东京大学讲授以兰克“纯正史学”为代表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39],他尤其强调历史学家应当重视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将历史看成一个“有机体”。他比较欧洲与其他大洲的历史,认为“欧洲历史可以写成一部无可挑剔的、有机体的历史”,而“东洋史究竟能否写成有机体的历史,尚存疑问”[40]。
他据此认为,印度与其他“东洋诸国”之间在历史上联系较为薄弱,针对当时一些人将印度史纳入东洋史教科书,他提出了以“葱岭、怒江为界,由此以东”为东洋史、由此以西直至利比亚沙漠的地区为西域史的构想[41]。与此相同,藤田所说的“东洋诸国”,只包括日本、中国、朝鲜等“东方亚细亚”国家,并未将西亚、印度视为东洋史研究的对象。藤田在翌年编撰的《中等教科东洋史》的开篇部分指出,东洋史是“东方亚细亚各民族兴亡之一般史”,由于历史上中国长期在东洋史上占据核心地位,故而“以支那为中心,合史上与之相关联之诸国民而构成一个团体,东洋史者,乃科学叙述该团体之历史者也”[42]。
那么,东洋史教科书是如何叙述“东洋”的呢?下面以“单一中心论”东洋史教科书中最为著名的桑原骘藏(1871-1931)编《中等东洋史》(东京:大日本图书,1898年)为例,进行分析[43]。桑原189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在校期间曾受教于坪井和那珂。《中等东洋史》是他攻读研究生期间在那珂的影响下编写的。《中等东洋史》分量较大,出版的第二年又出版了缩减版《初等东洋史》,1903年又经大幅度删减后改版为《中等教育东洋史教科书》。此后“凡三十年间,直至作者去世,桑原的初版东洋史教科书几乎垄断了中学历史教育”[44]。
桑原在《中等东洋史》的《总论》中写道:“东洋史主要在于解明东方亚细亚古来之沿革”,而“东方亚细亚”指的是“南至喜马拉耶、西至葱岭、北至阿尔泰,三大山脉环抱以内之土地。支那及朝鲜属于其中”[45]。在《中等东洋史》中,桑原对“东洋史”作了如下分期。
表1 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的历史分期

《中等东洋史》基本上依据中国历代正史之内容,援用欧洲世界史的历史分期与章节体之叙述体例,以汉族与周边民族的势力消长为主线,对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做了简要的概述[46]。如表1所述,桑原将东洋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个时期,并以各时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或人种为中心展开历史叙述。在空间上,《中等东洋史》描绘了自上古至19世纪末的三个“东洋”空间(图1)。
图1 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中的东洋

图1中的第一个“东洋”空间对应表1的“上古期”,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时期(以下简称“东洋I”)。东洋I由“中国”(汉族居住的中原地区)及其周边的“夷狄”构成。在东洋史的上古部分,桑原根据《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史记》等中国典籍,叙述了夏、殷、周三代的制度与王朝更替的历史,并记述了汉族与苗族等周边民族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儒家传统华夷秩序观念对桑原东洋史叙述的影响。在《中等东洋史》涉及周代部分的第三章《汉族与诸外族之关系及周代戎狄之跋扈》中,频频出现“中国”一词。桑原写道:“周代尤为跋扈者,实北狄与西戎。……周室衰微,西、北之戎、狄渐次侵入中国,周朝遂被迫东迁。”又称“东周之初,戎狄杂居中国者颇多”[47]。正如“戎狄杂居中国”“戎狄之猖獗”等字句所表现的,桑原以周天子为正统王朝的代表,将周边的“夷狄”视为入侵者或叛乱者。与中国的史书一样,桑原所谓的“中国”,不仅作为地理概念,指称汉族居住的中原地区,同时还是一个文化概念,意指代表中华文化的正统王朝。在空间上,东洋I是一个不对称的文化空间,即以“中国”为正统,并将其置于文化之最高序列,而将“夷狄”置于序列的最底层。桑原频频使用“中国”“夷狄”等词汇,乃是由于他长期接触中国古代典籍,“中国”“夷狄”等源自中国古人华夷意识的词语,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无意识地反映在东洋史教科书的叙述之中[48]。
第二个“东洋”空间对应表1中的中古期、近古期以及近世期中的清朝历史部分(以下简称东洋II),它由“支那”(或称“支那内地”)与“塞外诸国”两部分构成。前者指秦统一中国时的疆域,后者指蒙古、西域、西藏等周边地区。东洋II的地理范围,随着它所对应的不同时期而变化,在汉、唐、元三代中国国力的鼎盛时期,东洋II涵盖了中亚和西亚的广袤空间。在涉及拔都率领蒙古大军西征的部分,甚至包括了莫斯科、匈牙利与波兰。桑原在叙述东洋史时,既没有采用传统的基于王朝更替的循环史观,也没有采用为福泽谕吉等人所接受的欧洲中心的文明史观。桑原笔下的东洋史,是由众多民族在“东洋”这一大舞台上谱写的一部相互竞争的历史。尤其重要的是,与中国史籍不同,在《中等东洋史》中,这些民族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桑原以秦代至唐末为中古期,以契丹、宋、蒙古的历史为近古期,即为明证。桑原因蒙古人掌握了“争天下”的主导权,而将这一时期的东洋史视为“蒙古族最盛之时代”。同理,在属于“近世期”的清朝部分,桑原以大量篇幅叙述清朝的官僚制度与军事制度[49],而对清朝统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则很少涉及。桑原在题为《清代的官制与兵制》一章的开头部分称:“清自满洲而兴,先并蒙古,取支那本部,寻定外蒙古、图伯特(西藏)、天山南北两路,至有今之版图。清廷以何种官制、兵制,统辖镇压此广大版图?”显然,桑原更关心的问题是,清朝作为一个异族,是通过何种军事、政治制度来统治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之中国的。
《中等东洋史》的第三个东洋空间,对应于“欧人东渐时期”中清朝史以外的部分(以下简称“东洋III”)。在这一部分,桑原着重叙述了英、法、俄等欧洲强国为获得殖民地,在东洋III这一空间展开了激烈争夺、以及亚洲国家对此进行抵抗的历史。东洋III开始于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抵达印度,结束于1898年《中等东洋史》问世,跨越了“近古期”与“近世期”两个时期,时间跨度达4个世纪。东洋II中参与争天下的只是汉族及其周边民族,而在东洋III中,来自遥远西洋的欧洲人也登上了东洋这一竞争舞台。除此之外,迄今为止几乎未在《中等东洋史》叙述中出现的日本,也屡屡在有关台湾、琉球、朝鲜等叙述中登场。一如《露西亚侵略中央亚细亚》《英露两国之冲突》《后印度诸国之状况及法国之侵略》等章的标题所示,出现于东洋III的欧洲人,是以侵略者的面目登场的。涉及东洋III的叙述,字里行间强烈地体现出甲午战争后自封“东洋之霸主”的日本对于欧洲列强在亚洲扩大势力的警惕感。这也是《中等东洋史》与同一时期东洋史教科书的共同特征。
综上所述,在桑原骘藏描述的三个“东洋”空间中,东洋I与东洋II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亚细亚”各民族间的竞争之场,而东洋III则是在欧洲势力出现之后形成的“东洋”与“西洋”的对抗空间。其中,有关东洋II中提及的“民族”、尤其是北方民族的相关研究,后来发展成为日本东洋史学术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分支。
日俄战争前后,日本教育界一部分人批评东洋史课程人名地名过多,难教难学,甚至有人要求废除东洋史。大正初期,围绕中学东洋史课程的存废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有意思的是,争论双方在“东洋”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明显的对立。主张废除东洋史者,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斋藤斐章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历史教育应当重视学生道德观的形成,东洋史以中国史主,对日本而言,“东洋”已失去了作为文化典范的价值。显然,他们心目中的“东洋”是一个文化概念。反对废除东洋史者,以东京高度师范学校教授中村久四郎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为适应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军事扩张,有必要普及东洋史的一般知识。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东洋”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并不含有文化价值[50]。围绕此问题,上述二人的同事、时任东京高度师范学校教授的桑原骘藏,在《教育学术界》上撰文反对废除东洋史。他指出:
东洋史之目的,在于解明东亚之沿革。东亚、尤其是清、韩两国,自古以来与我国之关系最为紧密。解明其沿革,亦可间接了解我国之沿革。再者,无论现在或将来,东亚皆为我日本国民雄飞之地,因此必须通晓其民情风俗。由此二事推之,日本国民必须了解东洋史[51]。
桑原在这里列举了两点理由,强调东洋史教育的重要性。第一,历史上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第二,“东洋(即东亚,尤其是中国和韩国)”是将来日本在亚洲大陆的“雄飞”之地。比较桑原的第二条理由与那珂通世当初提议设立东洋史科目的,二者的用意是一致的。那珂与桑原都强烈地意识到日本在中国大陆的领土扩张,从而将东洋史的对象范围限定为“东方亚细亚”。然而,如后文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的势力范围超出“东方亚细亚”之后,东洋史的地理范围也随之发生了变化[52]。
1941年春,在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前夕,文部省教育局设立了东亚史编纂部,召集东京、京都两所帝国大学专攻东洋史的学者,着手编纂《大东亚史概论》[53]。在讨论“大东亚史”的编纂方针时,与会者对明治以来形成的“东洋史”框架提出了批评。究其根本,乃是“东洋史”背后的“东洋”概念,已经无法适应日本对外扩张的现实,故而显得不合时宜了。“大东亚史”编纂主任铃木俊指出,东洋史科目设立的初衷,在于强调亚洲文化相对于西洋文化之独立性与特殊性,然而,东洋史实际上只是从西洋史中去除亚洲部分,并加强了中国部分,其结果导致东洋史仅仅是“构成欧美世界史之一部分”。铃木指出:“如今,亚洲正在我国的领导之下建设新世界,朝向新秩序迈进。在此现状之下,理应打破西洋式的旧观念。”[54]有意思的是,此种观点不仅否定了东洋史以中国史为中心的叙事结构,甚至也否定了明治以来形成的新的“东洋”概念。“大东亚史”编纂成员之一、京城帝国大学副教授松田寿男说:“对我国而言,本来无所谓东洋与西洋。东洋应指美国,西洋则指支那以西地区。因此,要确立日本的世界观和世界史理论,就必须全面废除东洋史和西洋史之框架。”[55]值得注意的是,松田在此提出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即以日本为中心,日本以东地区为“东洋”,日本以西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为“西洋”。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三种“东洋”/“西洋”概念。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中国视角中的“东洋”/“西洋”概念,也不同于本文开头宫崎市定所说的将中国包括在“东洋”之内、与“西洋”相对应的第二种“东洋”/“西洋”概念。
文部省构想的“大东亚史”,是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它包括“以缅甸以东的东亚地区,是一部叙述日本精神起于最东方,渐次光耀该地区的历史”[56]。“大东亚史”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并不限定于亚洲,只要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相关地域,“即使不属亚洲,亦可按需处理”[57]。
“大东亚史”编纂过程中产生的第三种“东洋”概念,体现了空间思维的转换,它不仅否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的“东洋”“西洋”概念,也否定了与“欧洲即西洋”相对应的“亚洲即东洋”之地理观念。显然,随着日本的殖民扩张,明治时期形成的“东洋史”框架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三、中国东洋史教科书中的“东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废除科举制度前后,上海、江浙、两湖等地设立了许多新式学堂,近代意义上的教科书也随之问世。中国自古重视历史记述,史籍汗牛充栋,但多为数十卷、数百卷的鸿篇巨制,作为初学者的教材并不适合。日本的中学支那史、东洋史教科在新式学堂大受欢迎。其中尤以1899年上海东文学社刊行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翻译出版的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中译本《东洋史要》(樊炳清译)好评如潮。《东洋史要》在科举制度废除前就已被江苏、浙江等几个沿海省份用作中学堂的中国史教科书[58],后来又多次发行新版和重译本[59]。随着樊炳清译本的出版,“东洋史”一词在中国也广为流传。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写道:“日本人所谓东洋者,对于泰西而言也。即专指亚细亚洲是也。东洋史之主人翁,实惟中国。故凡以此名所著之书,率十之八九载中国耳。”[60]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在日本出版的东洋史几乎就是中国史的同义词。
1904年,清廷在废除科举的前夜,颁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等以日本教育制度为范本而起草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这一章程将历史定为重要科目,自小学起就设有历史课程。初等小学堂设“乡土历史”“历朝年代”(背诵历代王朝的名称);高等小学堂设“中国历史”;中学堂设“中国历史”(第一学年)、“亚洲各国史”(第二学年)、“中国本朝及亚洲各国史”(第三学年)、“东西洋各国史”(第四、第五学年)[61];高等学堂设“中国史”(第一学年)、“亚洲各国史”(第二学年)、“西洋各国史”(第三学年)[62]。中学“亚洲各国史”和“东西洋各国史”讲授中国以外的东亚各国历史。其中“东西洋各国史”包括“东洋各国史”与“西洋各国史”。1920年代中学设置“外国史”(世界史)课程后,“亚细亚各国史”“东洋各国史”随之消失,亚洲各国的历史被纳入外国史或世界史之中[63]。
清末和民国时期出版的东洋史和亚洲各国史教科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樊炳清译《东洋史要》为代表,不分中国史与外国史,将中国视为“东洋”的一部分[64]。清末就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将中国史视为东洋史的一部分,是将本国史与外国史混为一谈。某东洋史教科书的编者认为,强调应该区分本国史与外国史,“内国不得与外国等视,当另编之”[65]。另一部东洋史教科书的编者在序言中写道:
以前著译之东洋史,有为吾人所极不惬意之点,即彼常以东亚史为东洋史,或以中国史视为东洋史是也。日本人眼光中,以为东亚历史文明,专在中国。中国可为东亚代表,即可为东洋代表。吾人亦不必反对此议。惟吾中国人决不能抱此见解,以本国史混同东洋史。故今日所讲者,为广义之东洋史,即世界史中,与西洋史有平分之区域也。[66]
这位编者反对按日文中的“东洋史”概念,将中国史纳入东洋史之中,他认为,日本人编纂的“东洋史”以中国史为主,是因为他们以中国为东亚文明或东洋文明之代表。如果中国人也按此立场书写东洋史,那么原本应当属于外国史的东洋史就成了本国史,这将造成本国史与外国史的混淆。1935年,章赋浏在《东洋史》一书的开头部分,对东洋史的地理范围做了如下说明:“所谓东洋史,就狭义言,仅及亚洲的东部,除本国史外,只是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历史。就广义言,凡亚洲全部,无不包含在内。近世大都采用后说。故所谓东洋史或东亚史,实为除国史外之亚洲史。”[67]作者也基于区分本国史和外国史的框架,首先认为东洋史是外国史,所以不应该包括中国史;其次,日本位于亚洲东部,所以东洋史中理应加上日本史。其结果,东洋史实际上就是日本史和朝鲜史。除去中国史、加上日本史,作者的思路与明治时期日本东洋史中占主流地位的“单一中心论”并无二致。
清末以后出版的东洋史教科书,除去前述樊炳清译本及其转译本外,多数为此种不包括中国史的东洋史。后者又可分为两类,其一受中国历代正史四裔传的影响,按照与中国关系之亲疏,将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排列,叙述其地理、沿革、风俗及与中国中央王朝的关系;另一类则按照上古、中古、近世之历史分期,按章节体叙述中国以外的亚洲历史。
众所周知,正史四裔传以中国为中心,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排列,在每一个部分中,又按照与中国中央王朝关系之亲疏,叙述各国地理、沿革、风俗及与中国的关系。例如,《后汉书》按《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传》《南匈奴列传》的顺序排列。《东夷列传》依次记载高句丽、三韩和日本等国的风俗人情。然而,在清末民国时期出版的东洋史教科书中,只有柳诒征《东亚各国史》等少数教科书继承了正史四裔传的体例,将日本史置于朝鲜史之后[68],其余大多将日本史置于朝鲜史之前。以清末刊行的《东洋分国史》为例,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日本史,下卷为朝鲜史、安南史、暹罗史、印度史、波斯史,日本史占全书一半篇幅。对此作者做了如下说明:“现今东洋局面最有势力者,首推日本。故叙日本独详。日本明治维新,不独东洋之一大变局,实改变全地球之风潮者。故特详之。”[69]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说的“东洋”,已不再是中国视野中的东海或日本,而是涵盖亚洲东部的地理概念,包含中国在内。日本史占据全书一半篇幅,反映出时人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关注。
日本史在中国人编纂的东洋史教科书中占据重要位置,与癸卯学制确定的外国史教育方针也是相一致的。在《奏定中学堂章程》中,日本、朝鲜、越南等近邻国家是“亚洲各国史”的重点。《章程》要求讲授日本、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印度、波斯,以及中央亚细亚各小国的历史,强调应该将重点放在日本及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其他各国则可相对简略,并要求详近代而略古代[70]。此处应当留意的一点是,与中国历代正史四裔传不同,日本被列于朝鲜之前。这与癸卯学制“详近代,简古代”的方针不无关联。而朝鲜、安南以下各国的次序,仍与正史四裔传“由近及远”的编纂模式相一致。实际上,大多数东洋史教科书都是将除日本以外的各国与地区按照正史四裔传的方式并列处理的。
与此不同,另一类东洋史教科书突破正史的体例,按上古、中古、近世的历史分期和章节体编纂。以清末出版的赵懿年编《中等历史教科书东西洋之部》为例,该书是按照癸卯学制编纂的中学堂第四、第五学年使用的“东西洋各国史”。作者认为,东洋史是“同洲各国”的历史,但“东洋诸国分离散漫,贯穿为难。兹惟提挈大纲,示其概要。而事之仅关一家一国,无涉东洋大局者,往往略之”[71]。该书的历史分期与各个时期的概要如下。
(1)上古史。相当于中国上古(传说中的帝王帝喾)至东晋的时期。印度萌生宗教,文明自西北部向东南部延伸,法律、哲学得到发展,国家繁荣。朝鲜、大夏、安息国运盛衰交替,日本神武天皇统一全国。西亚大月氏、波斯、东亚高句丽、新罗、百济分别称霸。
(2)中古史。相当于中国东晋至明代中叶。印度文明经历黄金时代为伊斯兰教所灭,波斯为阿拉伯所灭。高丽统一朝鲜半岛,日本经历藤原氏专权、南北朝乱世,进入武人相争的幕府时代。
(3)近古史。相当于中国明代中叶至清乾隆朝。蒙古帝国统治中亚与印度,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分别占领印度西海岸和菲律宾群岛,并展开商业和传教活动。日本经历战国混乱后,德川氏统一全国。俄罗斯消灭蒙古政权,将势力扩张至库页岛。英国占领印度。波斯、暹罗、安南,分别扶植新王朝。
(4)近世期。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进入“东洋史上大变动”时期。英国与俄国在印度和中亚“为所欲为”,法国消灭安南。俄国与英国为争夺阿富汗而彼此对立,各国又与法国争夺暹罗。“东洋诸国”中唯有日本通过改革而崛起,统治了琉球、台湾和朝鲜。
和桑原的《中等东洋史》一样,赵懿年《中等历史教科书东西洋之部》一书也将东洋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个时期。但是,二者在上古史的划分上存在较大差异。如前文所述,桑原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作为东洋史中上古与中古的分界线,上古部分明显受到儒家华夷观念的影响。与此不同,赵懿年认为“东洋史即全亚洲的历史”,他根据朝鲜半岛、日本、印度、西亚这一广大区域中出现统一国家,以及文明之发达程度,划分东洋史的上古和中古时期。作者没有像桑原那样将蒙古势力的勃兴视为区分东洋史之中古期和近古期的标志,而是将蒙古帝国对中亚的统治与葡萄牙、西班牙势力的东渐相提并论。作者在重视地域广阔性的同时,又将彼此之间关联性较小的国家与地区的历史一并叙述,这一点与明治时期日本东洋史教科书的“多元中心论”相一致。在赵懿年的历史分期中,近世史以英俄势力在亚洲的扩张、以及欧洲国家间的对立为主要内容,暗合桑原《中等东洋史》中的 “欧人东渐”之近世期。
以1922年“六三三”新学制的导入为契机,中国的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清末以来的日本模式转型为美国模式。历史教育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合并“亚洲各国史”与“西洋史”,设置了“外国历史”(世界历史)科目;至此,清末以来的东洋史、亚洲各国史等科目,便从中学的历史课程中消失了。新学制下的外国史教育最显著的特征是强化欧洲史教育,中学外国史或世界史教科书基本上都以欧洲的古代、中世、近代史为纵轴,插入“印度的古代”“朝鲜与日本的开化”“明治维新”等为数不多的亚洲史单元。不但“东洋”一词在此类以欧洲史为中心的教科书中几乎销声匿迹,连频频出现于以往教科书叙述中的“东洋对西洋”“东方对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也被“中国对外国”“中国对西方”“中国对西洋”的新的二元对立框架所取代。例如,在1930年代出版的一部历史教科书之“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之比较”一课中,作者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之异同,认为后者的最大特征在于西方人信仰基督教,却没有妨碍由科学带来的物质发展。中国文化早在周代即已在伦理道德层面达到很高的水准,但由于自古以来中国人轻视物质层面的创造,导致了国运凋零。因此,复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是“研究科学、利用科学”[72]。
在“东洋”一词几近从教科书中消失的同时,由“东对西”向“中对西”的转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在“东对西”的结构中,无论“东”“东洋”还是“东方”,中国总被定位为其中的一部分;而在“中对西”的结构中,与“西”(“西洋”或“西方”)相对的是“中国”,以往包含在“东洋”“东方”范畴内的日本、朝鲜等“东洋诸国”或“东方诸国”,不知不觉便从世界史的视野中消失了。
虽然教科书中“东洋”一词的减少乃至消亡,意味着以中国为其组成部分的新“东洋”概念的式微,但是,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东洋”一词依然大量出现于各类报章杂志中。有意思的是,其含义不是指东西二元结构中的东方,而是中国传统语境中指称的日本。例如,随着日本工业产品的大量涌入,“东洋车(人力车)”“东洋布(日本产的机织棉布)”“东洋表(日本产手表)”等词汇常常出现在普通人的生活之中。每当诸如“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五卅事件”“九一八事变”等重大事件发生之际,中国各地都会发生抵制“东洋货(日本产品)”的运动。在民族主义情绪急剧高涨的抗日战争时期,“东洋鬼子”更是成为日本人的代名词。有一首题为《打东洋》的歌曲唱道:“卢沟桥,炮声响,难民逃亡到四方。没有吃来没有穿,日奔夜走苦难当”;“提起刀,背上枪,走上自卫的战场,争取民族的解放,洗雪国耻复边疆”。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这些铿锵有力的歌词激励了一批又一批民众奔上了抗日战场[73]。
“东洋”一词的此种用法,在文学作品中亦屡见不鲜。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主人公阿Q最看不起同村钱老爷的大儿子,这位钱大公子“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洋学堂”就是“西洋学堂”,即近代西式学校,而“东洋”指的是日本。从《阿Q正传》的“东洋”用例可以看到,尽管梁启超等清末士人将涵盖中国的新的“东洋”概念传入了中国,但其影响仅限于知识阶层,对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有产生影响。在普通人的心目中,“东洋”一词仍然意指日本。无独有偶,在中国近年出版的一些有关日本的书籍封面上,常常出现“东洋”这个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既陌生又新鲜的字样。如《照照东洋镜》(郭峰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又见樱花——一个中国女兵的东洋之路》(桃子著,长征出版社,2005年)、《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陈祖恩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7年)等等。在这些标题中赫然出现的“东洋”一词,所指称的也是日本这个中国的东方邻国。
在日本,包含中国与日本在内的“东洋”概念在明治时期定型之后,一直沿用至今,并未发生变化。《阿Q正传》有多个日文译本,包括藤井省三最近出版的日译本在内,所有日译本无一例外都将东洋译为“日本”[74]。对于今天的日本人来说,如果直接援用《阿Q正传》中的“东洋”一词来指称日本,将无法正确表达原文的意思[75]。今天,虽然中日两国都使用汉字,但原本产生于中国的“东洋”一词,在经历了多次词义移转之后,已经成为一个无法互译的词汇了。
结语
综上观之,在中日两国历史、文化诸多要素的制约之下,“东洋”概念几经移转,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东洋”和“西洋”在中国语境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分别意指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与印度洋一带。在19世纪,“东洋”一词在使用中出现了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亦指位于该海域的日本;其二则指包含中国、日本等在内的亚洲地区,与意指欧洲的“西洋”一词相对。本文主要以中日两国的东洋史教科书为线索,探讨了后者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语境中的语义变化,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涵义。概言之,在明治以降的日本,“东洋”一词不再指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或位于该海域中的日本,其地理空间扩大到亚洲,成为与意指欧洲的“西洋”一词相对应的概念,同时,“东洋”一词还意指包括日本、中国、朝鲜在内的“东方亚细亚”(即今人所称之“东亚”)。与此相一致,在甲午战争后日本中学设立东洋史课程之初,曾经出现过两种东洋史构想,一个是以整个亚洲为对象的“多元中心论”,另一个是以中国及其周边地区为主要对象的“单一中心论”。总体上说,后者构成了日本东洋史的主流,其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东洋史与其前身支那史一样,继承了江户时代重视中国史教育的汉学传统;第二,受到德国近代历史学的影响,日本史学界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亚细亚”的历史比之于相互间关联性较弱的亚洲各地区历史,更接近“科学性的历史”;第三,日本“东洋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自其诞生之日起,东洋史就背负了时代的使命,即为日本人“雄飞”于中国大陆提供有用的知识。在二战时期,随着日本军事势力的扩张,明治时期形成的东洋史框架被“大东亚”这一更为宽泛的概念所取代。
在中国,“东洋”一词原本意为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19世纪中叶以后,“东洋”成为专指日本的地理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文文献中出现了以中国为其一部分的新“东洋”概念,这与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等当时日本的中学东洋史教科书在中国的译介有直接关联。然而,当时大多数教科书都将“东洋史”定位为不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亚洲史或东亚史,而不像日本的东洋史那样“十有八九为中国史”。1920年代,东洋史与西洋史合并为“外国史”(“世界史”)后,欧洲史在中国的外国史教育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与受日本东洋史教科书影响之清末和民国初期的历史教科书相比,亚洲史部分所占的比例明显减少了。
由此可见,将中国视为其一部分之新“东洋”概念,虽然经梁启超等流亡日本的清末士人和留日学生之手被介绍到中国,并在一定范围内实际得到使用,但是,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新的“东洋”概念并没有取代以往的“东洋”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们仍然称日本为“东洋”。而且,此种传统的“东洋”概念在近年呈现出复活态势。
本文关于“东洋”语义变迁的考察从一个侧面说明,将模糊而多义的“东洋”概念从作为“西洋”(Occident)对立概念的“东洋”(Orient)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放回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可以为我们思考欧洲以外地区之“现代性”问题提供一个有用的视角。
注释:
[1]参见[日]仁井田陞:《東洋とは何か》,东京大学出版会(日本东京),1968年版。
[2]其典型观点认为,在近代日本,欧洲、日本、东洋三者处于非对称关系,“西洋”即欧洲是日本追赶的目标,而“东洋”(及“亚洲”“支那”)则是日本必须摆脱和克服的对象。Stefan Tanaka指出,Orient与Occident在欧洲原本不是对等的词汇,但明治时期日本的东方学者拔高了Orient的地位,将其与Occident对等使用,从而将日本与欧洲相提并论。Tanaka认为,在明治日本,“支那”代表古老落后的过去,衬托出日本的优越性(Stefan Tanaka, 〖WTBX〗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WTBZ〗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34)。此外,陈纬芬:《自我的客体化——近代日本的“东洋”论及藏匿其中的“西洋”与“支那”》(《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8号,2001年3月)、白永瑞:《“东洋史学”的诞生与衰退——东亚学术制度的传播与变形》(《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9号,2005年9月)、李圭之:《近代日本的东洋概念——以中国与欧美为经纬》(台湾大学政治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心,2008年)等研究,也注意到“东洋”“西洋”“支那”间的非对称关系。
[3]参见拙文:《中国における“亜細亜”概念の受容》,《東アジア近代史》第11号,2008年3月。
[4][日]宫崎市定:《南洋を東西洋に分つ根拠に就いて》,《東洋史研究》第7卷第4号,1942年8月,《宮崎市定全集》第19卷,岩波书店(日本东京)1992年版,第276页。
[5]山本达郎注意到,“东洋”一词所涵盖的地理空间,随着中国视角中“南海”范围的变化而变化,在元代,“东洋”指菲律宾至爪哇一带地区。见[日]山本达郎:《東西洋といふ称呼の起原に就いて》,《東洋学報》第21卷第1号。宫崎市定指出,“东洋”“西洋”概念,乃是将中国人所谓“四海”之一的“南洋”进一步分为“东南洋”“西南洋”而来,两者的分界线是以泉州或广州为起点的南北子午线,“东洋”一词后来才转为意指日本。见前引《宫崎市定全集》第19卷,第270页。
[6]关于近代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在东洋史学术领域成立过程中的定位,参见[日]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萤雪书院(日本东京)1940年;[日]杉本直次郎:《本邦に於ける東洋史学の成立に就いて》,《歴史と地理》第21卷第4号,1928年。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日本与中国除了“东洋”之外,也曾使用“东方”这一概念。“东方”是与意指欧洲或欧美的“西方”相对应的概念,中国与日本都被视为“东方”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与上述新“东洋”概念相合。本文主要以东洋史教科书为研究对象,故不将“东方”概念纳入讨论的视野。
[7][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第19卷,岩波书店(日本东京)1992年版,第275页。
[8]王尔敏:《近代史上的东西南北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1986年版,第111页。
[9]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自序》(雍正8年,1830年),台湾文献丛刊第26种,台湾银行发行,1958年版。
[10]同上,《东洋记》。
[11]徐继畲:《瀛寰志略》卷1《亚细亚·东洋二国》,道光28年〈1848年〉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12][英]慕维廉:《地理全志》卷之一《亚西亚州全志》(安政己未榴夏新刊,爽快楼藏版)。另外,美国传教士祎理哲《地球说略》万延元年(1856年)日译本中的东半球图有“大东洋海”(合众国袆理哲著述,大日本箕作阮甫训点:《地球说略》,万延庚申春晩新刊,东都江左老皀馆藏梓)。
[13]徐继畲著,[日]井上春洋、[日]森萩园、[日]三守柳圃训点:《瀛寰志略》卷一,文久辛酉(1861年)仲秋新刊,(日本大阪)阿阳对嵋阁藏梓。
[14][日]加藤祐三:《解説》,《飯塚浩二著作集》第2卷,平凡社(日本东京)1975年版,第504页。
[15][日]佐藤亨:《現代に生きる〓幕末·明治初期漢語辞典》,明治书院(日本东京)2007年版,第661页。
[16][日]新井白石:《東雅》,[日]市岛谦吉编辑·校订:《新井白石全集》第四卷,国书刊行会(日本东京)1906年版,第7页。
[17]《戊寅笔话〓第四卷〓第二十七话》(1878年3月3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62页。
[18]同上,第590页。
[19][日]津田左右吉:《東洋文化、東洋思想、東洋史》(1931年),《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8卷,岩波书店(日本东京)1966年版,第361页。
[20]《米欧使節派遣の事由書》,[日]芝原拓自、猪飼隆明、池田正博編:《対外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12卷),岩波书店(日本东京)1988年版,第23页。
[21][日]伊藤博文:《特命全権使節の使命につき意見書》,前引《対外観》,第29页。
[22][日]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の“発見”》,[日]貴志俊彦等編:《“東アジア”の時代性》,溪水社(日本广岛)2005年版,第47页。
[23]洪仁玕:《资政新编》(1859年),杨家骆编:《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 太平天国文献汇编》第2册,鼎文书局(台北)1973年版,第532页。
[24]张之洞:《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光绪29年11月26日),范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奏议·电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3-1594页。
[25]《地球大事记·比较英日势力》,《清议报》第47号,1900年。
[26]杨度:《游学译编序》,《游学译编》第1号,1902年11月。
[27]《俄国外交政策史》,《时务报》第48册,1897年。
[28]观云(蒋智由)《华年阁物语》,《新民丛报》第33号,1903年。
[29]那珂通世(1851-1908),近代日本蒙古史研究的开拓者。生于盛冈藩士家庭,自幼在藩校学习儒学,明治维新后入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学习英语。毕业后曾任千叶师范学校、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高等师范教授等职,1896年起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中国历史。[日]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伝》,故那珂博士功绩纪念会编:《那珂通世遺書》,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日本东京)1915年。[日]窪寺纮一:《東洋学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平凡社(日本东京)2009年版。[日]村上正二:《小伝 那珂通世——草創期の東洋史学》,《史学》第60卷第2-3号,1991年。
[30]《尋常中学校ニ於ケル各学科ノ要領》,《大日本教育会雑誌》第157号,1894年11月。
[31]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战后日本大学历史系设日本史、西洋史和东洋史专业,东洋史以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地区的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
[32]笔者查阅到出版于明治年间、以“东洋史”为书名的教科书计38册。最早的是明治28年(1895年)出版的儿岛献吉郎编《東洋史綱》(八尾书店,日本东京),最晚的是明治44年(1911年)明治中学会编《言文一致 東洋史講義》(明治中学会编著发行,日本东京)。
[33]例如,儿岛献吉郎编《東洋史綱》以整个亚洲历史为对象,除中国史外,还包含印度史和西亚史。但是,在该书中,中国史约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三。
[34]据福泽谕吉晚年回忆,他幼时曾在私塾学习汉学,仅《汉书》就学了四五年,他在课余时间读过11遍《春秋左氏传》,其中不少章节还能背诵。[日]福沢諭吉:《福翁自伝》,庆应通信(日本东京)1957年初版,1962年再版,第9页。
[35][日]那珂通世:《東洋地理歴史講義》第一回《総論》,《大日本教育会雑誌》第162号,1895年2月。
[36][德]里斯著:《史学会雑誌編纂ニ付テ意見》,[日]小川银次郎译,《史学会雑誌》第五号(1890年4月),[日]重野安绎等编:《明治史論集》第2卷,筑摩書房(日本东京)1976年版,第256-260页。
[37] Ludwig Riess, A Short Survey of Universal History: Being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Literature College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Fusambo, 1899, pp.2-6.
[38][日]藤田丰八:《書評·東洋歴史と東洋史綱と》,《大日本教育会雑誌》第172号,1895年12月1日。
[39]大久保利谦评论说:“明治时期西方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之引进始于里斯,完成于坪井九马三。”[日]大久保利謙:《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吉川弘文館(日本东京)1988年版,第103页。关于里斯与近代日本历史学形成之关系,参见[日]门肋祯二《官学アカデミズムの成立》,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歴史講座第八卷 日本史学史》,东京大学出版会(日本东京)1960年版,第170-176页。
[40][日]坪井九馬三:《史学研究法》,早稲田大学出版部(日本东京)1903年版,第46-47页。
[41]同上,第76-77页。
[42][日]藤田丰八:《中等教科東洋史》,文学社(日本东京)1896年版,第1页。
[43]桑原骘藏出生于日本福井县一个制造日本纸的商人家庭,189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桑原长期担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讲座教授,因《蒲寿庚事迹》获得日本学士院奖。东方学会编:《東方学回想Ⅱ 先学を語る(2)》,《桑原隲蔵博士》,刀水书房(日本东京)1999年版。关于桑原的学术研究及其中国观的研究,参见[日]小仓芳彦《桑原隲蔵全集から学ぶこと》(《アジア経済》第9卷第12期,1968年);[日]吉泽诚一郎《東洋史学の形成と中国——桑原隲蔵の場合》([日]岸本美绪编《東洋学の磁場》,岩波书店〈日本东京〉2006年版)。
[44][日]宫崎市定:《解説》,《桑原隲蔵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日本东京)1968年版,第767页。
[45][日]桑原骘藏:《中等東洋史》上卷,大日本图书(日本东京)1898年,第1-2页。
[46]正如该书开头部分所言,桑原对中国内地兴亡史的记述主要依据《御批通鉴》,涉及塞外沿革部分主要依据中国历代正史中的外国传,而印度及中亚部分则参考了欧洲人的著作。
[47][日]桑原骘藏:《中等東洋史》上卷,大日本图书(日本东京)1898年,第38页。
[48]桑原东洋史教科书中对“中国”一词的上述用法,一直持续到其晚年出版的东洋史教科书。参照拙文:《桑原隲蔵東洋史教科書とその漢訳テクスト——《東亜史課本》との比較分析を中心に》,《愛知県立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地域研究·国際学編)第43号,2011年3月。
[49][日]桑原骘藏:《中等東洋史》下卷,大日本图书(日本东京)1898年,第195页。
[50][日]奈須恵子:《中等教育における“東洋史”概念の展開——第一回中等学校地理歴史教員協議会の議論分析を中心に》,《教育学研究》第59卷第4号,1992年。
[51][日]桑原骘藏:《教育管見》,《教育学術界》第11卷第6号·第12号,(1905年9月·11月),《桑原隲蔵全集》第2卷,第521-522页。
[52]1928年,中学制度审议委员会、文部省审议通过了中学制度修正案,并定于1929年开始施行。按照该修正案的规定,中学东洋史的课时减少到只有西洋史的近三分之一。对此,桑原在《东京日日新闻》发表文章,认为实施该修正案将“对将来我国的国民教育产生重大不良影响”。[日]桑原骘藏:《東洋史の軽視——中等課程改正案の杜撰に就て》(《東京日日新聞》1928年10月2日·3日·4日),《桑原隲蔵全集》第2卷,第535页。日本于1944年战败之前进行了最后一次学制改革,规定东洋史与日本史、西洋史合并为“国民科历史”。与此同时,文部省编纂的国定教科书《中等历史》取代了以往使用的东洋史教科书。《中等历史》按通史体例展开,包含亚洲史、欧洲史、日本史。参见[日]奈须惠子:《戦時下文部省編纂中等歴史教科書における「アジヤ」認識》(《日本植民地研究》第19卷,2007年)。至此,由那珂通世提议创设的中学“东洋史”,走完了它半个世纪的历程。
[53]《大东亚史概论》是《国史概说》的姐妹篇,相关史料藏于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教育研究信息中心教育图书馆志水文库。
[54][日]鈴木俊:《大東亜史の意義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第六卷第四号,1943年4月,第1-2页。[日]小林元、鈴木俊等:《大東亜史の編纂 座談会》,《現代》第23卷第9号,1942年9月,第21页。
[55][日]小林元、鈴木俊等:《大東亜史の編纂 座談会》,《現代》第23卷第9号,第24页。
[56][日]宮崎市定:《自跋》,《宮崎市定全集》第18卷,岩波書店(日本东京)1993年版,第428页。
[57][日]鈴木俊:《東洋史と大東亜史》,《地政学》第1卷第10号,1942年10月,第43-44页。
[58]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序》,商务印书馆1909年初版,1911年第6版。
[59]实藤惠秀认为该书是日本人编写的历史书籍中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日]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くろしお出版(日本东京)1970年增补版,第258页。
[60]梁启超《东籍月旦》(1899年),《饮冰室文集》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2011年重印版,第98页。
[61]《奏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334页。
[62]《奏定高等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前引《学制演变》(见上注),第337-344页。
[63]总体而言,清末以后出版的以“东洋史”为书名的教科书为数很少,出版时间主要在癸卯学制发布前后,在体例和内容上受桑原《中等东洋史》等日本东洋史教科书的影响。民国时期,一部分师范学校和大学设置“东洋史”课程,编印了少量“东洋史”教材。如胡钧:《东洋史讲义》,法科政治门一年级,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南京图书馆所藏,未刊;王桐龄:《新著东洋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等。
[64]关于桑原东洋史教科书中译本的情况,参见[日]铃木正弘:《清末における“東洋史”教材の漢訳——桑原隲蔵著述“東洋史”漢訳教材の考察》,《史学研究》第250号,广岛史学研究会,2005年。
[65]秦衡江编译:《教科参考 东洋分国史》,《凡例》,育材学堂编译处校行,译书局代印,清末刊。
[66]前引胡钧:《东洋史讲义》,南京图书馆藏本,未刊,《例言》。
[67]章赋浏:《东洋史》,世界书局(上海)1935年版,第1页。
[68]该教科书由三编构成,第一编《朝鲜史》记述上古至日韩合并为止的历史;第二编《日本史 附琉球、台湾》记述从“古代倭人的开化”到明治以降的历史;第三编《南方诸国》概述越南、暹罗、缅甸、马来半岛、菲律宾的历史。见柳诒征:《东亚各国史》,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末刊。1930年出版的傅彦长编《东洋史ABC》一书,由印度、波斯、大月氏、朝鲜、大食、回纥、蒙古、西藏、日本及“余论”十章构成。该书第九章记述了自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岛原战争到明治、大正时代日本的历史概要。傅彦长:《东洋史ABC》,世界书局(上海)1930年版。
[69]秦衡江:《教科参考 东洋分国史》,《凡例》,育材学堂编译处校行,译书局代印,清末刊。
[70]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页。
[71]赵懿年:《中等历史教科书东西洋之部》,《总论》,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发行,1909年初版,1913年第3版,第1页。
[72]李季谷:《李氏初中外国史》下册(教育部审定新课程标准世界中学教本),世界书局(上海)1934年初版,1938年新第1版,第202-207页。
[73]韦简明作词、欧阳维鑫作曲:《打东洋》,《音乐与美术》第2卷第9号,1941年9月。
[74]鲁迅著、藤井省三译:《故郷/阿Q正伝》,[日]藤井省三译,光文社(日本东京)2009年版,古典新译文库,第88-89页。
[75]加藤祐三回忆说,当他第一次听到“东洋”一词在中国意指日本时:“作为一名东洋史学科的学生,我对此感到极为惊讶。”[日]加藤祐三:《解説》,前引《飯塚浩二著作集》第2卷,第497页。
转载自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论坛杂志社
作者:黄东兰,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