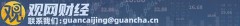结婚以后,第一次媳妇住在我家。早上,她起床出去看到客厅餐桌上放了一个红烧好的大肘子和若干馒头,回屋跟我说你妈真疼你,还给你带午饭。我懒松松的起床,进客厅,坐在餐桌前看了看桌子上的吃食,又懒松松的说到,这是我的早饭……!
活了半百,也记不清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能吃的,而且是很能吃。以至于小时候家人总是带我去东单三条儿童医院去检查我到底有没有甲亢。我觉得能吃应该是我在小学校队打篮球的时候开始的,那会儿是真的累,早上五点起床长跑拉筋骨,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基本不上文化课,一直在练球,练习间短暂的休息都是一下就瘫躺在操场上,不论酷暑或严冬,感觉再也起不来了。回家后,就风卷残云般的吃晚饭,能吃的能咽的,只要不是炸药全往嘴里送。到了初中,只能说无以复加了。一次,母亲包的羊肉包子,记得很清楚,一屉4个,一共蒸了8屉,32个手掌大的包子,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就全给吃了,吃完了我问母亲:还有吗?没吃饱!母亲完全惊了,看看我,再看看空盘子,仿佛在确认是吃了还是扔了。那次,我吃了全家人的晚饭。
我从来没把能吃当回事,只是觉得肚子总是饿。家里人也总是说要不去医院照照吧,看一下是不是我的肚子里只有胃,没有其它的,要不这些东西放哪呢?说能吃吧,但我不胖,初三时一米八的个头,体重一百斤,根本买不着裤子,要不腰围够了裤长不够,要不裤长够了腰围又太大。父亲当兵时的武装带基本可以在我腰上转两圈。就是能吃没办法,顺便花五分钱去灯市口东口红星电影院看个电影,别人三分钱买根冰棍了不地了,而我,带着十三个馅饼去的。
上班了,我收敛了一些,基本不让同事看到我能吃的样子,尽管如此,顺便吃吃就是双人份、三人份,还吃不饱。如果是遇到食堂吃肉,没谁了,食堂里的同事基本都会放下自己筷子,津津有味的看着我吃。慢慢的跟大家熟落了,就放开了一点。在单位,我有两个搪瓷盆,你没看错,也没想象错,是盆。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会收敛一点,用一个盆盛饭菜,外加一把西餐用的大号汤匙。如果赶上单位吃红烧肉,我就会带着两盆,一个盛肉,一个盛饭。吃肉绝对是件快乐的事,上小学的时候,家里不太缺钱,父亲当兵,一个月的收入大致一百块左右,七十年代就是高工资了,再加上母亲是高工,收入也不低。问题是,那个年代有钱不成,还要有粮本和肉票,才能买到肉,所以敞开吃的可能性不大,需要攒票。碰到机会买几斤肉就会红烧,做完后母亲总是在饭前先招呼我去厨房,给我盛上一海碗(旧时东北吃朝鲜冷面的大海碗,约等于现在汤盆),白嘴吃,我只要三五分钟结束战斗。之后,在煞有介事的盛上一盆放在屋里,等着姐姐们回来一起吃。
提干以后,我在吃上是很拘束的,想着咱儿也不能太丢人不是,大小宴请我在吃上基本与常人无异,但其实每次都吃不饱,一定会回家再大吃特吃一顿。一次,同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外出吃饭,两个人点了三个菜,一人一碗饭,席间二人谈笑风生,快吃完的时候,主任话锋一转说:“听说以前你很能吃,现在还行吗,如果行就表演一个看看”。话已至此,我也没谦虚:“行,但是菜要点我爱吃的,而饭我吃你点”。主任欣然同意,之后我又点了三个菜,两碗饭,开吃。每次添饭以两碗为准,之后在我吃到第十一碗,眼看要第六次添饭时,主任叫停了,并说:“行了,兄弟,就这样吧,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让服务员添饭了”!
还一次,去青岛,住在总督府,晚上吃总督府里的德餐,说是德餐,其实菜单里有德餐、日餐和中餐三类。最后,不算好吃重复点的菜,我吃了除主食外的整整一本菜单,服务员傻傻的看着我,一遍一遍的收拾桌子上空盘子。结账的时候,为我服务的服务员跟我说:“大哥,我在这干了七、八年了,你是我见过最能吃的中国人,有比你能吃的欧美人,但也屈指可数”。也是这次,我吃撑了,胃不舒服。我想我老了,可能今后都不能在这么为所欲为的吃东西了,那年我40岁。
有个朋友知道我能吃,就提醒我,岁数大了,能吃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加上青岛吃旅,我也反思,岁数大了是不是要控制,别再把自己吃死。但好像还没引起我足够的重视。
之后得了糖尿病(家族遗传,跟吃无关),去看大夫。大夫问我,多大,什么生活习惯等等,问后的结论是:没事,加强锻炼就行,不必担心。我就琢磨,这三百挂号费真好挣,两句话给我打发了,只好惺惺出门。拉开门把手,听到大夫又不经意的问:你吃饭好吗?我回头答:还行,能吃肉。又问:每顿米饭吃多少?我继续拉着门把手答:2斤吧!这次听到大夫急切的说:回来,坐下,仔细说。
之后,我被留院了。
住院可不是能让人高兴的事,主要是吃的问题很严重。内分泌科的饭应该是整个医院最难吃的饭,每顿饭大致的计量标准是,生叶菜一斤,肉一两,米饭一两半。天,这不是大夫要杀了我吧。我每顿饭都吃不饱,饿的时时刻刻低血糖,住院前空腹指标30,住院后不到4,天天都晕,下床的力气都没有。我抗争,带着病友出去吃饭。大夫说可以适当吃西红柿和黄瓜,我就五斤五斤的买,一气儿全吃掉。最终,医院营养科的主任急了,来找我,说我带坏了病房的风气…..!我勒个去,饿死又何妨,但我们要把实事说清楚!经过与营养科主任唇枪舌战,我争取到了把一斤叶菜换成三两肉,一两半的米饭可以外加一个小馒头,西红柿和黄瓜可以不限量。作为交换,我的药加量。最终,我跟主任捂手言欢。这也是在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里开先河了。
从此,我在吃上格外注意,尽量少吃。自己不能多吃就上网看别人多吃。
有段时间,经常看视频网站里的吃播,以我的经验来说,吃播里99.99%都是假的。这不是瞎嘞嘞,因为这些人基本不具备能吃的要素,就是快和不嚼。
平时,胃的蠕动比较慢,充血量低,在进食时,胃部开始充血,当充血一定数量后开始有饱腹感。也就是说吃得慢,没吃多少就会有饱腹感,大脑就会指示不在进食,即使进食味觉系统也工作的不那么热情了,所以,你会发现吃饱了以后的食物味道都平淡无奇。而吃得快的第一要素就是不咀嚼,或者尽量少的咀嚼。比如,我二十几岁一顿饭吃二斤煮白肉蘸酱油加上3.5升电饭煲的米饭(一斤米捞饭出饭约1.6斤,焖饭出饭约1.8斤,3.5升电饭煲满煲饭大约2.5~3斤米饭),总量在4.5~5斤,吃下去一般不会超过二十分钟,吃这些东西基本不嚼,就是生吞。
说白了,没等胃明白过来,已经吃了好几斤完事了。
而吃播不行,一般在一小时左右,这种速度吃几斤东西没可能,就好像让我放慢速度去吃,我也吃不了多少。还有就是,吃播一般吃完就结束视频了,让他坐那待一个小时,那他就废了。能吃的人可是吃完该干嘛就干嘛去了,没事人似的。另外,能吃的人是上下顿的这么吃,不是一天就一顿。以前我中午吃二十个馅饼,晚上继续二十个馅饼,不耽误事!所以绝大多数的吃播不可信。也有例外,比我能吃的人还是有的,我就见过朋友一顿吃两三斤挂面的,那东西吸水,煮好了得五六斤,半小时绝对解决完战斗。我比不了,我纯吃碳水的东西不灵,主要是吃肉。
吃的多不是本事,先天的条件。我更乐意吃遍天下,口气有点大。别人去某地游山玩水,我不,就是吃,在有限的时间里吃遍这个某地。当然,我也是讲情怀的,比如就喜欢去上海,顺便一个周末,想了,就飞过去,在丰裕去吃早点,阵仗很大,丰裕比较小,都是几个人拼桌,而我得占一张桌子。你想,丰裕里七八种浇头的面条总要一样一碗吧,几个口味生煎总要一样一份吧,再加上这个鸡那个鸭子的,总之一桌子未必够。早上去丰裕,白天就要去第一副食去买咸肉,回北京做腌笃鲜,味道美极。说的我又想去了。
吃遍天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到了一个城市,租一辆车随意地开,随意的吃,我从来不看大众点评什么的,直奔主题没意思,要自己找、自己碰,碰到了就像中了奖,那种兴奋溢于言表。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家里人吃饭就去酒店下的餐厅或者酒吧吃饭,我不,我自己溜达,溜达到了一条不认识的街道,街道两边全是很市井的茶餐厅,找了一家人比较多的,打包一盒卤肥肠盒饭,再走回酒店和家人会合,面对着维多利亚港夜色,他们吃着西餐,而我拿着盒饭,显得那么唐突违和。但不要紧的,我喜欢就好。说真的,盒饭里的卤肥肠味道好极了,上网查了查,原来是一家小有名气的店铺。像是中了奖。
我不是为“吃”辩驳,去到一个新地方,了解当地人文的最好途径,不是什么名胜,而是“吃”,越下沉越好。去个五星酒店吃东西,除了排面儿,没什么新鲜感,只有去了市井才有意思。就像去了成都、重庆去吃海底捞,一定是没吃药就出门了。到了成都、重庆必须是路边的大排档,恨不得光着膀子吃火锅也没人觉得不文明。疫情前去澳门,不知怎地,糊里糊涂的走到了澳门老城区,那里除了卫生还好,其他环境不如内地的农村整齐。但是,打开了我对澳门的新认识,窄窄的街道,在老电影里才能见到的古老的售卖形式的店铺,有意思,长长的胡同走累了,就在路边的小档口坐下,喝杯冰水,点上一碗鱼翅饭,炒凉瓜,总共五十几块人民币,漫不经心的吃着,看着形形色色的路人,看着店铺里店员用竹提子给买家从大缸里盛酱油。吃完,去老店铺尝尝干果杏圃,稍买一点,提在手里依旧是漫不经心的走在小街道,一边走一边吃。
看看,说着说着,从多能吃说到了情怀。情怀是一种人生阅历,是某一种寄托或是希望。从能吃到情怀,说明我已经从年轻走到了苍老,对“吃”已经从数量走向了内涵。“吃”的含义很大,可以是历史,可以是文化,可以是人生,我以上说的有些许片面了。现在,我15岁的儿子也很能吃,但比起我像他那么大时的饭量,儿子可是差远了。不过,这算是一个轮回,他的人生开始了,他还谈不上情怀,情怀只适合我这个岁数的人。
手机书写,如有不畅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