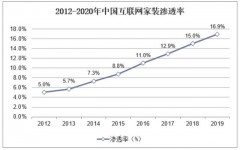此刻,阳光不错。冷,被关在窗外。越来越近的“年”走向我,忍不住浮想联翩。一个人敲打着键盘,想起四十几年前采购“年货”的种种,颇有点“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的可笑。
年货是什么?顾名思义,是过年的货品。换言之,只属于过年的吃喝用度。喝什么?没印象。反正没有饮料,应该有酒,白酒。参加工作后,在单位小卖部买过一瓶半斤装瓷瓶洋河。挺贵,还是同事刻意帮忙。犹记得当年老爸收到这瓶酒的大开心!

琳琅满目的小食
年货里,吃是大头。不是有钱就能买到,何况没钱。好在凭票供应,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虽然说是“革命化的春节”,过年,依旧保持了传统的味道。凭票供应,不是走去能买,而是买什么都要票排队。作为家中老大,这些杂七杂八的活儿,非我莫属。那就排吧。
买副食品,到扬州副食品商店,在今天的广陵路上。那是扬州最有名的副食品商店。虽然平时品种不多,各种糖果包含奶糖,好像一直有供应。每次带了弟弟妹妹走到那里,看他们眼巴巴的样子,会花一分两分买块糖,给他们吃吃。最便宜的糖球,一分钱四粒,彩色。
运气好排半天,运气不好排一天。采购回几乎所有要票的品种。主要是大金果、小金果和麻饼。是不是还有京果粉、桃酥,记不太清了。我的老外婆一个人独居淮阴,对扬州大麒麟阁的桃酥京果粉情有独钟。八十年代初期,我已经工作。有一年去淮阴陪她过年,带了京果粉与桃酥各两袋,她开心得不行,还拿去送给她的弟弟。那自豪的神情,如在眼前。

红红火火的期待
印象中最难排的煤炭。虽说“民以食为天”,没得柴火的城市,煤炭是唯一。现在的煤气、天然气和电磁炉,那时候听都没听过。煤炭是蜂窝煤。店里一台打碳机,骨笃骨笃不停地响,煤炭一个一个出来。一百斤煤炭券,对应多少只蜂窝煤,付钱后数数。排队的过程,很艰难。有一年遇到下雪,排了一整天才买到,头发都结冰了。
采办年货的时间,看运气。三五天至少了。临近过年那几天,腊月二十四的糯米饭,必须吃。那时候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糯米饭,原来是为了糊住灶王爷的嘴巴,让他上天述职的时候,不许胡说八道。自然,糯米也是排队买来的。
其实,那么多的所谓“年货”,都是平常的吃食。为什么非要在过年的时候,一次置办齐全?因为怕“过不去”年呀。过年、过年,为的是让年“过”去。
什么是过年?传说中的年,是个怪兽。它凶恶无比,能吞食无数巨大的东西。是饕餮?不,年不是饕餮!比饕餮更凶残。不过,它有明显弱点,这个弱点被我们的先人发现了。具体地说,年害怕红色与响声。

年夜饭的部分菜肴
看来,年对于吃物,是囫囵吞枣。否则鲜红的血,会让年避退三舍。人们对付年的办法有了:贴春联,燃爆竹。只有将年吓走,再来就是三百六十五天之后。这便是一年。岁月由此有了一年一年的轮回。年走了,庆贺吧。载歌载舞,锣鼓喧天!来了。
年,过掉了。随着年一起离开的,还有不顺遂、不安宁、不得意。重新规划,从头再来。年走后的空窗期,给所有的人以机会。
给孩子压岁钱,过年的仪式之一,庆贺孩子逃脱了年的口,长了一岁。据说压岁钱可以压邪祟,驱凶险。晚上悄悄放在孩子枕头下辟邪。压岁钱由此来。
年来的前一天叫除夕。“夕”,是年的曾用名。将夕除了就好!什么时候年才过掉?过了除夕夜。除夕夜,全家守岁,大人都不睡觉,担心睡着后,怪兽“年”过来害了家人。守岁的人,责任重大。为了不睡着,打牌、玩乐、看小戏,怎么愿意怎么来。所以说,大年三十除夕夜,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没有之一!
今天没有怪兽,没有“年”和“夕”要除要过,三百六十五天一个周期的“年”,不过是计算日子的工具。但是,美好的愿望没变。就像现在生活中不再缺少吃吃喝喝,却依然会在过年前,买回家好多有用没用的东西一样。

换一种风格的年夜饭
年货,承载了对于新一年的所有祈盼。顺风顺水的人,过年为了辞旧迎新;过得磕磕巴巴的呢?则希望在新一年到来后,将旧有的一切,统统清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每一个岁末年头更为浓烈。
年夜饭算不算年货?不一定。可是年夜饭是过年的黄钟大吕,最不能缺。扬州人善吃会做,除夕夜的餐桌上,少不了白斩鸡、八宝鸭、清蒸鱼、红烧肉、全家福!各种冷盘热炒,堆得层层叠叠。
对扬州人来说,既是年货又是必须的两道蔬菜为:清炒水芹和豌豆苗。豌豆,扬州话读“安豆”。水芹菜没有节,一路通到顶。两道平常的蔬菜,被赋予了极美好的寓意:新一年阖家平平安安、路路通顺!
春运已经开始。每年重复的故事,这两三年有了改变。疫情让不少城市又一次发出“非必要不出行”的通知。这个年,再一次有了不确定因素。或许,采购年货与阖家团聚的习俗,会因为疫情、病毒被改变也未可知。那么,年货,会不会成为不为人知的“过去时”?

春的祈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