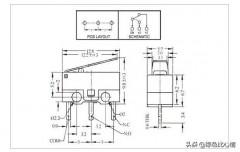好省食堂,一听这响当当的名号您就能知道它是大跃进时期的产物,“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多么响亮的口号。而当年的好省食堂也确实名噪一方,历史上有过超长的辉煌。当然,除了诸多必要的客观因素,主要还得益于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早年间的西城区二龙路人民公社位于二龙路南端路西的一个小院里(后来才迁至屯绢胡同),略向西是上岗、下岗,背后是小口袋胡同,好省食堂就在向北不远的师大女附中对面。大跃进时期,北京市的所有街道办事处全部更名为人民公社,这样的一呼百应不能不称作是件伟大创举。附近几条街巷的居民每天熙熙攘攘地穿梭于好省食堂,着着实实地在这儿吃了些日子的大锅饭,更称得上是国朝历史上罕有其匹的壮举。

说好省食堂得益于地理位置,则因为食堂立于人民公社的中心区,即二龙路西巷和王爷佛堂两个胡同口之间,南面不单有公社社址,还有派出所和西城分局,北面过了副食店则是区委区政府和法院、邮电医院,对面是师大女附中,周边还有不少中学小学幼儿园,这儿就不赘述了,反正单是琢磨琢磨也够热闹的,尽管搞不清楚当时有多少干部职工居民在好省食堂就餐,但想来也够那些八大员之一-----炊事员同志们忙活的。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无论咋回忆也记不清到集体食堂吃饭是凭本儿,凭证儿,还是凭卡了,何况我们住家附近另有一处食堂,就位于石驸马桥儿十字路口南边儿不远的一个院子里,所以只能记得家里不起伙了,锅碗瓢盆也大多贡献了(主要是指沾铁的家什包括我们院大门门簪上的吊件儿),每天三顿吃食堂倒也确是让人省却不少心。多少能有些记忆的是,曾有一段时间食物很充裕,据说是农业大丰收,快要到共产主义了,主食任您随便吃,米饭、馒头就盛在食堂的大笸箩里,只有大锅菜还要到窗口排除领取。只不过这样的日子并不长,随后就进入了供应紧缺年代,食堂基本瘫痪,人们不得不又回到家里自己起伙做饭,一些炊具也要重新置办,按票按本供应,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家的一只小奶锅还是抓票抓到的,按说当时用处不大,但因为是凭票,母亲最终决定买下再说。其后搬了两次家,母亲也没舍得扔,并经常将那黑黢黢的“钢种”锅做为我家忆苦思甜的实物教育素材。
我与好省食堂的亲密接触却是在自然灾害困难时期。
六零年,由于市面儿上供应匮乏,吃不饱饭及长期的营养不良,浮肿病开始在居民中流行。母亲和妹妹都得了这种病,我不知道现在医学上如何称呼,它的学名儿又是叫什么,不过当时只叫做浮肿病。记得我所在小学的班里,因病休假的同学竟达到一半以上,包括班主任老师。空荡荡的教室里许多无人的课桌被垛在了一起,本来的半日制也经常上自习课,一些淘气的学生虽然不敢跑出教室去,但总可以在课桌间钻来钻去,权当游戏了。

浮肿病人凭医院证明,按规定能够配给二斤黄豆,一斤豆面,以及每天早餐的豆浆,记忆已经不太准确了,大体好像是这样的。黄豆是拿捏不准如何吃法儿,大多让我们排在炉盘儿上或放在饼铛里烤熟当零食吃了;豆面比较难吃,也相对复杂一些,记得是先要将面炒熟,拌上古巴糖,或用开水“冲服”,或者干脆一把把地填进嘴聊以充饥了。
妹妹患病可以休假,但母亲却还得坚持上班。母亲当时的工厂位于西槐里,而领取早餐豆浆的地点恰恰就在好省食堂。母亲当然舍不得将豆浆自己喝掉,于是便命令我每天清早陪她走到好省食堂,领完豆浆后,她去上班,我回家与妹妹弟弟分喝这两份豆浆。
那时我上小学三四年级,对一些事情也似懂非懂了,在好省食堂的窗口领到豆浆后,我会劝母亲多少也喝些,但母亲通常会面色阴沉地说:“我不饿,赶紧回家去吧。”随后还要做出很匆忙状,并叮嘱我,注意汽车,特别要当心别把豆浆洒了。
由于是孩子,印象里的好省食堂很大,相当于如今的一个大会议室。食堂的操作间在西面,门和卖饭的窗口都向东开。食堂里摆放着七八张特大号的可折叠圆桌,桌腿儿就如同那时的乒乓球案子的木制折叠腿儿,可供多人同时进餐。食堂的水泥地很光滑,表明工作人员在工余时间里也非常地敬业。
还记得我家盛豆浆用的那只饭盒,因为直到后来我上中学时期还要用它带饭,盖子周边的接口地方已经破损,不是很严,如果走得过快,就可能“逛荡”出来。所以在打好豆浆回家的路上,我总会迈着碎步,走得小心翼翼。那时塑料还是稀罕物儿,塑料袋也从没见过,热饭盒只能放在玻璃丝网兜中,还要经常担心网兜是不是会被烫得断了丝儿。
这一时期大概经历了三到四个月吧,一切好像略微有了好转,浮肿病似乎被抑制住了,病人享受豆浆的待遇也就自然取消,好省食堂便从我的印象中渐渐淡化消失了,只是偶尔路过才会有所触动。
匆匆忙忙当中就到了八十年代初,社会上突然兴起了一股办舞会的热潮,请上四五个人的小乐队,架子鼓、电子琴、电吉他再加把小号,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甚至政协礼堂都在周末周日或晚上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什么三步、四步、探戈、伦巴,水兵舞,只要有票(基本是赠劵)就能玩到十一二点。
非常有幸的是有一次我得到的舞票却是在好省食堂内举办的。
它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辉煌和生机,据说它后来成为一家街道工厂的车间,或是临时仓库,因为给我票的朋友好像与这家工厂有些瓜葛。二十年的沉沦让它老迈寒伧了许多,特别是它根本没有我记忆里的那样大,就是与对面经常开舞会的师大女附中小礼堂也根本不能相比。

那天晚上,我一点儿兴致也没有,只是陪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望着似曾相识的老房子,在靠窗的椅子上坐了很久,想了很多。
又过了几年,随着建设拆迁,街道展宽,好省食堂已经奠基在楼群和街道的地下,连一丝痕迹也没有了,只是在一些人的记忆中,还会有那么一星半点儿的影子。
(转自老北京网)

阅读往期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