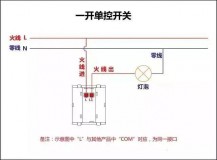初一到现在,整整5天了,息交绝游,关门闭户,捧着一本厚厚的《国学讲义》,在书房一目十行地随意浏览,何尝有半个字入脑入心?满架图书,曾经让我不止一次产生坐拥书城的快感,而今天,在共克时艰、抗击疠疫的关键时候,我却只能独坐书房,状如楚囚,不能尽缚鸡之力,还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了。
带着对之乎者也的鄙夷离开书房,我戴上口罩,走出小区,沿人行道向东郊的翁涧河走去。人行道两侧的女贞树,不知何时已挂满了黑色的颗粒,饱满圆润,像一串串墨玉珠子。
几天没出门,竟好像物是人非了。街上行人寥落,机动车也很少见。政府的三令五申往往在关键时候发挥重要作用。喜欢扎堆热闹的山城人很识趣地把自己隔离在家中:大家懂得,来自江城的这一场恶疾非同小可,真不敢当作一场儿戏。
瓮涧河并不远,步行十几分钟便可抵达。这是一条经过改造的城市景观河流。2019年春天,我曾经满怀喜悦写下一篇散文,赞叹这里鸟语花香的三春美景。今天才是正月初五,离花团锦簇时令尚早,两岸景致依然萧瑟。
蒹葭苍苍,流水潺潺,临水平台上坐了三个我熟悉的钓者,各自气定神闲,盯着自己的浮子。和往常不同的是,每个人都戴上了口罩。我对钓鱼是外行,并不理解他们垂纶的执着。这条河不像有鱼的样子,即便有鱼,也完全用不着这样的全神贯注。下这么大的功夫来钓鱼,性价比实在不划算。但他们告诉我,真正的乐趣并不在鱼本身,而在于那种聚精会神的期待和鱼儿咬钩的狂喜,当振臂起竿、悬鱼离水的瞬间,体验到的是一种真正的人生快感。
我在旁边静静地作了一会儿看客,然后无趣地离开了。在看客期待的目光注视下久无所获,对钓者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儿。更何况非常时期,他们也无意于和外行人作更深的交流。我开始诅咒这欺人太甚的新型病毒了,它让人们的活动空间大大压缩,而即使在偶然的相遇里,也不得不谨慎地保持着心理和生理的距离。
瓮涧河比邻文汇大道,路东是一块河滩草场,几十只羊悠闲地啃着干枯的草皮。忽然不知有什么情况发生,一群羊跑得四分五散。牧羊人严厉地吆喝几声,手中鞭子在空中挽了个S型的花儿,“啪”的一声炸响,又是几声吆喝,羊群便很顺从地往一块儿聚拢。
瓮涧河畔依然人心悠闲,岁月静好。时光如水,不疾不徐,保持着从容的节奏。
牧羊的鞭声,把我带回从前的老家,那是黄河北岸极普通的一个村落。冬春是较长的农闲时节,枯黄的堤坡和坎坷的堑壕里,常有三五成群的绵羊在乱莽中钻来转去,牧羊人则怀抱长鞭,旧棉袄一掩,躺在向阳的麦秸垛边做黄粱美梦,放任自己的羊爬高上低,构成一幅非常迷人而慵懒的田园风景。
农村的车把式和牧羊人都有一手甩鞭的绝技,旷原上时常传来清脆的鞭声。牧羊人刚才绕的那种S型的鞭花,其实并无技术含量,不过是起步阶段的练习作业,它最大的弊端是极易抽断鞭梢。牲口把式的鞭梢是非常讲究的,一般有筷子一样粗细,约有一尺长,梢端更细一点。最高明老练的打鞭是直接甩在地面上,一下接一下,不用在空中绕曲线,连珠炮般的声声炸响。
我的街坊中有个杨姓的老人,是全村公认的打鞭高手,那水平比《青松岭》里的李仁堂厉害多了。他的牧羊鞭是自己精心加工的,鞭梢专门选用狗皮做成。柔软耐用,还能避邪。有人看见,他傍晚赶羊群进村,狗皮鞭梢噼里啪啦,能在地上抽出火花来。有人向他求证,他神秘地说,只要打在妖怪身上,就能崩出火花,有时候鞭梢上还能看到血迹。
肆虐的病毒恰如阴霾笼罩,多么需要神鞭廓清妖氛!
刚才那一声响鞭,让我想到童年,想到老家,想到母亲。今年过春节原本是要把母亲接来城里过年的,农村冬天太冷,尤其过年期间的送往迎来显然让一个80多岁的老人力不从心。因此,近几年春节母亲都是在城里度过的。但今年我因为工作的原因,慢了半拍。等我忙完手头事儿,准备去老家接母亲的时候,防疫风声已紧,各种各样的断路堵村封城措施已经风行各地。
乡村派人村口值守,严禁外人和外地车辆进入;城里的小区横幅高挂,全部对外来人亮起红灯。这样的环境气氛无疑增加了把母亲接来的难度,但却和母亲不愿来城的心意正好合拍。老人反过来安慰我,不要再麻烦了。农村也通上了燃气,家里安装了壁挂炉,暖暖和和,一点也不冷。还有兄弟几个都在县里,随叫随到,用不着来回折腾。待在家里不串门,不走亲,自己不染病,也省得给公家添麻烦。
但哪有这么轻巧!毕竟是一场从未见过的传染病啊!
两岸的翠竹经冬犹绿,竹林间一条红色甬路向远处蜿蜒,像春天飞扬的五线谱。
我在九曲桥停下脚步,水面上两只红嘴黑水鸡忽然停止了嬉戏。尽管我与它们还有较远的距离,远远构不成威胁,但它们还是惊恐地掠过水面,拖起两道细碎波纹,逃进芦苇丛中去了。我怅然久之,十分怀疑自己的心绪一定凝结成可怕的面部表情,让这一对美丽的水禽望风逃遁。
我从东岸绕回西岸,在如意轩的石凳上坐下。1000多米的信天游,以我的脚力从来不在话下,但今天我却感到有些疲惫。郁闷不仅恶化精神,也消耗体力。打开手机,微信接收到一则官方通报,有个县新增一位确诊病人。那是我老家相邻的一个县,但直线距离离我们村更近。我的心又一次被牵引,想那一个寨堤环绕的小村,有东西南北4个入口,现在是否已封村闭户,严防死守了?
我从手机屏上抬起头来,看到不远处大田里有一位妇女,她坐在一个马扎上——马扎是那种能折叠起来方便携带的简易样式。身子随着她的动作轻度起伏,很专注地在采挖什么。——这里是去年秋天的一片葵花地,当时万朵金黄向阳盛开,我曾在这里拍下很多照片。葵花收获之后,留下茬地,涵养地力,等待春天的播种。
“你在挖什么呢?”我来到路边,与她保持两三米的安全距离。
“荠荠菜。”她边说边抬头,戴着浅蓝色的医用口罩,右手捏着两株锯齿状的大叶草。因为戴着口罩,声音便有了音箱一般的共鸣效果。
“原来碰到老乡啦!”我顿时惊喜。老家话别具特色,在豫西北方言中很容易识别。
“对呀,我也听出来啦!”她站了起来,显然和我一样兴奋。在新正初五的下午,在远离故土的城市,一个神情沮丧的孤独旅者,忽然听到久违的乡音,我布满阴霾的心里顿觉照进一缕亮色。
马扎旁边放着一个敞开的纸袋,那是超市里常见的金典牛奶的包装袋,里面已经有不少的收获。
“今儿个大年初五啊,你挖这干什么?”我有点纳闷。即使是勤劳的农村人,也极少在这个时候下地干活的。
“做饺子馅儿啊,这可是好东西。”看来这是一个开朗而健谈的老乡,即使带着口罩,也能看出来她的眉飞色舞。她从纸袋中挑出两棵做样品,开始讲她的荠荠菜。
春正月是采挖的最佳时机,再晚就长老了。洗净去蒂,用开水一焯,调成饺子馅儿、包子馅儿,真是一种绝佳美味。遭年景的时候,这可是农村的救命菜。眼下在农村不主贵了,但城里人却稀罕得要命。每年刚进正月,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城里人喜欢开着车到乡下的滩地坡上去采挖。但他们认不准,分不清,挖了半天,都是一些不能吃的丁刚苗啊、轱辘葱啊,劳而无功。所以就干脆从农民手里买。回到家里,换换口味。
异地遇故人,让我落寞的心里扫除了郁闷。她也不想再挖了,便坐在路边的连椅上拉起了家常。她和我同庚,来焦作30年了,退休前在一个区里工作。她指着远处隐约可见的两栋高楼,告诉我她家的大致位置。因为南水北调工程拆迁,旧家拆除了,她搬来离体育中心较近的住宅小区。
“过年怎么吃这个东西呀?”我指着她纸袋里的宝贝。荠荠菜再好,也不应在春节的食谱上啊!
她笑了笑说,这是给老伴儿、儿子提前准备的。老伴儿在江城负责一个项目,原本说回家过年的,因为突然有紧急任务,当地要加紧建一座疾病检测中心,年前打电话说不能回来了。儿子在郑州一家医院的呼吸科上班,年三十放假刚到家,板凳还没坐热,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连夜返回郑州在医院值守。现在他们家是三人三处过春节,焦作家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平时联系很少,大年初一早上通了电话报平安。他们说春节最想吃她做的荠荠菜饺子,但现在顾不上享这口福了,回来一定要补上春节这顿饭。
我告诉她,我住的小区离她家不远,恰成一条对角线。困在家里太无聊,来瓮涧河散散心。
她显然听出了我的担心和忧虑,话题变得认真起来。
“你还记得17年前那场‘非典’吧?多吓人啊!不是也过来了。”当时她和环卫处两个同事穿上防疫服,全副武装,背着一架喷雾器,严防死守一个村口,那是通往垃圾处理站的一条重要通道。所有的过往车辆、行人,一律登记造册,喷药杀毒。
“一个市直机关领导的车企图从这里闯关,我们几个挡在前面,决不通融。按规定把车前车后、里里外外全部喷洒消毒之后才放行。灾异面前,必须严格落实措施,一点也不能含糊。”她回顾着当年的战绩,依旧沉浸在兴奋之中。
她告诉我,别看中国人平时各有各的小九九,但一到关键时候,都能识大体、顾大局,人心齐,听招呼。这些年来,前前后后经历了多少大事难事,中国人都挺过来了。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大家听上级号令,按专家意见办,人人管好自己,照样会渡过难关。
“关键时候,人心不能垮!”她像是在提醒我,又像是在坚定自己。
在一个初次相遇的老乡面前,我开始感到羞愧,尤其还是年龄相当的一位女士。我觉得自己的消极情绪既无必要,也无道理。她的老公还在江城的建设工地上加班加点赶工期,那是灾异的核心区域啊!她的儿子还在省会医院里值守,面对成群结队的患者,那是最易感染的高危岗位!她孤身一人留在山城,默默筹备着特殊的美味,满怀信心地迎接亲人凯旋,这是何等的人生自信和精神强度啊!
暮色四合,她收拾物品准备回家了。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坚持要把采挖的荠荠菜分我一半。我推辞不掉,只好收下并再三感谢。她向我招招手,算是告别。然后沿着那条蜿蜒曲折的竹径,向桥头款款而去。
我看了看手中的荠荠菜,第一次想到它竟然与春天有关。苏词中的“春在溪头荠菜花”,应该就是指它了。但因为自己心田萧索,往往对春讯视而不见,忽略了垄头阡陌的缕缕生机。
收工的几位钓客经此路过,他们指着远去的背影问我:
“你认识我们区长?”
“区长?”我摇了摇头。
“就是她啊!与你说话那位。”他们告诉我,区长半年前刚办退休。
我顿时茫然。

作者简介
张丙辰,笔名阿丙,作家、诗人、教育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焦作市诗词学会会长。河南省杂文学会会长。历任焦作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温县县委副书记、焦作城市管理局局长,焦作市教育局局长,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原校长、党委书记。
出版有杂文集《阿丙杂文》《聚蚊录》《无章集》《锦上添足》《凭栏》《三余阁拟古》等书。2010年,其散文作品《缘》一文被收录进国家规划中职统编语文教材,成为当代文学的唯一入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