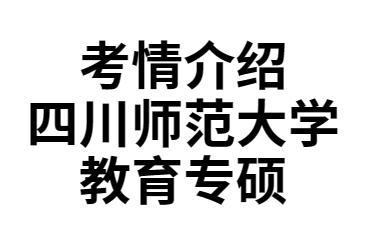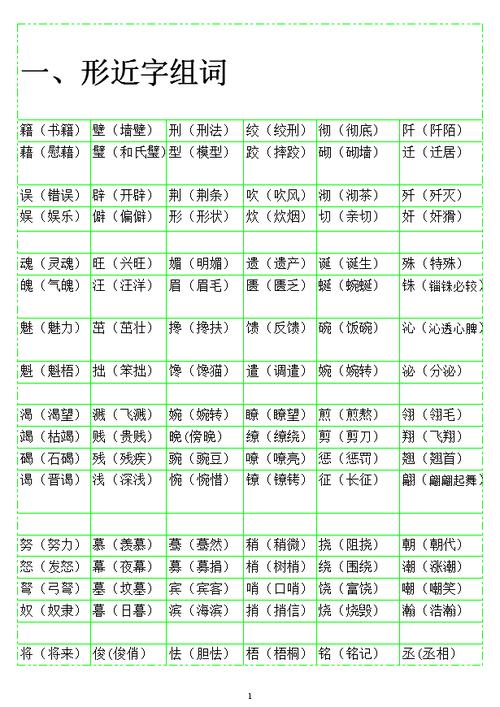许久之前,就看过《倾城之恋》了。也许,是把张爱玲的作品悉数看尽了的。只是,看了就忘的毛病,让我对它们并不存多大的印象了,只差把书名都给忘了。
这次,却又陷落进去了。这次,起源却不是《倾城之恋》这部文学作品本身,而是因了一部由它改编的电视剧。多少有些曲折的意味,兜兜转转却仍又绕回原处。
寂静的夜,看着他们演绎幻想。白流苏身着浅粉色的长袍睡衣,抚着颈颊幽幽守候。一场又一场的空,满满地溢出来。缓慢极致的节奏,悠扬舒缓的配乐, 没有胡琴咿咿呀呀的隔世苍凉,却多了情愫的暗自流动。她静静往那一坐,戏全在那些个仓惶湿热的呼吸、极力抑制的渴望、自持之下的缓慢步调、欲诉却似哑了般 的咽语半喉、猝然回醒的猩红脸颊与难以掩饰的失望之中。隔壁,范柳原一身白袍睡衣,枯坐电话旁侧。月色泛华,夜却如此漫长。一道墙壁,平白制造出几多的忧 愁,折磨了一双精打细算情感的男女。最后一夜,白流苏终就崩塌了无望守候,破灭了空寂幻想。电话线拔出,她径自切断几夜的守望,空泠泠地落荒而逃。范柳原 却终于拿起身侧的电话,对着没有应答的话筒,低低徐徐地告诉她,我想到你的房间,看看月亮。无法到达的声音充斥在流苏耳畔,她听到了,也听不到了。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不太适合的说法,却有那么一丝意味在其中,似乎有别于原著描摹的那几分市侩,多了一番真实的渴望与按捺。老派人的矜持稳重与过来人的直截了当,两者矛盾交杂,对情感的盘计却迫得他们原地踏步,谁也没能戳破那层薄薄的窗纸。
又翻回原著,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温了两遍。
她也听得见柳原的声音在那里心平气和地说:“流苏,你的窗子里看得见月亮么?“流苏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哽咽起来。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银色的, 有着绿的光棱。柳原道:“我这边,窗子上面吊下一枝藤花,挡住了一半。也许是玫瑰,也许不是。“他不再说话了,可是电话始终没挂上。许久许久,流苏疑心他 可是盹着了,然而那边终于扑秃一声,轻轻挂断了。流苏用颤抖的手从褥单上拿起她的听筒,放回架子上。她怕他第四次再打来,但是他没有。这都是一个梦——越 想越像梦。
直待白流苏第二次赴港,范柳原才终于走进她的房间,从那里看到月亮。
柳原道:“我一直想从你的窗户里看月亮。这边屋里比那边看得清楚些。“……那晚上的电话的确是他打来的——不是梦!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 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拨转身走到梳妆台前。十一月尾的纤月,仅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窗上的霜花。然而海上毕竟有点月意,映到窗子里来,那 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镜子。流苏慢腾腾摘下了发网,把头发一搅,搅乱了,夹钗叮铃当啷掉下地来。她又戴上网子,把那发网的梢头狠狠地衔在嘴里,拧着眉毛,蹲下 去把夹钗一只一只拣了起来,柳原已经光着脚走到她后面,一只手搁在她头上,把她的脸倒扳了过来,吻她的嘴。发网滑下地去了。这是他第一次吻她,然而他们两 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为在幻想中已经发生无数次了。从前他们有过许多机会——适当的环境,适当的情调;他也想到过,她也顾虑到那可能性。然而两方面都是 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始终不肯冒失。现在这忽然成了真的,两人都糊涂了。流苏觉得她的溜溜转了个圈子,倒在镜子上,背心紧紧抵住冰冷的镜子。他的 嘴始终没有离开过她的嘴。他还把她往镜子上推,他们似乎是跌到镜子里面,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去,凉的凉,烫的烫,野火花直烧上身来。
《倾城之恋》未完,我的心中,陈数却已是白流苏,黄觉也等同范柳原。电视剧的缓慢与铺张,只是奋力将张爱玲的寥寥几笔充盈成完整的故事,却着实冲 淡了主线。无复原本的精彩练达,却能够满足大众对情节的要求。我亦草草看了由旁杂延伸的冗长交代,只着重欣赏了他们的香港相遇。倒还谈不上相守的。着迷于 他们似有若无的期许,轻描淡写的拨弄,明里暗里的相持。他们相互试探,话说一半;他们彼此撩挑,迟疑不定。也许,他们真的都没有那么真心。到底,我看不 穿。
记住了那几夜。原著中,只一句话吧
“这是他第一次吻她,然而他们两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为在幻想中已经发生无数次了”。
剧中对这几夜空等、煎熬、幻想的呈现,却是花了大力气的,精致到位,亦别有风情。
再慢慢看吧,空了心思,看白流苏旗袍摇曳,低眉浅笑;看范柳原嘴角上扬,招摇风月。沉醉在,他们相会的每一刻。
也许是理解出现偏差,或者仅仅是程度有限了,好像更把这一出戏往最为简单真实的情感上去看了,没了张爱玲冷淩淩的犀利。
不可否认,她是文字的天才。只是,少了一些诗意。她不留情面地揭露男男女女的装腔作势、自私自利,我却宁愿相信尘世有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