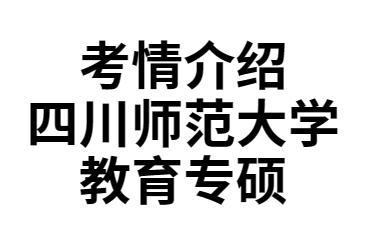一条清亮的小溪,看不见她是在流还是在静静地思索。她像个哲人,你不知道她有多深奥。
但是,我感觉得到她的动。
溪水里面杂草浮生,成群结队的小鱼虾在里面穿梭游戏,就像儿时的我们在村庄的院子里打闹那样,调皮而惹人爱怜。
溪边是一株株合抱大小的麻柳树。它们粗壮、枝条横生,围住小溪,阳光下来,斑驳的水面波光闪耀。春天,麻柳树的飞絮,铺满溪水面,而微风起处,花絮们还在纷纷扬扬,像雨像雾又像风。
小溪不远处,是一畦又一畦扬花的油菜田。雨后的早晨,蓝天下,油菜花的黄浸润在花瓣里的水珠之中,有蜜蜂伏在上面,不知是在采蜜还在戏水。这一片一片潮湿而又动人的云霞,像是镶嵌在川北丘陵的山水之上,让小溪变得油画或者梵高的向日葵般眩目。
既是小溪,当然有她美丽的“小”。宽不过丈余,深不过数尺,夏秋时节还可供少年游泳、打水仗。但溪水里面满是杂草,我们称它丝草。那是一种生长在小溪里的霸王草。它的丝条上长满锯齿,少年下去游泳的代价,往往是下肢被它割出一条条血印。
小溪畔,少年英俊的大哥,一身草绿色军装,手持钓竿,在拨开丝草的小溪水潭垂钓。菜花季节,鱼儿膘肥体壮,颜色鲜亮。我是他的忠实仆人,大哥专心致志钓鱼,一钩上来,鱼儿把钓竿弹成弧形,大哥极力往岸上拉,突然,那鱼儿挣脱钓钩,掉在岸边的茅草里,我猎犬般扑过去,一把卡住鱼儿的腮帮子,那鱼儿尚在我手上板跳,银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亮……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刻,看见我手里的鱼,大哥面有得色,“唰”又一竿飞了出去。
“看看你,笨死球了!”当然,也有我失手的时候,免不了大哥的一顿责备,“这条鱼肯定大!”
“气死球了!”或者大哥自己不小心把钓线缠在了麻柳树上,或者鱼儿钻进了丝草,鱼跑了,钓线、鱼钩也损失了,大哥也免不了着急一番。
雨后初阳的早晨,有水牛在河边吃草,有鸟雀在麻柳树上鸣啁,有早起的农人在菜花田间逡巡,有蓝色的炊烟在竹林院子里袅袅升起……于是,乡村四月便有声有色,美得让人颤抖。
这是一个梦境。四十年来,我都在极力地复制、下载,我想以我的笔力,让那个田园诗一般美丽的村庄,连同那条诗意四溢的小溪名扬天下。而四十年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志趣烟消,我才明白,那是一个奢望,是痴人的说梦,是一个活在我心底的传说。而不变的只是杂草的见证。去年,我回故乡时,特意去看了那条让我梦牵魂绕的小溪。但哪里有她的影子?横在我眼前的只是一条干涸的、杂草丰茂、宽不盈尺的沟。没了麻柳树的踪影,鸟语稀落,只有菜花还是那样灿烂而夸张地开着,一副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样子。
我茫然无措。这是我的故乡?那个曾经鸟语花香,小溪如画,恬淡自然的村庄?这条干涸的沟,是文明与自然成功减肥的结果?还是一条永远也无法愈合的刻在故乡与乡愁脸上的伤疤?
蓦然回首,大哥已是满头白发,沧桑扑面。兄弟的聚散,家庭的分崩,陌生的村庄,不由得我不望着蓝蓝的云天,吼一声:“时光他一去不回头!”这一声吼,痛也罢,不痛也罢,都让人刻骨铭心。
我在曾经的小溪边坐下来,顺手掐断一根芨芨草,白色的断裂处,立刻冒出了一颗水珠,像热恋时离别恋人夺眶而出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