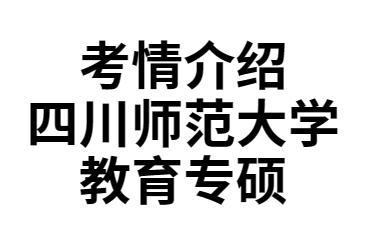留洋回来的振保在一家外商公司谋了个高职。为了交通方便,他租了老同学王士洪的屋子。振保留学期间,有一个叫玫瑰的初恋情人。
他曾因拒绝过玫瑰的求欢而获取了"柳下惠"的好名声。王士洪有一位风情万种的太太,她总令振保想入非非。有一次,士洪去新加坡 做生意了,经过几番灵与肉的斗争,在一个乍暖还寒的雨日,振保被这位叫娇蕊的太太"囚住"了。
令振保所料不及的是娇蕊这次是付出了真爱的。当她提出把真相告诉了王士洪时,振保病倒了。在病房,振保把真实的一面告诉了娇蕊--他不想为此情而承受太多责难。娇蕊收拾她纷乱的泪珠,出奇的冷静起来,从此走出了他的生命。
在母亲撮合下,振保带着点悲凉的牺牲感,娶了身材单薄、静如止水的孟烟鹂。新娘给人的感觉只是笼统的白净,她无法唤起振保的性欲。
振保开始在外边嫖妓。可是有一天,他竟发现了他的阴影里没有任何光泽的白玫瑰烟鹂,居然和一个形象猥狎的裁缝关系暧昧。从此,振保在外边公开玩女人,一味地放浪形骸起来。
有一天,他在公共汽车上巧遇了他生命中的"红玫瑰"娇蕊,她已是一种中年人的俗艳了。岁月无情,花开花落,在泪光中,振保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已是一种现实中的幻影。旧日的善良一点一点地逼近振保。
扩展资料:
关于红玫瑰的叙述,张爱玲在开篇就定好了基调:“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通,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这是一条原则,一种观念,一条栏杆,在整个故事,也就是佟振保的一生中,是具有统治地位的。从伦理和心理层面讲,振保与红玫瑰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在这条原则与振保之间拉锯的过程。
从”嫖娼”这一行径贯穿振保生活这一点可以透露出,白玫瑰与红玫瑰在振保的世界里,并不是显然的“是”与“非”的对立,而是“单数”与“复数”的对立,一个在婚姻主线生活以外浮游的欲望对象。
说得更清楚一点,因为是复数,所以是可以被其他人替代的。所以在整个上半阙,也就是关于红玫瑰的段落,张爱玲很密集地加入了巴黎妓女、玫瑰和娇蕊这三个角色。这也使得在与鹂烟成婚后,振保宿娼成癖才显得不那么突兀,毕竟照理说,他是刚刚结束了一段极为“沉痛”的恋爱。
却因为这种复数的、浮游的性质,他很草率地把娇蕊定位为一个替代品,即便在两人的蜜月期,也认定了这一条规矩,使得他自身即便意识到对娇蕊已经滋生出真情,却也可以视之为“身外之物”。
通过对振保与红、白玫瑰之间纠葛的解读,可以发现,在《红》中,振保的伦理之所以荒谬、可笑,并非由于他掩藏在表演人格下的趋利性。甚至可以说,这种趋利的伦理恰恰是在文中所肯定的,是娇蕊和振保所享受到的“犯罪”的乐趣,即使振保对于娇蕊的背叛也依然是出于类似的本能,为了让生活过得好一点,需要守规矩,在张爱玲看来是没错的。
但是振保却硬是把这种趋利上升到了威权的层面,要营造出一个“对”的世界,妄想在“沉重的时代”中,做自己的主人,就显得极端、教条,甚至弃自己的真情不顾,便渐渐滑入了可笑且可悲的境地。且最终因为自己的盲目),对自身处境缺乏领会,对欲望也缺乏规划,反而沦为了以嫖妓取乐也无家庭归属感的空空皮囊,半红、不白,调出来一盘脸色蜡黄的凄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