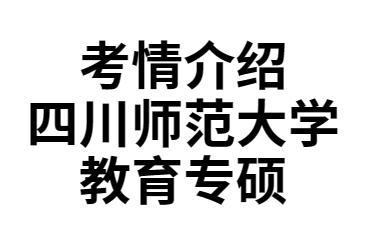《鸿鸾禧》讲的是一场民国时代大户人家标准而又盛大的婚礼。主人公是娄家的大公子娄大陆,待嫁人员是邱家长女邱玉清。二乔四美是娄大陆的二妹跟四妹,相应的玉清就是她们的大嫂了。
也许她们自己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恶意,不过是当姐妹间的一点谈资而已,但这背后实际折射出来的含义恐怕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罢。又或者她们早就知道自己以后的命运也会如此,所以才会这般放肆,在期限未到之前,一边肆无忌惮地取笑她们的大嫂,一边为自己还待字闺中而莫名庆幸。
一场盛大的婚礼,本应是喜事,人们看到的却是悲哀,就像是《留情》里面没有什么“情”,而《鸿鸾禧》里面也没有什么“禧”一样。总觉得有些不正常,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对劲。
或许我们从娄家老太太身上可以找到些许答案。
娄太太的婚礼
忽然想起她小时候,站在大门口看人家迎亲,花轿前呜哩呜哩,回环的,蛮性的吹打,把新娘的哭声压了下去,锣敲得震心;烈日下,花轿的彩穗一排湖绿、一排粉红、一排大红、一排排自归自波动着,使人头昏而又有正午的清醒,像端午节的雄黄酒。轿夫在绣花袄底下露出打补丁的蓝布短卦,伸出黄而细的脖子,汗水晶莹,与吹鼓手成行走过,一路是华美的摇摆。看热闹的人和他们合二为一体了,大家都被在他们之外的一种广大的喜悦所震慑。
虽然在这里作者说的是娄太太小时候看别人结婚时的样子,但我以为这实际上写的就是娄太太自己结婚时的样子。只有自己结婚的时候,这些描述、这些细节才会记得这样具体、这样深刻。试想别人结婚的时候,你还会那么认真的去记得这些琐碎的东西吗?大概能记得新娘长什么样就不错了,毕竟时间过去那样久了,已经三十年了。
那个时候娄太太对结婚和婚礼的喜欢是真实的,她就是需要一场这样的婚礼,这样的一种形式,你说她虚荣也好,说她贪图物质也罢,总之那一刻她是真真切切的欢喜。至于三十年后她才知道结婚并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后话了。
想必那个时候娄太太也不无憧憬过,有这样好的婚礼,那这婚后的日子应该也是不错的,怎么说她也是经过明媒正娶、八抬大轿迎进娄家的,这样好的开端,她还担心什么呢。只是她不知道,婚姻就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娄太太的婚后生活
1、为媳妇做鞋这件小事
娄太太一团高兴为媳妇做花鞋,还是因为眼前那些事她全部不在行,虽然经过二三十年的练习,至于贴鞋面,描花样,那是没出阁的时候的日常功课。有机会躲到童年的回忆里去,是愉快的。
因为对外面的事都不在行,而玉清暂时又没有买到合适的鞋子,终于让娄太太找到机会做一点她认为自己还在行的事情了。虽然做鞋的时候一样是紧皱着眉毛,看似满脸的不得已,但是她清楚的知道,只有在这里她才能找到某种快乐,不需要别人认可的那种,因为那是在她还未出嫁前就熟知的事情,她已经练就三十年了,没有谁在这方面能比她更精了。
当四美跟她说玉清的鞋子已经买到了的时候,她是一脸的失望,一只手连针线都舍不得撒,还别在大襟上,另一只手还拿着玫瑰红的鞋面。连这仅有的一点快乐也被剥去了,不禁让人想到《陈情表》里面那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样子,所以你让她“喜”从何来?
2、跟丈夫吵架那些平常事
娄嚣伯:“百忙里还有工夫去弄那个!
不要去做它好不好?
头发不要剪成鸭屁股式好不好?
不要穿雪青的袜子好不好?
不要把袜子卷到膝盖底下好不好?
旗袍叉里不要露出一截黑华丝葛袴子好不好?
不要这样蠢相好不好?”
这样近乎咆哮又不带情感的语气,作者却还说他只是焦躁的,商量式的口吻,并说他是出了名的好丈夫。这样反讽的艺术真是用到绝处了。
而面对嚣伯的咆哮,娄太太只是回了一句:“我做我的鞋,又碍着你什么?”
在她心里,只觉得是自己惹了丈夫生气,并且是因为旁边有人,她丈夫才让她三分的。若是旁边关心的人都死绝了,左邻右舍空空的单剩下她和她丈夫,那她丈夫便再也不会理她了,连吵架的机会都别想有了。
在旁人眼里,娄先生娄太太是一对错配的夫妻,多少人都替娄先生不平。娄先生早年在美国得过学位,是最地道的读书人,是个极其能干的人,最会敷衍应酬,长袖善舞。而娄太太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只不过是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三十年如一日的对待他,对待这个家。是以尽管娄太太知道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但还是一味的容让,生怕丈夫生气,到时连在这个家里生活的权力都没有了。
3、跟孩子斗嘴那些挫败事
娄太太:“瞧你这孩子这么没算计!把我那张床给了你罢,我用你那张小床行了。”
二乔三多四美齐声反对:“那不好。妈屋里本来并排放着两张双人床,忽然之间去了一张,换上只小床,这两天来的客又多,让人看着说娶个媳妇把一份家都拆得七零八落,算什么呢!爸爸第一个要面子。”
娄太太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有一阵温柔的牵痛,既心痛儿子也心痛钱,她考虑的是经济适用性,想为这个家里节省一点,精简过日子总是没错的。本来换张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在孩子们眼里,他们爸爸的面子比什么都重要,一句话就把娄太太说的哑口无言。这让她不免又心生挫败感。
而因为这个事丈夫对她又是一阵数落,说她怎么不早点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什么都要他来管。娄太太本来委屈得想怼他几句的,但又想到自己要做婆婆的人了,话到嘴边又硬生生的咽下去了。最后一个人躲到厕所里面哭去了,哭完便用水把眼泪冲走,这一刻她好像又把什么都甩开了。
做丈夫的要面子,做孩子的也一心只想着维护父亲的面子,她好像就不是这个家里的人,她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局外人。一个母亲做到这份上,是不是很失败?
4、与外人接洽那些糗事
娄太太又递了两筒茶叶过来,李太太极力推让,娄太太一定要她收下,末了李太太收下了,态度却变得冷淡起来。娄太太觉得这一次她又做错了事......
坐到该走的时候,站起来穿雨衣告别,还没走到门口就把雨伞撑了起来,出房门的时候过不去,又合上了伞,重新洒了一地的雨。
娄太太儿子结婚请的证婚人悄然离开了,他们不得不另请证婚人,于是打听到一个还算是小有名气的医院院长李先生,想请他来做证婚人。因为丈夫在办公室脱不得身,便要她自己去李家请人,这也是她可以外出拜客的机会,所以她欣然应允。
很显然这不是她的长项,送礼也没送好,觉得事情没做好后慌乱得连门都没出就把伞打开了。一点也不像她丈夫那样“长袖善舞”,使应酬成为了一种本能,观众都会不自觉的围着他团团转。
巴菲特说:“不要做自己不懂和不擅长的事,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做起来未必那样简单。人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做不了自己喜欢又擅长的事情,就像娄太太。她喜欢做女工,做得也好,可人家根本不需要,所以她做起来也没有意义了。而她不擅长的应酬,却是因为丈夫,因为家里需要,她又不得不去做。所以在这点上,人其实是很矛盾的,每个人都不能随心所欲的活着,都有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责任和担当。
娄太太回顾自己的一生
那天她看见的结婚有一种一贯的感觉,而她儿子的喜事是小片小片的,不知为什么。
有一种悲哀连她自己也说不清,可能人就是那样一种矛盾体,既希望躲在婚姻的围城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又渴望自己能做点什么有价值的事,得到他人的尊重。可实际上连她的孩子都嫌弃她,想尽一切办法试验她,发现她就是个没用的人。这让她觉得很气恼,但她又没有办法,因为要她去过穷苦的日子,没有机会穿戴整齐,拜客、回拜,她又会不快乐,所以就安慰自己说“繁荣、气恼、为难,都是生命”。
在她儿子婚礼举行完毕之后,他丈夫不过是向他媳妇问了一个极其简单又平常的问题:“结了婚觉得怎么样?还喜欢么?”全屋子人都只是象征性的笑了笑,而她却笑得最响,为什么?
因为她内心空虚,没有内容填充,只有用那最响亮的笑声来弥补这一切,这样才显得她好像还不是一个麻木得没有了知觉的人。
大概三十年前,她是绝不会料到今天会生活成这个样子的。只是她还算的上是一个比较看得开的人,没有为这不如意的现状而要死要活,她从容的接受了,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所以在她脸上表现出来的只是“麻烦,麻烦”,而不是悲伤。
在这里看来,娄太太比好些女人的境界还要高那么一筹。因为一个人最怕的是对现状无力改变,却又不肯坦然接受的样子。就像你对一个公司不满意,不是整天去抱怨这抱怨那,最好的办法是要么辞职不干,要么闭口不言。但大多数人却因此把自己活成了祥林嫂,既可怜又可悲。
结语
我们都知道“剧终”就是完结,是从此不会再来,就像生命只有一次,结束了就永远不会再有。而二乔四美却用这种近乎决绝的比喻来形容她们大嫂的婚礼,看似冷漠到不近人情的背后,却是因为她们早就从她母亲的身上看到了婚姻的结局:结婚很应该不是那么回事。
一场完美的婚礼并不代表就有一个完美的婚姻,婚礼只是你走进这场婚姻的形式,一场进门礼,并不是童话里说的王子和公主就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只是开始,婚后的生活才是真实的过程,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因为,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就像娄太太,幸与不幸,都是她自己的选择,与旁人无关。你想要靠他人过轻松优雅的日子,就得忍受他人带给你不习惯的一切;你要想自己心里活得舒坦,不受他人之气,就得踏踏实实靠自己的双手赢得尊重。
说到底,人生就是一场取舍,一番选择,全部的问题是要看你能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如果你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那么最终你也会屈服于这样的选择,并为之感到坦然,也就不存在幸与不幸的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