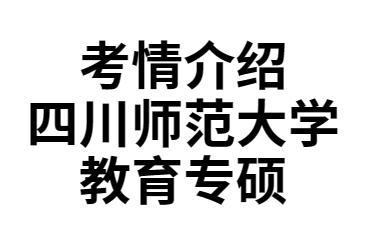在我国东北有座长白山,风景特别美,空气特别清新。长白山上的积雪,从来也不化,雪娃就住在山上。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春天、夏天和秋天,雪娃只能待在山上,好长好长时间都见不到小朋友们,雪娃真想他们。秋天了,雪娃用长白山桦树叶写了一封“树叶信”,请风阿姨捎给小冰娃。
喂,告诉你哟,雪娃和我(冰娃)成了好朋友。我们不哭泣,不撒娇,还不吵嘴;游戏玩耍,说悄悄话儿。几乎忘了吃饭;忘了上学;忘了做作业;都不知道孤寂和烦忧了。可开心噢!
怎么开心的呢,恐怕一两句话没法说清楚。你耐心等着,待我和风细雨地慢慢读来。
这天,我醒得特别早。没有赖床,也不要爷爷奶奶叫喊,就自个儿睁开眼睛了。家里还静悄悄的,一切都在沉睡中。
天啊,整个房间被映得雪亮!兴奋得我一忽地下床,从窗口眺望,外面竟是白茫茫见不到天的世界。噢,下雪了!洁白的雪朵儿还在不知疲倦的纷纷扬扬。我狠不得飞出窗去,与它们结伴共舞。
在我的记忆里还没经过雪天,因为我们江汉平原难得下场好大雪。只是听人们依恋雪天;只是电视里有雪天;只是书上画着雪天,便好生新奇起来。久久凝视,睁眼的天空,真美啊!
时儿有了大人的甜甜鼾声;时儿哐啷的有了响动,大人们起来了。他们也欣喜的惊呼:下雪了,好大雪哟!
奶奶把我穿得象企鹅;爷爷抢着送我上学。我都没太在意,任他们摆弄洗漱,就想快蹦出屋去看好大雪呀!
地是白的,树是白的,房子也是白的。天斧神工,一夜间将婀娜的荆楚装扮得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我一脚又一脚的踏下去,好不欢快。还躬下去抓一把,心里更是美滋滋的。在海绵似的地上留下一个个我小小的脚印。爷爷的大脚更厉害,也一前一后的蹬得更深。
踏着踏着,心里不知不觉地踏出酸涩味来。把块平坦而软绵绵的洁白地毯踩得残缺了。跟着踩的人更多了,还有了车辙的沟壑,让人心疼不已。看着好端端的雪地被践踏得乱糟糟的,我再也不忍心踩着它好玩了。干脆站着不动,看着小鸟们叽喳地在雪地里跳跃鸣唱;在树枝上跳跃鸣唱;在半空中展翅盘旋……
有人向我们投以莫名其妙的目光;也有人不屑一顾的匆匆而过,他们为什么不理解人呢。可爷爷终于等待不耐烦了,鼓起眼催;快走嘞,别野了。要迟到啦!
你象人家骑车去,准不会迟到了。我执拗说。
嗯嗯。爷爷从鼻孔里发出自嘲的笑声,又按捺着性子。是的,他这大年纪了哪能还骑车。也许他根本没猜到我的心思,还在故意逗我:是你上学要迟到了。
怎么,下雪天还上学去呢。我真不知道大人们是怎么思维的。不能让我们在雪地里好好观赏和自由吗!
爷爷不再吼了,要躬身背我。也许他心软了,认为人家孩子都有爸妈送,我没有。他在履行着爸妈的义务,这样依着我,疼爱我。我没有再使性子,还得上学,还得交了昨晚做的作业,让老师打红勾。觉得这样也好,我不会把雪地再踩坏了。我还是一点也不懂事,只管骑上去。
大街上,被早慌的人们蹂躏得不象样了,街中都裸露出了硬邦邦的水泥地。然而,他们人人个个几乎都很欣喜和得意。爷爷已经气喘嘘嘘,步子明显放慢,似乎要倾倒。可不,我背上还有一个书包,那快和我一样重了。我让他放下,走在水泥地上。
学校里也是喧闹一片,雪地也不象样了。看,那边还堆着小雪山;还有顽皮的男孩子在抓着雪坨,相互追逐投掷,劲头可足啦!但我心里在责怪他们,为什么没一个人象我要爱惜纯洁的积雪呢;也在心里矛盾着,不要响起上课铃声,禁锢了这欢闹的天真场景。
课间休息和往日不同,教室里一下跑得没人了,象风刮过的干净。我也掺和其中,飞了出去。在操场上,有同学在小雪山上加了个雪砣,还有同学更绝,一横两横的染上颜色。小雪山神奇的活了,成了有脸像的雪娃娃。同学们更来劲,喊着堆着,要堆更大的雪人。一个,两个,操场上都堆起好几个了。有老师瞧见,也显出难得的微笑。就称她们雪娃娃吧,因为,我家里有布娃娃做伴,我可喜欢她们了。现在又有了神奇的雪娃娃,不是更美好吗!
终于放学了,是奶奶来接我的。课堂上的描红书本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就没忘记雪娃娃。望着她们可爱的模样,不舍离去。奶奶用包着的热烘烘,香饽饽的烧红薯哄走了我。还说我们院子里有更俊的雪人。
回到我居住的院子,果然有小朋友在忙着堆雪人,劲头十足。我停下来,奶奶依了我。站到雪娃面前去,他们给她做了大眼睛,俊鼻子,小嘴巴。我学着同学的创造,有了自己的灵感,动手给她添上了耳朵,添上了辫子。雪娃更神气了,活灵活现起来。几乎在向我微笑,我也朝她微笑,一下有了我们共同的感觉。
积雪在人的智慧下产生了新的生命力,我不再痛惜人们把洁白的地毯给糟蹋了。洁白的积雪不再成为人们出行的障碍,还变成了洁白的雪娃娃,更招人喜欢。
朔风一阵紧过一阵,夹带着扎脸的雪扦,吹得我都呼吸不过来。几个玩耍的孩子被大人们叫回去吃饭了。他们是爸爸妈妈叫去的,让我羡慕,甚至差点伤心的落下泪来。然而,雪娃不仅没有爸妈,还没有爷爷奶奶。我不想让她孤零零的一人立在这,要陪着她。雪娃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柔和地说:“晶晶,回家去。吃了饭还要上学。别给爷爷奶奶淘气。”
开始我以为是呼啸的寒风让人产生的错觉,便四处张望。后来我听清楚了,明明白白是雪娃在说话,在和我说话。她怎么知道我名字的,还问我愿不愿意和她成为好朋友。我没有立刻回答,详端着她稚嫩的微笑。心想,布娃娃不会说话,再有雪娃做好朋友,一定是很高兴的事,就愉快的答应了。
她接着说:“晶晶,既然你和我是好朋友了,就听好朋友的劝。饿了吧,回家去,爷爷奶奶着急的。”
“不行!我回家了,丢下你一个人怎么行。这怎么算好朋友。”
“好朋友,不是让你陪着我受冻挨饿遭罪,是我们的心灵感应。”
对于好朋友的解释似乎雪娃更在理,但无论如何我还是不愿离她而去。便说:“要不你同我回家去。” 她听后淡淡地笑了,淡得我目瞪口呆。疑惑地问:“我说错什么了?”
不是。雪娃茫然了下,自言自语:“笑比哭好?”
也许她知道我无法带她回家;也许她不愿成为我的累赘;也许我不懂得在家里的温度下她会更难受;更也许是她替我考虑护着我。我怎么会这么笨,领悟不到自己的想法是得不偿失呢!
雪娃看到我愁苦的样儿,又微笑地说:“没什么,晶晶。你快回去吧。我会永远和你是好朋友的。”
为了不让雪娃担心难过,我装得开心的说:“雪娃娃,你再叫声我的名字,我就回去。”
“晶晶!”雪娃毫不犹豫地亲和地叫了,声音象幽静山间泉水滴咚的立体效果。
她的“晶晶(我的名字,冰娃是雪娃对我的称呼)”比爷爷奶奶喊得好听;比教师喊得好听;也比同学喊得好听,有点甜蜜的味儿,我喜欢听。可雪娃叫什么名字呢,我问她。她说:“还没谁给我取名儿。”
“你爸妈怎么不给你取名儿。我的名字是爸妈取的。”
“你爸妈有文化,名字取得好听。我是天生的,我爸妈也是天生的。我们都没名字。”
唉,我忘了,她原是没爸妈也没有爷爷奶奶。可她清纯的目光里没有一丝寂寞和遗憾。我忙笑着说:“我也是天生的。因为我爸妈去了很远的地方,他们的模样都记不得了。”
“那我们真该是好朋友了。”雪娃说。
我真的又高兴说:“你还是取个名儿。”望着她为难的样儿,我自信的说:“就叫你雪娃。”
“不行!那不是我的名字。那是我的身体。”雪娃坚定说。
一时让我陷入沉思,确实想不出更好的名字来。丫丫、巧巧,还有小小都是我布娃娃的名字;雯雯、惠惠、娟娟也都是我同学的名字;小勇、强强、大志是男孩子的名字,不能给雪娃取男孩的名字,那是名不符实。
“你不是很喜欢和我做好朋友吗?这名太好取了。”雪娃提示似的说。
我挠着后脑勺,想了想,也许她想让我叫她“喜欢”。便得意地说:“就叫你喜欢吧。”
然后,她却摇头了。是的,怎么能把喜欢一个人称着他的名字呢。我又使劲地想了想,又说:“喜喜”。她又摇头。再说:“欢欢”。她还摇头。没办法,干脆我倒过来说:“欢喜!”
“我叫欢喜!我有名字了,是晶晶给我取的。”雪娃终于高兴地接受了,简直雀跃地在呼喊。
这个又好听又美丽的名字,其实是雪娃自己给取的。但我还是为能给雪娃取了满意的名字而自豪。从此,我不再叫她雪娃,叫她欢喜了。
正在我们高兴的时候,爷爷跑来,喊了我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