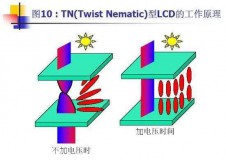哪有你这样你作者,春阳篇幅短小,确是抒情诗的内在律令。历史上,淳熟的格律诗大抵简洁。唐人五七律绝,八句,四句,宋词长歌慢曲鲜见超过二十句,遑论小令,再看波斯哈雅姆的四行诗,商籁体,更有日本俳句。帕斯就此曾经说:“由简单音节构成的诗,其复杂性决不亚于《神曲》或《失乐园》。”
诗集《西班牙三棵树》中我最喜爱的短章,是这首J J:十五年前阴凉的晨恍恍惚惚清晰的诀别每夜,梦中的你梦中是你与枕俱醒觉得不是你另一些人扮演你入我梦中
哪有你,你这样好
哪有你这样你
读罢,无言。再三再四读,总要一次次停下,犹如美好面容显现的那一刻,或在乐音间隙,给自己全然的静默。
诗的题目,是两个大写的英文字母的并置,成符号状,中有间隙——我与你。出声念,汉语没有这读音。汉语诗歌描述思念,经验丰富,作者借字母作题,于是和同类汉诗显现距离:矜持的距离。
十二行,字句轻捷,六小节,六十字。其中四字一句六行,占全诗行数半。第一节两行皆为四字一句,其余四节,每节的两句中一句是四字,第三、六节各以一个逗号,将其第一句断开。
前三节,分别用一个现代汉语的“的”,大体齐整,有规律。四字成句比较稳定,成语以四字为主,来源深远。《诗经》大多四字,四言诗的发轫,远早于五言七言,取效风雅,文约意广,比笙箫琵琶,四言如琴:十五年前阴凉的晨记忆的枝杪,流落生机,以眼前为结点上溯十五年。“阴凉的晨”,“晨”与“沉”同音,音节短促,轻击时光,停在彼时。
恍恍惚惚清晰的诀别诗文中的生离死别,多见,生而“诀别”,词语即显寒光。“清晰”对应“恍惚”,是这诀别的镌刻之痕,刻入时光。“诀”在“别”前,恍兮惚兮,“别”在“诀”后,刻骨铭心。
每夜,梦中的你梦中是你“每夜”……“梦中的你”,也多见,要紧的是下句,仅易一字:“梦中是你”,大伤恸,然而语气极轻,极轻,犹如梦中自语,几不出声——尤为悲恸,但悄无声息,诗人不用重音。
从“梦中的你”到“梦中是你”,“你”在第三节诗中连续现身,是不在场的“在场”,诀别后的“到来”。
与枕俱醒觉得不是你另一些人扮演你如我梦中
梦在枕,醒,是在枕上。“枕”何尝入梦?“枕”何来“醒”?何其触目惊心啊!“与枕俱醒”——有位俄国公爵曾对屠格涅夫念普希金诗句,然后说,假如能写出这样的诗,我愿割去自己两枚手指。
醒,残酷无情,“觉得不是你”。理智提示,“你”不在场,“觉得”,不是判断,是对梦的怀疑,然而不甘心,不甘心在梦中或醒来的一刻,“不是你”。
于是“另一些人”,注意:“扮演你入我梦中”。此下的诗句,便是“我”醒时的自语,还是关于“你”:
哪有你,你这样好
哪有你这样你
喃喃的结语,最后七字、六字,钻石般的光芒渐次闪烁,又如乐曲终了,重复的音节:“哪有”出现两次,“这样”出现两次,“你”出现四次,俱皆口语,平凡至极。在我们读见的汉语中,见所未见,在爱与思念的表达中,闻所未闻:
“哪有你这样你”——哪有“诗”这样“诗”!
是的,我们从未在汉语诗句中读到如此性状的表达——“你这样你”。相爱之人的全部关系,成为词语的关系、节奏的关系,直接成为诗,反之亦然。木心先生作诗,亟擅于使极度抽象与极度具象,不分离,“意义”即“去意义”,“无意”即“有意”。“你”,作为称谓,马丁.布伯称之为“原初词”,原初词一旦迸发,即玉成“存在”。假如我们视上帝为“永恒之你”,这首诗可否即是对信仰的确认?诗是人类试图跳出“我-它”关系而步入“我-你”关系的永恒挣扎,诗于焉成为存在的证言,“与你诀别”,“我”进入诗。
“诗在话语的空间相互追逐”(让.贝罗尔),作为语言中的语言,一首诗常被认为永未完成。木心先生的诗,总使我感觉有什么存活下来。绝好的诗在被写出的一瞬,神性显现,读诗人因之灵魂出窍。我们过去所能阅读的汉语新诗,依然存活在我们心中么?我常怀疑它们的作者是否写“对”了,竟或是否是“诗”。诗人,要看他运用词语焕发事物本真的魅力,也看他以事物的本真,如何焕发诗句的魅力,在木心先生那里,我看到,这是他天然葆蓄的能量,也是他轻而易举的能力。
帕斯:“为了体验一首诗,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它——把它变成一种回声、一片阴影,把它变成无。”
请再次阅读这首短短的小诗。
《木心诗七首细读》之一,自《读木心》,孙郁、李静编。广西师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