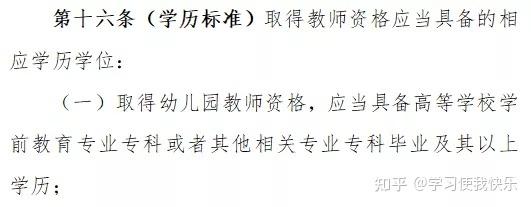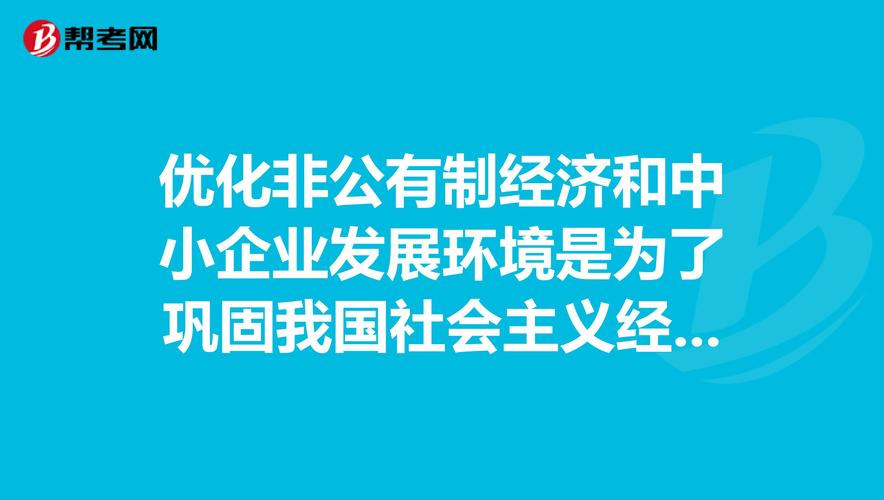罗志田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与中外关系史的领域中,研究成果尤为显著,在我国极具影响力。
而在他独特又深刻的视角中,巴蜀文化也呈现着不同的色彩。由于,他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一开始并不能认清作为巴蜀文化的独有特色,直到与一位游遍中国的美国老师进行交谈后,才逐渐了解到:原来四川人极为独立。巴蜀地区的人们,很有自己的见解,不会轻易地人云亦云,而巴蜀文化也是如此。
纵观全局,中国文化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它的特点是:中心稳定,边缘波动。而巴蜀文化,也同样遵循着这个准则,它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保持着稳定性,但是,也适度的容纳着外来文化。这种特性可以从三星堆到金沙的出土中看得出来,它拥有着自己的区域特色,与中原地区的特点截然不同。
但是,这些文化却又与中原文化有着丝丝入扣的联系。四川的整体地形是盆地,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四川人便时常抬头向上看,尽力地汲取来自四面八方乃至于头顶上传来的信息与文化。因而,巴蜀文化就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与生机。除此之外,巴蜀文化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关于《易经》的传统深厚而浓郁。
宋明理学家程颐,曾说过“易学在蜀”这句话,一直到晚清时期,张之洞来到四川,依然能随处可闻关于易学的谈论。这足以证明,易学早已深深的植根在了巴蜀文化之中。可能是因为四川人过于独立的思考能力,巴蜀地区的经学传统,一直很薄弱,不像中原地区和清朝的江南地区,发展得红红火火。
不过,从儒、道相争等方面来看,巴蜀地区的道家思想影响更加深远,所以,也必然会放弃一些儒家思想。
另外,巴蜀文化还包括文学方面的种种造诣,从古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到宋代的三苏;从现代的巴金到郭沫若,四川的文人们一直着力于创新文学题材与体裁。而且,风格千变万化,风骨各不相同,世人对于他们的评价,更是不得了。
我们可以看到,从早期到现在尽管中间被杀掉了那么多人,但是,最奇特也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天文、易学、中医,还有“文学”,等等。这些巴蜀文化原来的特点,都没有因为明末的杀戮而改变,直到到清朝、近代,仍然是这么一个传统。另一方面,四川地处边远,仿佛在主流之外也是一个持续的认识。
晚清张之洞到四川办尊经书院,就被不少人看作是近代的文翁。其实,中国本是一个诗的国度,在《诗经》时代,似乎是全民皆诗,弦歌之声不绝于耳,更是伴随读书人的行为特征。至少,唐宋时代,我们还是一个轻歌曼舞的民族。当诗文的追求与“斗方名士”挂钩时,传统其实已经发生了改变。
然而,正是这些不专以经史之人,却成为了传统文化最有力的维护者。
实际上,川人对所谓“国学”的看重,在清末民初可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清末有十多个省,办了存古学堂,而有些却在辛亥之前,便被本省的谘议局废止了,其余的也都在民国代清之后,被中央政府明令停办了。唯独四川不仅没有被废止,还想尽办法抵制了教育部的指令,转换各种名目,以“国学”的名义将其保持了下来,直接与今天与四川大学衔接。
而“独特”的代价,在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不入流”,使川人对别人来说,不过是脱口而出的“藐视”,非常敏感。籍贯在浙江的任鸿隽,曾任川大校长,而他的太太陈衡哲是湖南人,不习惯四川的生活,无意中说话伤到了川人,便引起了轩然大波。
之后,连川籍留学生李思纯也出来说话,挖苦陈衡哲虽为“洋奴”,却仅得西洋文化之表;甚至,进而攻击自己的老友任鸿隽学问欠高深,不足取信于社会。最后,任先生不得不辞掉了川大校长以息事宁人。这样的激烈反应,多少也带有前述“打老陕”的味道,并揭示出了川人的微妙心态:
“在生怕被人视为‘化外’的表象之下,正隐伏着四川长期被视为边远之地的事实。”
另一方面,巴蜀文化的独特,有时也因为外来文化而保持着更开放的态度。
如清朝旗人驻防全国都市,在南方留下持久影响的以成都为甚。而绝大部分南方人,多喜欢喝绿茶或乌龙茶,只有成都人爱喝花茶,这大概就是受旗人的影响。闲暇是茶文化的基础,也成为了今日成都文化的一个特色。此前的四川文化有此渊源,却不以此著称。
我们看过的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几千年旱涝保收。水稻从插秧到收割,其间,只需少量的劳作,所以,农闲的时间不短。然而,现在成都人讲求安逸,或更多是受清朝旗人的影响。因为,旗人有固定的钱粮,不富裕也不忧温饱,若自己不另求“上进”,可以终日闲暇。
在成都的茶馆里,众生平等,不特别强调茶的品级,一杯茶可以终日,是真正大众消闲的茶文化。或因吸纳了旗人的生活风格,今天的成都,不仅是南方大城市中唯一爱喝花茶的,也是中国所有大城市中保留闲暇最多的一个。
现今,这个人人都急匆匆赶着走路、忙着做事的时代,说不定,这便是中国仅有的一个讲究安逸的大城市了。对于那些要把赖汤圆、龙抄手做成麦当劳式联锁店的市场思维来说,慢慢悠悠恐怕已是落伍的表现,但对于不一定事事模仿的独立思维而言,能在匆忙的时代缓步徐行,或许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