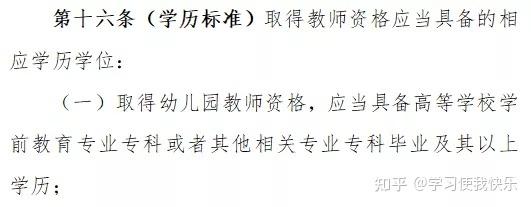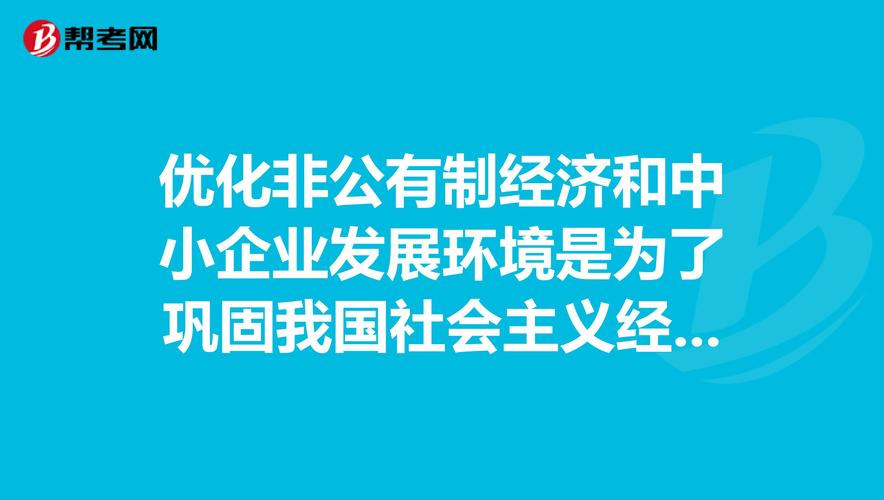奉法者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以私害法。慎子说:“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商鞅更从治乱两个方面分析了私与法的关系,他说:“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不以私害法,则治”。由于法是“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只有认真执法才可以发挥法的公平性价值。中国古代思想家多以度量衡器来比喻法的客观、公正、公平。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又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蜀汉诸葛亮严行法制,但并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如同诸葛亮所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其二,在上位者敬法、尊法、行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当时,太子非议商鞅变法,但因太子是君嗣,遂刑其师傅。结果秦人皆遵守法令不敢违反。“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汉文帝时,一人“犯跸”,文帝欲加以重刑,但廷尉张释之只判处罚金四两。文帝有所责难,张释之对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这一意见使汉文帝折服,由是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先河。与此相反,隋文帝时欲于“六月棒杀人”,这是违反汉以来秋冬行刑的传统法律规定的。因此大理寺少卿赵绰力谏:“季夏之月,天地长成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然而文帝却强辩说:“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此例一开,文帝逐渐走上了“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的毁法之路。既然皇帝以言代法,法外施刑,官吏们也窥察圣意,构煽大狱,陷害无辜。史书曰:“每有诏狱,专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数”;“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从而埋下了隋二世而亡的危机。
其三,法贵诚信。古人将信与诚联系在一起,所谓“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国家的法律政令重诚信,才具有权威性,所谓“政令信者强”。商鞅变法时主张信赏必罚,他说:“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唐太宗为了惩治官吏假冒资荫,曾欲重惩一假冒资荫的司户参军。大理寺少卿戴胄依法谏阻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他希望太宗能够“忍小忿而存大信”。最后唐太宗终于被说服了,他表示:“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宋代王安石曾经赋诗赞美商鞅信赏必罚:“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其四,治法与治吏相结合。治法指的是制定良法,治吏指的是选任贤吏。治法与治吏并重,就是选任贤吏执行良法,二者缺一不可。唐时,白居易面对中唐以后法纪败坏、奸吏迭出的乱象,发出了“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之慨叹。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没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一大批贤吏严于执法,《贞观律》也很难实施。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一书中,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单纯任法“未足以治天下”,是“治之弊也”,但只任人而废法,则是“治道之蠹也”。结论就是“择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进长者以司刑狱,而使守画一之法”。五四运动时期,我国共产主义先驱者李大钊,很有现实针对性地阐述了法治与人治的统一性,他说:“国之存也,存于法,……国而一日离于法,则丧厥权威。”但“若惩人治之弊,而专任法律,与监法治之弊,而纯恃英雄,厥失维均,未易轩轾。”他一方面强调:“溯本穷源,以杀迷信人治之根性,……盖此性不除终难以运用立宪政体于美满之境;”另一方面又阐明了“法律死物也,苟无人以持之,不能以自行”,“故宜取自用其才而能适法之人。”可见,治法为本,治吏为用,本用结合,即法与吏的统一,方能收到良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