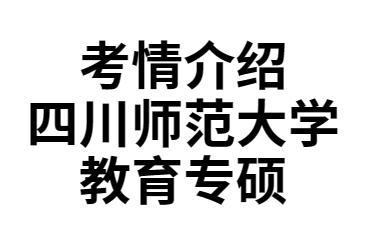1.
妮可是广东人,长得像蒙奇奇,蛮甜。她是高级日语翻译出身,日语说得比普通话流利。2000年年初,她独行西藏,然后定居拉萨当导游,专带外籍团,同时在拉萨河畔的仙足岛开小客栈,又在酒吧兼职会计。当年,她在我的酒吧当收银员,我在她的客栈当房客。
那时拉萨仙足岛只有四家客栈,妮可的客栈是其中一家。客栈没名,推开院门就是拉萨河,对岸是一堆一堆的雪顶小山包。我和一干兄弟住在妮可客栈的一楼,每天喝她煲的叫不上名字的广东汤。她喊我哥哥,我常把房间弄得像垃圾场,她也一点儿都不生气,颠颠地跑来跑去帮忙叠被子清桌子,还趴在地板上,从床底下掏我塞进去的酒瓶和棉袜。她把我们的衣服放进大盆里,蹲在院子里吭哧吭哧地洗,我蹲在一旁吭哧吭哧地啃萝卜。
我边啃萝卜边问她:妮可妮可,你们客家姑娘都这么贤惠吗?妮可龇着牙冲我乐,我也龇着牙冲她乐……真奇怪,我那时候居然一点儿都不脸红。她说:哥啊,你真是一个大少爷。
拉萨是日光城,十点钟晒出去的满院子的床单,十二点钟就干透了,白床单随风轻飘,裹在身上贴在脸上全是阳光的味道,怎么闻也闻不够。
真好闻啊!我每天睁开眼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满院子跑着抱床单闻床单。我一蹿出来,妮可就追着我满院子跑,她压低声音喊:哥啊,你别老穿着底裤跑来跑去的好不好?会吓到客人的。
我不理她,自顾自地抱床单,抱得不亦乐乎。
有一回到底是吓着客人了。那天阳光特别好,飘飘然的白床单像是自己会发光一样,我一个猛子扑上去抱紧,没承想一同抱住的还有一声悦耳的尖叫。太尴尬了,床单背后是个日本妹妹。
那时候流行穿超人内裤,日本妹妹掀开床单后被超人吓坏了,一边哆嗦一边连声地喊:苏菲·玛索、苏菲·玛索。然后刷地给我鞠了一个躬。
我连滚带爬地跑回去穿长裤,然后向她赔罪,请她吃棒棒糖。她估计听不懂我说什么,讪讪地不接茬,我跑去找妮可学简易的日语对话,抄了半张A4纸,我也不知道妮可教我的都是些什么,反正我念一句,日本妹妹就笑一声,念一句就笑一声。
很多年之后,我在香港尖东街头被那个日本妹妹喊住,她的中文明显流利了许多,她向她老公介绍我,说:这位先生曾经抱过我,我想跑,没跑成。她老公特别开心地握着我的手。我请她和她老公以及他们家公子去半岛酒店吃下午茶,她老公点起单来颇具土豪气质,我埋的单。
临别时,已为人母的日本妹妹大大方方地拥抱了我一下,她说:再见啦,超人先生……
2·
秋有凉风夏有月,拉萨的生活简单而惬意,并无闲事挂心头,故而日日都算是好时节。和单纯的旅行者不同,那时常驻拉萨的拉漂都有份谋生的工作。妮可除了开客栈,还兼职做导游。
当年来拉萨的穷老外太多,一本《孤独星球》走天涯,人人都是铁公鸡,妮可的导游生意常常半年不开张,偶尔接个团都像中了彩票一样。每当她宣布接到了团,整个客栈都一片欢腾,然后大家各种瞎忙活,瞎出主意,这个给她套上一件冲锋衣,那个给她挂上一个军用水壶,大家都把自己最能拿得出手的物件贡献出来,逼着她往身上挂。那个时候,我身上最值钱的是爱立信三防大鲨鱼手机,也贡献出来给她撑场面。每每她满身披挂地被我们推出门,捯饬得比游客还要游客。她的手抠着大门不撒开,笑着喊:不要啊……只是去布达拉宫而已啊。
布达拉宫门票贵,我们都不舍得花那个钱,妮可是我们当中唯一进过布达拉宫的。她的导游旗是最特别的,登山杖挑着一只爱立信大鲨鱼手机,后面跟着一群日本株式会社老大叔。
那时候,我们在拉萨的交通工具是两条腿加自行车,偶尔坐三轮车,万不得已才打车。拉萨的出租车贵,在北京起步价7。5元钱的时候,拉萨早就是10元钱了。我的印象里大家好像都不怎么打车,再远的路慢慢走过去就是,心绪是慢悠悠的,脚下也就用不着匆忙赶路。
我的印象里,妮可只打过一回车。
有一天下午,她像只大兔子似的蹦到我面前,摊开手问我借钱打车。我说:借多少?她说:快快快,150元!我吓了一跳,150元钱都可以打车到贡嘎机场了,一问她,果不其然。
妮可带团的客人掉了个单反相机盖,她必须在一个半小时内赶去机场才来得及交接。我问她是客人要求她去送的吗?她说不是。
我说:那客人会报销你的打车费吗?
她说:哎呀!哥哥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
我乐了,好吧,这不是钱的事,这是算术的事好不好?打车去贡嘎机场150元,返程回来又是150元,这还不算过路费……我拗不过她,陪她打车去贡嘎机场,计价器每跳一次我就心痛一下,我算术好,十几斤牛肉没有了。
丢镜头盖的是个大阪大叔,我们隔着安检口把镜头盖飞给了他,机场公安过来撵人,差点儿把我们扣在派出所。返程的钱不够打车,坐机场大巴车也不够,于是我们走路回拉萨,走了十里路才拦到顺风车。
司机蛮风趣,逗我们说:你们是在散步吗?
我一边敲妮可的脑袋,一边回答说:是,啊,吃,饱,了,撑,得,慌,出,来,散,散,步,喽,啊,哈!我说一个字敲一下,说一个字敲一下。
后来那个丢镜头盖的大阪大叔邮寄来一只招财猫,算是谢礼,我把那只猫横过来竖过去掏了半天也没掏出来我那150元钱。
十几斤牛肉啊。
3·
2013年除夕,妮可来找我过年,我们一起在丽江包了饺子,那里有我另外一个世界的另外一群族人。
我们喝酒,弹琴唱歌把嗓子喊哑,12点钟声敲响时冲到门口放鞭炮,满世界的喜气洋洋,满世界的噼里啪啦。我醉了,满世界给人发红包。发到妮可时,我敲敲她的脑袋,问她开不开心啊,喜不喜欢丽江啊,要不要留下来啊?
她坐在门槛上,火光映红面颊,映出岁月修改过的轮廓……妮可妮可,蒙奇奇一样的妮可,你的娃娃脸呢?你的眼角怎么也有皱纹了?
妮可也醉了,她说:哥,我不哭。
我说:乖,不许哭啊。
她抬起一张湿漉漉的脸,闭着眼睛问我:哥,我们什么时候回拉萨?
除夕夜里的丽江,烟花开满了天空,我轻轻地抱了她一下,拍拍她的背。
妮可,你看,好漂亮的烟花。
妮可,我曾悄悄回过一次拉萨。
2010年30岁生日当天,一睁开眼,就往死里想念。一刻也不能等了,一刻也不容迟缓,脸都没洗,我冲去机场,辗转三个城市飞抵拉萨贡嘎机场。
再度站在藏医院路口的时候,我哽咽难言,越往里走,大昭寺的法轮金顶就看得越真切。那一刻,我是个近乡情怯的孩子,匍匐在滚烫滚烫的广场上,一个长头磕完,委屈得涕泪横流。端着枪的武警过来撵我,他说:走喽走喽,不要在这里躺。
我打车来到仙足岛,客栈林立,没有一个招牌是我熟悉的。我翻手机,挨个打电话。空号、空号、忙音……很难受,自17岁浪荡江湖起,十几年来第一次尝到了举目无亲的感觉。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再也回不去了。
两年后,我随缘皈依三宝,做了临济宗在家弟子。大和尚开示我缘起论时,告诉我万法皆空唯因果不空。他说,执念放下一点儿,智慧就升起一点儿。
可是师父,我执念重,如缕如麻无尽绵延。时至今日,我依旧执着于和拉漂兄弟们共度的那些时光。他们是我的家人,我的族人,我弥足珍贵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