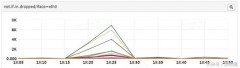一九九五年对于日本是极为糟糕的年份。一月十七日发生7.2级神户大地震(日本称“阪神大震灾”),三十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最后超过六千四百人,《每日新闻》形容说“状况简直同刚刚战败时无异”。此后不到两个月又发生沙林毒气事件。三月二十日清晨,十名奥姆真理教信徒两人一组分成五路,其中五名钻进三条线路的地铁车厢,在上班高峰时间段用打磨锋利的伞杆尖端捅破装有液状沙林毒气的塑料袋。毒气在密封的车厢和停车时的月台上弥漫开来,受害者超过五千人(官方正式公布为三千八百人),其中死亡十二人,更多的人苦于后遗症,有的终身致残。地震摧毁了日本抗震施工技术的神话,“沙林”终结了日本社会治安的神话,乃日本战后最惨重的天灾人祸。村上春树在《地下》题为“没有标记的噩梦”的后记中就此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九九五年一月和三月发生的阪神大震灾与地铁沙林事件,是日本战后划时代的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两大悲剧,是即使说‘日本人的意识状态因此而前后截然不同’也不为过的重大事件。有可能作为一对灾难(catastrophe)、作为在讲述我们的精神史方面无可忽视的大型里程碑存续下去。”
--村上春树《地下》前言
在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时间发生二十周年后,今天与大家分享村上春树与日本心理学者、学者、前文化厅长官河合隼雄的一篇关于人之“恶”的对谈。
与“恶”共生
--村上春树对谈河合隼雄
摘自|《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
- 声明:如需转载先请私信联系 -
此次对话于平成十年八月十日于京都举行
村上:
想写《地下》的时候,也是因为社会的目光压倒性集中在作为沙林事件施害者方面的奥姆真理教,我则很想以贴近地面的眼睛将遭遇不幸方面的普通人形象浮雕出来,而不是仅仅说“有这样一些可怜的受害者”。
而在一度整理完以书的形式出版之后,又强烈觉得仅那样怕是不够的。在将那一视点在自己身上牢牢设定的基础上,这回觉得恐怕有必要将目光转向奥姆真理教方面。心想若不那样,真正的全景图就难以呈现出来。
河合:
那是理所当然的吧。
村上:
这样,我首先采访了几个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和原来的信徒。但作为一个小说家,坦率地说,可以说我为奥姆方面的人共同拥有的问题意识那样的东西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因为同听受害人讲述时相比,那部分的表现方式毕竟是明确的。但是,关于如何将他们讲述的那种问题意识付诸程序的方法,则没有怎么吸引我。相反,就《地下》中列举的受害者方面来说,较之问题意识的提出方式,我感兴趣的则相反是问题本身的程序化方式。我觉得,尽管两者带有许多同质问题,却又带着异质意识生存于世,这点让我刻骨铭心。
河合:
你写到,奥姆人做的事和小说家做的事有相似部分,同时又有不同部分。我觉得这个极有意思……
(但与此同时,和他们促膝交谈起来,我不能不深深感到小说家写小说这一行为同他们希求宗教那一行为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共通点这一事实。其中有极其相似的东西。这点毋庸置疑。话虽这么说,却又不能下定义说二者的行为完全同根。这是因为,在存在相似性的同时又存在某种决定性的不同点。和他们交谈时最能激起我个人兴趣而又让我觉得坐立不安的也是这点。(据《文艺春秋》九八年四月号,《后地下“序”》)

村上春树著《地下》
村上:
这点我的感觉非常强烈。我对准意识的焦点,下到自己这一存在最底层那样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写小说也罢,追求宗教也罢,相互重合部分是很大的。在那样的语境中,我觉得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正确理解他们讲述的宗教观。但不同的地方在于,在那样的作业中,自己能在何种程度上主动负起最终责任。说清楚些,我们是自己单独以作品这一形式接受它,也不得不接受它。他们则归根结底委托给教主和教义。简单说来,那里就是决定性差异。
交谈当中,一谈到宗教,他们的话语就没有延展性。所以么,我就一直就这个思考: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呢?最后这样想道:我们是本能地把世界这个东西的结构作为Chinese Box(套匣)来把握的。匣子里有匣子,那个匣子里还有匣子……就是这样的东西。我们现在所把握的世界之外或者之内,大概还有另一个匣子——想必我们是潜在性这样理解的吧?这样的理解赋予我们的世界以阴影和深度。以音乐来说,就是给予泛音那样的东西。但是,奥姆那些人尽管口头上说希求“另一个世界”,然而对他们来说,实际世界的构成方式则莫名其妙地是单一而平板的。有的地方延展性已经终止,有的地方只能以一个匣子看世界。
河合;
有那样的感觉,一点儿不错。
村上:
例如上祐这个人。此人利用非常巧妙的修辞高谈阔论,但他所谈论的是仅仅在一个有限的匣子里才通用的话语和道理,再往前根本没有展开,所以理所当然无法抵达人心。然而单纯、坚固、自成一体。个中奥妙恐怕他也十分清楚,从而巧妙地反为己用。对方没有办法说服他。即便知道他说的没有深度甚至荒诞,也无法有效反驳。大家因此心焦意躁。可是问奥姆的人,都说没有比上祐脑袋更好使的人了,无条件地尊敬他。向他们说明上祐言论哪里不正常是非常艰难的。因为那必须证明那只匣子的局限性。
河合:
是的,那是非常艰难的。不过回想起来,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大家就满不在乎地杀人来着——战争。而且有人胡乱杀人并因此获得勋章。只要是进到匣子里干的,那也全部作为正确行为通行无阻。
而且,如您说的,全都一起忽一下子进到匣子里干的,进到“好孩子”那个匣子里。那的确是万分危险的事,但只要心里明白,就无疑是好家伙。那类人应该具有某种——怎么说好呢——正直啦诚实等品性的。若不然,是不至于进入奥姆那样的地方的。
村上:
的确,一般社会中,以“善的动机”进入公司的人基本没有。
河合:
是以无动机进入的,统统(笑)。
村上:
不过就奥姆来说,进入那里当时分明是有“善的动机”的。善的目的也有。
河合:
况且是情愿抛弃现世利益进入的。
村上:
这个嘛,我隐约心想,抛弃一切想必是相当畅快的吧?
河合:
那个因人而异。哪怕再想抛弃也抛弃不了的人也是有的。也有人做出抛弃的样子却悄悄放在旁边。我这样子的恐怕就难免(笑)。
村上:
不过交谈起来,都好像轻易出家的。说着说着,就突然说出“所以出家了”那样的话来。“且慢,所谓出家不是家人也好、工作也好、财产也好,要统统抛弃的吗?那不会是很不得了的事?”——我这么反问,但感觉上,对于多数人好像并不像从清水寺舞台上飞身跳下似的(清水寺建于悬崖峭壁之上,据说不时有人从其“舞台”跳下自杀。)。
河合:
细想之下,带着东西去那个世界的人是根本没有的。不是什么都要抛弃的嘛,所以出家和赴死是同一回事,好比去那个世界。所以说轻松也可以说是轻松,可以说是一身轻松。话虽这么说,毕竟我们都是活在这个世上的,在抛弃东西的同时必须承受活在这个世上的苦难——二者密不可分。若不然,人大约是信赖不得的,我确实这么认为。因为纠葛那东西没有了,对吧?
村上:
不过让他们说来,那种物欲性质的东西让人的烦恼膨胀开来,对人造成消耗。所以必须抛弃烦恼来纯化自己。
河合:
啊,所以嘛,有烦恼而不消耗是不成其为宗教的。一旦抛弃烦恼,人就成佛了。
村上:
抛弃烦恼并不是修行。
河合:
嗯。那已经是佛,不是人的修炼。但我们不是神也不是佛,即使以为烦恼没有了也还是有的……亲鸾就是那样的吧?以为没有了却还是有,自始至终。因为搞得彻底,所以亲鸾才到了那个地步。一开始就那个样子是无从谈起的,我想。
所以,这里冒出的(奥姆那些)人,拥抱烦恼的力气是不够多的,遗憾。换个角度打上光照,可以说比我们凡人纯粹啦、善于思考啦什么的。可以说是可以说,但那到底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些人统统去了天国倒还好,而只要作为人活在这个世上,我认为恐怕就几乎没有可能从烦恼中解脱出来。
村上:
不过,其中显然有“此人在人世间大概很难顺利过下去”那样的人。同一般社会价值观原本就格格不入。至于占人口的百分之几自是不晓得,但在社会体制中过不下去——好也罢坏也罢——这类人的确是存在的。我倒是觉得,是不是应该有接受这类人的托盘那样的东西……
河合:
在您说的事情之中,这是我最赞成的。就是说,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那类人所在的位置。问题是人们都想错了,以为排除掉这类人,社会就能变得健全。这是大错特错的。那样的场所如今的社会实在太少了。
村上:
退出奥姆的人也异口同声地说一点儿也不为加入奥姆一事本身感到后悔。
河合:
自己与犯罪有关另当别论,但这些(接受采访的)人并不知情。这样,我想有人不后悔甚至打算继续下去是理所当然的。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如果叫这些人洗手,可洗手后做什么呢?没有替代的嘛!
这同吸信纳水(信纳水:即香蕉水,高浓度吸入有麻醉作用。)的孩子是同一回事。谁都可以对吸信纳水的孩子说:“那东西不好,别玩了!”吸那东西不好这点,吸的本人也心知肚明。问题是,只要我们不提供不吸信纳水后可以让他生活下去的世界,他就绝对戒不了。正因为那个世界对于他是有意义的,他才欲罢不能。所以,说实话,退出奥姆的人也可怜得不得了。
村上:
是够可怜的。
河合:
所以么,采访当中有人说进入奥姆后稍微做了做,身体就忽一下子变好的吧?那个我很能理解。我们这里也有那些人来访。见面交谈时我这么想来着:这种人如进了奥姆那样的地方,很可能一切不翼而飞。依你特有的说法,就是一下子进入一个匣子里。所以,一旦进入,就全都好了。
村上:
这我明白。
河合:
可是一旦进去,这回怎么对待匣子就成了严重问题。所以我们才要在不把人关进那样的匣子的情况下把他治好。而那样一来,就要花很长时间。不过我最近想来着:花很长时间大约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有一点我要说清楚:“如果想快些治好,那么请到别处去。来我这里是快不了的。”对方吃了一惊,“哦?”我说不知道自己对治疗是否热心。自己不是不热心治疗,而是你对求生不热心,所以要花很长时间。如果无论如何都想尽快治好,这种地方另外也是有的。
认为花时间受不了的人,就让我把他转去那边,不过那样的人是看得出来的。也有人表示治不好也没关系。还有更极端的人,说自己不是为了治好而来这里的。厉害!
不过也有人说:“听说来先生这里也根本治不好,去别处会马上治好的。”我说:“是吗,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别去,但如果无论如何都想去,那么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于是他就去了,一下子好了。好了是好,但后来糟了,结果焦头烂额地回来了。毕竟有过一次体验了,于是说还是慢慢来吧,我就重头治起。
村上:
所谓“进入匣子”,在宗教那里,就是“绝对皈依”吧?
河合:
是的,绝对皈依。这个说舒心也舒心。看见这些人,就会对世界怀有疑问,觉得“这好像有些怪”,全都。而“有些怪”这个疑问,一旦进入匣子,就全部被解释得十分通透:“这是karma(业障)”。
村上:
解释通透这点,对个人是很重要的。
河合:
不错。不过么,全都解释通透的逻辑,那东西是绝对不成立的。让我们说来就是这样。可是,普通人喜欢解释通透的东西。
村上:
是啊,大家都在寻求那样的东西。这不限于宗教,一般媒体也是那样。
此外我还想到一点,那就是,麻原彰晃这个人是怀有极其自我矛盾那样的东西的。缺点多多,在某种意义一塌糊涂。但我觉得在结果上恐怕幸好这样。假如他干干净净一表人才,说话滔滔不绝,那么说不定大家不会那么追随,我感觉。
河合:
虽然能够解释得十分通透、似乎无所不知,但教祖某个地方没有费解性是不行的。那方面他大概有天生的东西。不过么,他是明白的。处于那样的立场,那么看来看去,判断力却是非常精确的。当然也犯错误,但凭直觉恍然大悟那样的地方我想也是相当不少的。所以大家才被他一下子击中。就连我们这样的,只瞧一眼就当即了如指掌的场合也是常有的,不是开玩笑。
村上:
那种类似魔性直觉力的东西希特勒也是有的。他能把军事专家也看不清的事情接连看得一清二楚,在战争中取得摧枯拉朽般的胜利……
河合:
正是。但最后撑不住了。体育选手也一样。胜、胜、每战必胜。那种时候他总说“没有败的感觉”。即使在绝对无法反败为胜的情况下,而只要认为“我反正要胜”,心里也镇定自若,实际上也如愿以偿。但是,如果一旦觉得撑不住了,这回就怎么也爬不上岸来。不过在某个时期,人是会那么精确、精确、一直精确到底的。在我们的职业中,最危险的就是那个。
村上:
您是就作为医疗者的阅历而说的吗?由于见了谁就一眼看穿?
河合:
不错。或者莫如说,自以为一眼看穿。而有趣的是,有时居然百发百中——是这样的吧?正是这样!可是就这么干下去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迟早会说歪打偏,毕竟是人嘛。另外——倒不是说麻原彰晃——也会心想自己总得想法露一手。那一来就完蛋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好像一直修行过来的,修行得渐渐莫名其妙,真的。人“精确”那一时期固然有,但为此沾沾自喜的人统统完蛋了。

村上春树著《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
村上:
回到刚才谈的无法很好适应社会(现世)之人的话题上来——有效接受那些人的托盘那样的东西能制作出来吗?
河合:
人这东西,不妨说,制作的是某种程度上满足烦恼并尽可能使之长效化的世界,尤其到了现代,效果变得相当直接而又快速。变得直接而又快速,即意味与之不适应的人增多了,无论如何。就是这样的体制被制作出来。这样,对于“不适应”的人我们该如何考虑呢?
对此,一个能有影响的,就是艺术啦文学啦等一类东西,虽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有人这个也是不会的。那么那些人怎么办?这是很难的事。不过,这么考虑下去,如果有生活保障什么的,觉得给那些人发放补助金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给补助金,请开心地活下去吧!”
村上:
是的是的(笑)。
河合:
可以做着有趣的事蛮不错地活下去。那些人我也见来着,到底是有人拥有自己完整的世界的。
村上:
就是说,官方如何虽然不清楚,但社会本身恐怕还是准备这种托盘为好,是吧?
河合:
我是这么想的。为那种莫名其妙的人提供生活保障,简直岂有此理!要是有往那种地方花的钱,还不如用在日本经济上。或者,那样的人任凭他掉下去好了——有人这么说。但不要那样,这是要由社会好好对付,给那些人发放钱款。我想我们应该是有那样的义务的。
村上: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除却引起地铁沙林事件等社会犯罪事件这一性质不论,奥姆真理教大概就成了那些人不错的托盘。实际上现在的奥姆真理教也表示作为纯粹宗教团体开展活动。情况会怎么样呢?作为道理固然明白,但我觉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河合:
所以说那本身是个不错的容器。但还是不可能永远作为不错的容器存在。如果成为那般纯粹的、以极端形式出现的团体,那么肯定发生问题。那般纯粹的东西紧紧集中在内侧,外侧如果没有杀也不足惜那样十恶不赦的家伙,就没办法维持平衡。那样一来,如果不打到外面,里面就有可能发生非同小可的骚乱,组织因此从内侧崩溃。
村上:
言之有理。和纳粹不能不挑起战争是同一原理。越膨胀,里面类似集约点的地方压力越大,而若不向外喷发,其本身就会爆掉。
河合:
是那样的。无论如何都要攻击外面。麻原不是一直在说“我们受到攻击”的吗?因为他不经常将恶置于外侧就维持不下去。
村上:
美国啦共济会啦的阴谋说,也是因为这个。
河合:
所以么,真正的组织那东西,在自己身上没有恶是不行的,在组织内部。这点家庭也不例外。即使家里面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恶。否则,势必为组织安稳而在外部制造恶。希特勒干的恰恰就是这个。
村上:
是啊。
河合:
所以完蛋了。奥姆也一样,以现在这个形式是长远不了的,我想。
村上:
那就是您说的“危险性”吧?
河合:
是那么回事。
村上:
不过问起信徒来,仍然有人说不相信地铁沙林真是奥姆干的,“或许干了,但很难相信。”
河合:
我想是真不相信。都认为自己是纯粹的,不可能干那种坏事。问题是,什么坏事也不至于干的人满满汇聚一堂,势必干天大的坏事,非干不可。不那样,组织就维持不了。
村上:
那是一个圆球形集合体,虽然外侧是软的,但热量——刚才也说了——都集中在中心点。而外侧对此浑然不觉。几乎所有的信徒都说:“我们过的是连一只蟑螂都不杀害的生活,怎么可能杀人?”
河合:
那就是卓别林的《杀人狂时代》。那个见人就杀的家伙,看见毛毛虫却赶忙捡起来拿到花丛那里——虫子一条不杀,只杀人。人这东西到底是无可救药的生物啊!所以需要一种自觉:以自己的责任在多大程度上放纵自己的恶。
村上:
可是,西藏密教也是和奥姆一样修行的。出家做密教修行。到底哪里不同呢?
河合:
我对西藏佛教不太熟悉。不过我想,那种类似恶的问题肯定是巧妙地纳入其中的。把那个翻译拿进来,估计是要弄得十分简单易懂的吧?这地方是再难不过的。多大程度上放纵恶,行使恶,这是书中最不容易写的事。
村上:
只能在现场部分从体验上传达。但若解析,就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加以整合。
河合:
人用脑袋想东西,如果整合性写出好事来,恶就进不去了。就这点来说,一开始就有“原罪”这东西的确想的非同一般,西方人明确表明“都有原罪”。
村上:
就是说我们原本就是从恶里面出来的。
河合:
正是正是。所以事情就成了这个样子:“哪怕再拼命努力,以人的力量也是奈何不得的。”结果,基督被绑在了十字架上——就这样打发了。在这点上,那到底是了不起的宗教。
村上:
那和karma(业障)不大相同。karma(业障)那东西总是可以打发的。在这点上,原罪是完全无可奈何的。
河合:
无可奈何。西方人为此苦不堪言,结果又杀人去了。所以,可以说无论如何都很难的。不过么,往下人也聪明些了,无论什么样的组织还是家庭,最好认真考虑一下该拥有怎样程度的恶。就是说,怎样表达它、容许它。
村上:
奥姆真理教一系列事件也好,或者神户A少年事件也好,我都不能不从社会对其表现出的某种愤怒中感觉出异常的东西。所以我想,人是经常在自己这个体制中带着恶那样的东西生存的。
河合:
正是那样。
村上:
要是有人碰巧“啪”一下打开恶的盖子,就不能不像看对照镜一样注视自己身上的恶。正因如此,我觉得世人才表现得那么气急败坏。所以,例如把A少年相片在杂志上刊出——为刊出还是不刊出相互争吵,破口大骂。若让我说,那不是本质性问题。我想应该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认真讨论。然而问题气势汹汹去了那边,成了情绪性愤怒的喷发。或者要把奥姆罪犯的父母装进麻袋打死。我感到那岂不和复仇情绪差不多少了?反正就是要惩罚,或者说。
河合:
大家都顶顶喜欢惩罚对自己没有实际危害的某个人,因为如果作为自己的事看就不得了。“那种坏家伙的相片刊出干什么!”这么一说,大家都心安理得了。
村上:
去年见先生时谈起恶,使得我思考了很多。我有个印象,就是恶这东西恐怕是作为人这一体制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而存在的。那既不是独立的东西,又不是可以交换或单独销毁的东西。或者莫如说,我甚至觉得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恶又可能是善的东西。就是说,从这边投光,其影子成了恶,从那边投光,其影子又成了善。这样,很多事情就能得到解释了。
但也的确有仅仅这样解释不了的东西。例如无论见了麻原彰晃还是见了A少年,说纯粹恶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觉得像恶性肿瘤那样的东西忽一下子集结起来鼓涌而出的场合也是有的。想必那种东西就在体内,从而引起不妨说是“恶的照射”那样的东西。这种印象很强烈。倒是说不太好……
河合:
我想那恐怕还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让我们别看、别看、别看那种东西,别看过头了造成的。这样一来,凝聚变硬的东西无论如何都要喷涌出来。
比如说,A少年事件发生时,以小孩子藏着躲着干坏事可不得了为理由,把那一带的树木一砍而光。我听了气得不行。事情整个弄反了嘛!孩子们是在大人看不见的地方以孩子的方式干着坏事成长的。无时无刻总是被大人看着才发生那种事的嘛!可把我气坏了。我喜欢树,光砍树都够让我气恼的(笑)。
都太没见识了,以为看得紧紧的就能培养出好孩子,大错特错!自己总在别人监视下是多么难受,这点想一想就不难明白的……
村上:
关于这个,有人实话实说,不说的人也有。但听加入奥姆的人讲述过程中,得知成长的家庭环境有问题的人到底是有不少的。来自父母的正常关爱在儿时人格形成期间说乱套也好说不足也好,总之那类情况很多,我觉得。
河合:
这地方非常难。不过若泛泛而论,的确可以那样说。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人是要用脑袋思考的吧,而这么一下子进到小匣子里一个劲思考的时候,切断思考流程的毕竟是人际关系,毕竟是父亲或母亲,是感情。如果那个动起来,就无论如何也不会进到那样的小匣子里。好像有点儿奇怪啊——这样的心情就会发挥作用。
村上:
就是说平衡感开始启动。
河合:
是的。平衡感。那种巧妙运作装置(如果接受不到父母的关爱)就很难发育。
所以么,和这些人说的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年轻人多多少少都那么思考。为什么活着啦、做这种事也解决不了什么啦等等,这个那个认真思来想去。但那里有刚才说的那种自然情感的流动,有整体平衡感的启动,在那一过程中形成自己。可是,进入奥姆的人由于那个地方断裂了,就一下子直接去了那边。说可怜也的确够可怜的。
村上:
我听了奥姆的音乐,强烈感觉出了那点。听也根本听不出好在哪里。真正好的音乐是有种种阴翳的,是吧?悲伤啦欣喜啦等阴翳什么的。然而奥姆的音乐中完全感觉不到,只好像在小匣子里叫个不停。单调,没有纵深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是mesmerising(催眠的)也好像未尝不可。而奥姆那里的人却以为是好音乐,所以也才让我听。我认为音乐是和人的心理最为密切相关的东西,因此觉得那东西有让人害怕的地方。
于是,我就“身体性”问了对方。例如做瑜伽会产生某种醒悟吧,但那归根结底是物理性(physical)的东西。但在整个“新纪元运动”尤其奥姆真理教那里,物理性和形而上学性(metaphysical)不由分说地结合在了一起。
河合:
正是那样。现代人无论如何都要从身体性中脱落下来,以致无论如何都变得头大体小。所以,这些人认为必须恢复身体性而做瑜伽什么的。而且这些人有倏然贯通之感。那种开悟意识同一般日常意识之间没有联系,利利索索两相断裂。或者说唯其因为没有日常性障碍(barrier),这些人才格外容易开悟。而当那种开悟同日常生活中隔绝感那样的东西合在一起的时候,事情就不得了。我们这样的人就算暝想也根本开悟不了的(笑)。
村上:
我也同样。
河合:
想必。冥想当中,总想什么时候结束啦想吃好吃的什么的(笑)。就是说,到了更普通的人那里,满脑袋都赚钱啦税款啦,宗教什么的根本无从谈起,那方面强大得多。这样,生活势必同“灵性”毫无关系。即使没严重到那个地步,我们稍微搞一会儿冥想也因为有烦恼而很难出效果的。可是,“有烦恼而仍然争取”那东西具有很大意义。不料,这些(去了奥姆的)人的烦恼世界却又过于弱了。
村上:
所以能马上开悟,开悟得太快了。
河合:
有趣的是,过快开悟的人,其开悟往往很难对别人有用。相比之下,“怎么还不开悟呢?为什么只自己还不开悟呢?”——这么千辛万苦慢慢在烦恼当中开悟的人更对他人有所启发。拥有相当严重的烦恼世界仍然争取开悟,这才有意义。
村上:
我也是。我在做体育运动的时候,有某种类似开悟的感觉。但并没有从中发现精神意味,无非心想那种情况也是有的吧。说是说不好,估计是在同周围的关联中把握的。可是,这些人做瑜伽时一旦有了某种开悟感,就一口气去了那边,而且放弃了同周围世界的关联。这方面不单单奥姆,也是整个“新纪元运动”同样存在的危险性,我想。
不过,即使没有奥姆,迟早也必有其他类似偏执性宗教团体(cult)出现。我是这么认为的。
河合:
非出现不可,毕竟有多少具有那种才能的人。把那个巧妙地表现出来,必定有同样的东西出现。
村上:
那一来,再次发生同样事件的可能性就很大。
河合:
我想可能性绝对很大。所以,“只要不造成实际危害,出现也是奈何不得的”——这么认为是解决不了什么的。只是,实际危害这东西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即使奥姆,最初出现的时候我也认为很有正面意义,以致当时评价奥姆真理教的人左右为难。
最初规模小的时候,一般都有相应好的东西。但组织变大之后,就无论如何都变得复杂起来。刚才也说了,越大整体压力越高。
村上:
不过,那里越有“善的东西”,凝聚力那个东西就越能发挥作用,球也就必然越变越大。
河合:
这是最难的地方。我想麻原起始阶段也是相当纯粹的,而且具有相当强烈的感召力。可是,刚才也说了,一旦站在某个组织的顶点,堕落立马开始。这是极可怕的事。站在顶点,总有众人期待的吧,不能不照着做,不能不妥协。而心里又完全清楚迟早必然败露,于是借助科学的力量蒙混过关。这样一来,就已经是犯罪性质的了。
村上:
如果真正是宗教天才,就能忍耐?
河合:
天才一开始就不会做这种傻事。例如亲鸾说“不收弟子”。尽管说了,但后来还是形成了那么厉害的宗教集团。因此我想,从此往后,宗教性的追求恐怕只能以个人为单位进行。
村上:
我好像和您看法不同,个人有那么强大精神的人,在很多情况下恐怕不至于去搞什么宗教的吧?世间追求宗教的大多数人,想必是个人能力有限的人。
河合:
不构筑坚实的组织就可以了,例如没有规则的散松组织之类。想集中就来,完了就散,类似这样的东西。每次都临时聚会。
村上:
我怎么也乐观不起来。看奥姆的组织也看出来了,那里必有专家出身的领导者(technocrat)那样的人。世人都有疑问:“那样的精英为什么会参加奥姆呢?”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由于种种样样的原由而成了微型虚拟世界——而不是广阔的现实世界——的精英分子。想必害怕踏上广阔世界。哪怕地方再小,那类人也一定要去的。
河合:
即使为了不再让那样的人出现,往后也必须使每一个人变得坚强起来。必须为此好好进行教育。现在的教育根本不行。教育必须考虑如何使每一个人坚强起来。不过么,不去学校的孩子有十万之多,这到底进步不小。文部省之所以容许,说明文部省也有相当大的变化。
村上:
那是好事啊!我也讨厌学校的。不过么,前些日子有人在哪里搞调查,我也看了。上面说让日本人选择自己喜欢的词,结果“自由”排在第四或第五位。我么,不管怎么说都要把“自由”放在第一位,可日本人最喜欢“忍耐”和“努力”。
河合:
哈哈哈,那怕是的。日本到底是“忍”为第一。我总是忍从,是平成(平成:平成年间。)的忍者(笑)。
村上:
不过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时不时怀有疑问的:日本人果真在追求自由不成?尤其采访奥姆里的人的时候,我切实感觉到了这点。
河合:
啊,日本人大概很难理解“自由”这个东西的吧。“随意”倒好像都喜欢,可“自由”都觉得可怕。
村上:
所以我有个印象:即使对奥姆那些人说“飞出去一个人自由干吧”,差不多所有的人恐怕都是受不了的。大家或多或少都处“待命”状态,等待哪里下达命令。对他们来说,没有命令不是“自由状态”,而只能是“暂定状态”。
河合:
正因为这才更没有激情,是“逃离自由”。所以,要从小教育自由是多么美好又多么可怕的事情,这是教育的根本。我是真希望这么做,却怎么也做不到。但要是会做的话,是做得到的。我喜欢那样的老师,和那样的老师搞过对谈。会当老师的老师是让孩子自由的,让孩子做。那样,孩子就会做得相当不错。怪事也会做一点点的,让他做就是了。
现在是一个劲儿往里塞知识的吧?以致人生智慧部分的学习难免稀里糊涂。日本人尤其严重,从上小学就开始“用功”。用功这东西是同人生毫无关系的东西。最近同唐纳德·金(唐纳德·金(Donald keene):美国学者,日本文学研究专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有《日本文学史》、《百代之过客》等。)交谈来着,他年轻时为了拿奖学金而在数学方面拼命用功。数学是最能出分数的,最适合拿奖学金。至于用功到什么程度自是不清楚,只听他说“那么用功学的数学对我的人生毫无用处(笑)”。那怕是的啊,我说。
村上:
我要求自己尽量找时间去法庭旁听。但我看见那些成为罪犯的人时,他们犯的罪固然是罪,可我还是不能不感到可怜。虽说是自己选择的道路,但毕竟精神上多多少少受到了控制。所以,关于法律上的量刑问题另当别论,而作为人的责任能够追究到何种地步,我很难决定。见了那么多的受害者人士,对那种犯罪我自然感到怒不可遏。尽管这样,可怜感也还是顽强留了下来。
河合:
关于日本许多BC级战犯也同样可以这么说。
村上:
说到底,可能归结为体制问题。不过,狭义而集约式下达命令并让人执行的体制这个东西,大也好小也好都是自然形成的。这对我是极其可怕的。为什么,那样的技术秘诀(know-how)会忽一下子出现在那里并且在较短期间无可抗阻地变得坚不可摧呢?这是个谜。只能认为有嗜好那种东西的力量自然而然或自缚式地发挥作用所致。确实和战犯问题相似。无论怎么审判都必有问题遗留下来。
(完)
村上春树 Haruki Murakami | ||||
| 日本小说家。以《且听风吟》获日本群像新人奖。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畅销超过一千万册。写作风格受欧美作家影响,被誉为日本80年代的文学旗手。 | |||
新书推介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村上春树作品系列) | ||||
| 译者 林少华 竺家荣 陆求实 岳远坤 姜建强 毛丹青 ISBN 978-7-5327-6877-6 定价 35元 出版时间 2015年3月底 | |||
村上春树最新短篇小说集 一张最妙的“概念专辑” 返回原点,再出发! 对于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来说, 世界是广阔而痛切的混合, 一如月亮的背面。 | ||||
上海译文
文学|社科|学术
名家|名作|名译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或搜索ID“stphbooks”添加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