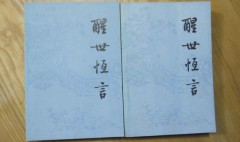2021年有不少社会学方面的通俗读物译介出版,比如田中正人等著的《惊呆了!原来这就是社会学》、堀内进之介等著的《这就是社会学》,再比如将社会学常识融入故事形式的安格斯·班克罗夫特等著的《米拉的猜想》。如果说这些书能起到普及社会学基本人物、概念的作用,那么恐怕它们的作用也仅止于此了。严苛一点讲,这些书终究是可有可无的,是可替代的,它们并不包含社会学的洞见。
赵鼎新的小书《什么是社会学》,只有一百多页,可它却完全不是一本通俗读物。它没有像社会学导论著作通常会做的那样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讲起,因为作者无意于向读者普及百科全书词条里会出现的那类社会学知识。《什么是社会学》是一本充满个性、具有学术原创性、读起来令人感觉痛快淋漓的书。尽管它预设的读者对象也是对社会学工作所知有限的初学者,但作者显然表现出对读者思考能力的充分信任,他从他心目中最紧要的学科精髓讲起,从今天仍论争不断的学术分歧讲起,从自己从事社会学最有心得的地方讲起。如果把“入门书”看成是对新兵进行训练,那么这位教官显然不是在军营的空地上让新兵们立正、稍息、操练队列,而是直接把新兵带进实战,在枪炮隆隆声中向他们讲解什么是真正的打仗。
赵鼎新在书中首先指出,人在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所采用的最基本的叙事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事件/时间序列叙事,历史学以其为基础,另一种是结构/机制叙事,在赵鼎新看来,社会学就是一门以结构/机制叙事为基础的学问。对宏观的结构与相对微观的机制二者,赵鼎新又更强调机制,他给机制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机制,是一组在控制条件下可被观察到的,同样也能通过推理获得的,因此是可以被解释的、因果链最短并且关系确定的结构性因果关系。该书仅有三章,第一章题为“结构与机制”,第二章叫“机制解释的问题”,第三章叫“机制解释弱点的弥补”。不难看出,赵鼎新此书是围绕“机制”展开的,而三章的设置则不无“正反合”的味道,既强调机制解释的重要性,也不讳言其不足。针对社会学者的任务,赵鼎新则提出:“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来说,他所提出的问题不应该是微观层次的因素对宏观的社会现象是否有作用,而是这个作用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到底有多大。”
作者对机制做了分门别类的分析,精彩之处甚多,在这里,姑且只以关于“正反馈机制与负反馈机制”的分析为例,因为这个命题既宏大,又有紧迫性,对社会学不甚感兴趣的读者也很可能会从中得到启发。赵鼎新指出:“主宰生物世界运行的主要是让生命系统趋于稳定的负反馈机制,但是由于人有通过策略取胜和论证自我行为正确性的能力,主导社会发展的就成了正反馈机制。”众所周知,正反馈是不稳定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人类的社会发展是不稳定的。赵鼎新强调,在历史上,一批具有特别强烈的权力和成功欲望的人士的追求成了社会变迁的最大原动力,这会加剧正反馈的不稳定。赵鼎新以不无鄙夷的态度写道:“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对人类社会的正反馈特性缺乏清晰认识,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因此会显得天真和简单。”赵鼎新认为,我们应建立起如下观点(经我提炼):一,文化的延续必须有各种制度维系,文化不具有超越制度的稳定性;二,人类社会完全不具有自稳定性,只要人类存在,历史就不会终结;三,非企及后果(通俗地说,就是背离初衷、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轴。赵鼎新最后以格言式的精炼和悖论意味总结道:“生物是没有智力的,但是生物系统却都是有智力的;人是有智力的,但是人类社会却是没有智力的。”
在分析机制解释的弱点的第二章,赵鼎新其实主要表达了三种“鄙视”:一是对社会学中“一批问题意识发散,不讲机制,没有因果,不懂行动者的权力和约束,只有个性化叙事的文章和书籍”的鄙视;二是对一些“以提新概念为己任”的人类学、文化史和质性社会学学者的鄙视;三是对部分社会学经典的鄙视,他说:“许多名著在经验上甚至逻辑上都漏洞百出,它们的价值主要在于启发……支撑这些名著形成的最关键因素其实也不是社会科学方法,而是作者的品味。”
如何弥补机制解释的弱点?从主观上来说,也许就是要求社会学家们保持对自己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审慎态度。赵鼎新不无感慨地写道:“我接触过大量的优秀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有着某种紧张和不自信,因此反思力也就比较强。如果有人以为自己在年轻时就认准了真理,并且认为自己所看到的、理解的和讲出来的故事都是对的,那么这个人就无药可救了。反思能力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太重要了。”
然而,有点矛盾意味的是,赵鼎新在陈述他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时,不时流露出一种他“所看到的、理解的和讲出来的故事都是对的”的意态。当然,我们对他的社会学见识是非常佩服的,坦白讲,我们也并无能力在专业上对其论述进行指摘,但或许“某种紧张和不自信”对作者并不是无益的。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二版序言中曾说,人类总以为自己有控制社会领域的无限权力,可“无数的经验在告诉他们,得意洋洋地幻想的这种无限权力,一直是他们变弱的原因,而只有在他们承认物具有其固有的本性并虚心地探求物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对物的支配才真正开始。”或许,每一位社会学者也都应该首先承认社会学具有其固有的本性并虚心地探求它究竟是什么罢。 (乔纳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