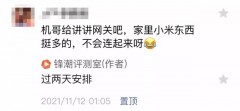伍里川
杭州“天才翻译家”金晓宇和父亲金性勇的故事,最让我心有戚戚的是,金晓宇的母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症,她去世的消息,金性勇最初是瞒着金晓宇的。
金晓宇能走上译书之路,离不开母亲的帮助。对患躁郁症的儿子忧心忡忡的母亲,突然忘却身边亲人,成了被儿子照料三年的人,这个人生转折,未免太令人唏嘘。
阿尔茨海默症,一个听上去挺普通的词,却残忍到让人无处话凄凉。
四年前,父母所住老人房的围墙和礼堂被轰然拆毁的那天,母亲告诉我,“小晟妈老年痴呆了。”
我大惊,“怎么了?”
“谁都不认识了,突然的。她就比我大两三岁。”
“上个月见到她不是还好好的吗?不是还好好地打招呼吗?”小晟妈每次在老人房的大门前看见我的车开进来,就会笑盈盈地问我:“又来看你妈吧?”脸上是欣慰的表情。
我的心头掠过阵阵伤感。我一边开着车小心避让着挖掘车的巨长铁胳膊,一边不停地追问母亲。母亲能解释的就一句:“哪个晓得呢,哪个晓得呢。”
我们的村子拆迁之后,很多村里的老人搬进了村前临时盖的老人房,继而又从老人房搬进拆迁安置楼,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母亲这一拨人,多已年过七旬。劳苦了一辈子,在刚刚住上新楼房后,小晟妈却出了这事。阿尔茨海默症,在本地都被喊为“老年痴呆”——这是一个没有贬义也没有褒义的称呼。
打年轻时候起,我妈和小晟妈就玩得最好。半辈子下来,算是村里的闺蜜。我当兵探亲回来,如果找不到母亲,就会上小晟家寻找。小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一起在村河的岛上放过牛,一起在田野里追逐过水鸟。
小晟妈是一个脾气很好爱笑的妇人。夏天,我每次去找小晟的时候,她总会笑呵呵地递给我一只红瓤的菜瓜。我们家的菜瓜,青涩时就被啃光了。我们两家的自留地挨着,所以那个时候,我总看着他们家的瓜地流口水。
我当兵后,小晟父亲去世了。几年后,小晟妈再嫁了,男人来自苏北。外乡男人脾气很好,成天到晚沉默着,除了干活就是干活,家里拿主意的是小晟妈。村里人说,没想到她还挺有福气的。
在沉默的村庄,沉默的老人房,沉默的拆迁安置楼,小晟妈飘荡的话音是一个特别的记号。这个记号,能让我记起很多吾乡往事,能让我记起很多世间冷暖。现在,这个记号毫无征兆地坍塌了。
一个人患上老年痴呆,是一个大事件。
在吾乡,老年痴呆是仅次于死亡的消息。宣布一个人老年痴呆,不需要医嘱,人们凭借观感,作出判断。TA还在我们的身边存在着,但是没人觉得这种存在是一种存在,就像是他们与世界隔着一堵墙。
我打量过老年痴呆患者的神情,是那种忘我的木然。他们下意识、没来由的笑透着纯,也透着诡异。
某天,我大声喊着路边行走着的一个极其熟悉的老妪,老妪回头满脸是笑地看着我,却毫无语言上的反应。旁边的人告诉我,“别理她,老年痴呆了”。
“别理她”。我的心一阵刺痛,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惜别。
很多新闻描述过,从走失的老人的口袋里,找到儿女的电话号码和地址。有的老人,脖子里挂着钥匙,却满世界找不到世界上唯一的门锁。他们不再理解那些关于一间房子、一个小区、一条马路的信息,但是却知道自己在焦虑着。
我的外婆,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和父母去看望她,她已经对曾经最疼爱的长外孙毫无印象。自言自语间,有时会突然问:“你是哪一个?谢谢你来看我啊。”
每一个被阿尔茨海默症找上的人,都是失忆者。人活一世,一直在努力“装满”,可突然之间,就被清零了。他们告别世俗社会,活回婴儿般的一个人的世界。
我们谁都不能体会那种放掉世间包袱,进入一种世事与我无关的境界的感觉。但是我们明明知道,他们越是“简单快乐”,越是不纠缠亲情和人情,越是不追问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们越无法释怀。
我们宁可他们的身心有那么一点点“负累”。别那么轻,别那么“无关”。
我读龙应台的《目送》,一遍遍地看她和母亲相处的那些事。她的母亲也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她选择辞职去“陪母亲走最后一里路”,这和金晓宇在家照料母亲,是相似的。
这“最后一里路”上的珍贵和苍凉,以及那些回报和救赎,最终还是在世间某个地方留下来了。

责任编辑:陈才 图片编辑:胡梦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