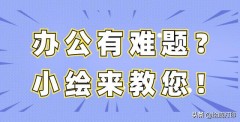文/程靖
编辑/漆菲
“在阿富汗的中国人”过去是一个仅有百余人的小群体。去年8月,阿富汗局势天翻地覆,绝大多数中国人已随撤侨专机离开,留下的人一度仅为个位数。
如今,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掌权已近半年,一些曾离开的中国商人重新回到阿富汗,另一些留守的人也开始探索这个“搬不走的邻国”的新机遇。
多位中国在阿商人和研究者告诉《凤凰周刊》,塔利班政府对乱局中留守的中国商人很是感激,对中国项目态度也十分积极,但囿于阿富汗目前严峻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以及西方国家撤离后流失的购买力,新政府能在何种程度上助力中阿经贸关系发展,仍是未知数。
收购松子时曾与塔利班“狭路相逢”群山绵延,高大茂密的松树林顺着山坡向山脚延展,积雪轻覆其上,露出一片片高耸的树尖,初冬季节的空气凛冽而清新。
中国人王翰(化名)2020年11月前往阿富汗霍斯特省(Khost)的山区收购松子时,见到的便是如此景象。这里是兴都库什山脉余脉苏莱曼山的西沿,平均海拔超过1000米,阳光充足,从印度洋吹来的西南季风让山上雪水充沛,适合松树的生长。
霍斯特省、帕克提卡省等10多个省份的山区素来以出产松仁饱满、口感优良的松子闻名,山间的城镇上散落着好几个松子干果集散地。其中霍斯特省的松子产量占全国40%以上,许多家庭世世代代从事松子采摘、包装和销售工作。
王翰早在2018年就来了阿富汗,之前与阿富汗政府合作过两年,最终因数个冗长而无效率的承包工程而感到精疲力尽。之后,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发现了松子的商机。

阿富汗霍斯特省出产的松子
2020年初冬,王翰和友人决定前往霍斯特省山区选货。霍斯特省与巴基斯坦西部的瓦济里斯坦地区接壤,自塔利班政权上一次垮台后,那里地势复杂的山区成了本·拉登所训练的“基地”组织激进分子们天然的庇护所。与此同时,塔利班控制着全国为数不少的农村地区,山区更是散兵游勇的地盘。
王翰和友人雇了一名本地司机,三人坐进一辆毫不起眼的旧车,头一天晚上9点就出发了。王翰解释道,为了躲避路上的意外情况,长途车多要走夜路直奔目的地。从喀布尔到霍斯特的路途并不算远,据他回忆,一路几乎都是砂石路,加上冬季积雪很厚,路况不佳,250公里的路程足足开了8小时。
最终,他们抵达了一个山村。山民们的住宅散落在邻近的几座山坡上,这边十来户,走上一两里地,又是八户十户。恰逢松子成熟的季节,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出动了,王翰形容,“年轻力壮的爬到树上打松果、敲松子。敲下来的松子,村里有人挨家挨户地收,收来了再供我们选购”。

政权更迭后,阿富汗松子生产联盟社媒主页显示“已关闭”
他和友人选完松子、装完货后已是凌晨。天蒙蒙亮,一行人再次启程。开到半路,一名揣着枪的武装人员拦住了一车人的去路,王翰心想,“完了,遇上塔利班了”。
“当时我特别害怕,心跳都加快了。我心想,‘你们(塔利班)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别伤害我的人就行。”那时的王翰从未与塔利班正面“交锋”过,在心里做好了最坏打算,“十多吨松子要是全部扣给塔利班,我也认了”。
所幸的是,对方并没有要他的货,而是按照货量收取了50000巴基斯坦卢比(约合1800元人民币)的“过路费”后就放行了。
王翰解释说,霍斯特省邻近巴基斯坦,阿富汗一侧的交易多用卢比进行。事实上,几年前“阿富汗松子”在中国市场上尚无姓名,甚至被冠以“巴西松子”的名号,即巴基斯坦西部山区出产的松子。这不仅是因为巴基斯坦西部山区也产松子,更因为阿富汗早年没有直达中国的运输渠道,只能借道巴基斯坦出口至其他国家。

霍斯特省的山区
阿富汗松子上热搜,但生意没那么好做那是王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霍斯特山区。
松子是季节性作物。他原本打算第二年冬季再到山区进货,但在2021年8月,塔利班以兵不血刃之势火速夺取政权,阿富汗一夜“变天”。王翰担心遇到危险,政局平稳后再没离开过喀布尔。
自那以后,王翰便委托本地收购商进行采购,后者在山区向农户收购松子,运至喀布尔的工厂。工厂雇用了女工,手工挑选品相好的松子,将这些松子运送至国内,再由国内工厂炒制、销售,整个流程通常不超过20天。
王翰依托的是中阿之间2018年11月开通的“松子空中走廊”。这条航线从喀布尔直飞上海,松子下午从喀布尔装上飞机,经过六个半小时的飞行即可到达上海,国内时间一早收货、清关,出关后马上就能进厂,便利显而易见。

阿富汗松子。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阿富汗松子的年产量有2.3万吨,但过去常因内战战乱和运输不便而滞销,或只能以极低的价格走私到巴基斯坦。据统计,2017年阿富汗仅有400吨松子出口到中国。阿富汗经济部曾预测,若停止通过巴基斯坦走私松子,阿富汗每年从松子获得的收入将增至10亿美元。
而当“松子空中走廊”项目启动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有超过1000吨阿富汗松子直飞中国。
一年后,阿富汗农业、灌溉和畜牧业部副部长加福里(Hashmatullah Ghafoori)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从2019年起的五年内,阿富汗将对中国出口6.2万吨松子,这将为农民、贸易商和国家财政带来22亿美元的收入。此后,阿富汗松子的年出口量保持在3000吨-5000吨之间。
然而好景不长。2021年8月,塔利班夺取政权后,阿富汗对外交往的官方渠道几乎全部中断。随后美国对阿富汗实施金融管控,阿国内现金短缺,本地货币阿富汗尼迅速贬值、物价飞涨,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
于是,塔利班政府向中国紧急求援,希望中国能帮帮他们。中方特事特办,更新了包机飞行许可,再次打通中阿“松子空中走廊”。同年11月,中国电商主播李佳琦搭档央视记者王冰冰首次在电商平台上为阿富汗松子“带货”,一上链接后,12万罐松子迅速售空。不久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在外交部记者会上为阿富汗松子“背书”。
一时间,“阿富汗松子”登上中国社交平台的热搜榜。抱着对阿富汗政局变换的关注以及对“远方的人”的挂念,不少网友涌进售卖干果的网店,追问着,“阿富汗松子还有吗?”

松子选品工厂
李佳琦卖出的首批12万罐松子里,就有王翰通过恢复后的首条航线运往国内的货品。他很感激网红主播们的“带货”,认为这的确帮阿富汗松子打开了销路,但整体上,这一年的生意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那么好做。
他坦言,2021年是松子产量的大年,但果小、价格低,更致命的是,美国撤军后,原先由美国政府给予阿富汗航空公司的物流补助不再发放,松子的运费一度从每公斤1.5美元飙升到4.5美元,今年初才回落到4美元左右。
和松子的出货价相比,如此高昂的运输成本让王翰感到压力重重:即使是品相最好的大果,松子季初价格最高时每公斤也才185元人民币;小果的价格为每公斤100元人民币,但最低时降至80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松子空中走廊”仓位有限,王翰有时还要“抢位置”,否则就要等下一批。他想过将松子经由巴基斯坦走海运运回中国,但海运路程长、不可控因素多,“松子是一种很娇贵的果实,在海上漂得久了,容易受潮、发霉。海运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松子的品质就大打折扣了”。
相比拥有厂商渠道的中国商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本地商人收购的松子一旦滞销便只能放入冷库,如此一来这些松子会流失水分,而流失质量就是流失金钱。
王翰说,喀布尔街头小贩们的手推车里,通常都是些个头小、品质不那么好的松子,以前松子卖得便宜,当地人也爱吃,“但自从发现能卖到中国赚钱,价格还年年上涨,大家都舍不得吃了,把品质好的都拿去出口”。
2018年11月6日,在首架松子包机起飞前的启动仪式上,时任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说,“随着松子出口到中国和其他国家。我们的目标是将阿富汗变成一个出口国。”
加尼的讲话壮志凌云,但事实上,连年战乱让经济基础薄弱的阿富汗极度依赖进口,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2018年,阿富汗的年出口额达到创纪录的8.75亿美元,但仅从中国的进口额就超过了这个数字(9.78亿美元)。
而在塔利班执掌政权后的2021年,小小松子的创收显得更为珍贵。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对《凤凰周刊》指出,松子价值较高,且年年涨价,如今阿富汗出现了经济危机,松子带来的现金流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流动性危机。
但他也提醒说,松子作为一个小型支柱产业,意义巨大但拓展空间有限:阿富汗每年能达到出口标准的松子不过七八千吨,而在自然状态下,一棵松树生长20多年才能结出果子,采摘依赖山区的野生松树,当下产生的效益难以被大规模复制。

阿富汗霍斯特省的松树林
朱永彪认为,未来除了干果贸易外,中阿间在“短平快、小而美”的轻工业项目上有不少可发掘的领域,例如防疫物资、食品加工等,而前者尚未有人进驻。
新政府财政吃紧,人人“勒紧裤腰带”2021年11月,离开阿富汗近一年的孟晓丽又回到了喀布尔。
孟晓丽所经营的是不间断电源(UPS)和稳压器业务,这是一种保护电脑服务器不受断电损害的设备。阿富汗电力基础设施不足,停电是家常便饭,但数字化办公不能没有电脑。过去,在阿富汗的国际组织、外国企业,还有阿富汗政府、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机构,有不少是孟晓丽的客户。
孟晓丽2003年辞去了国内的工作,和丈夫一起来阿富汗创业。丈夫是电源工程师,两人很快就确定了业务方向。彼时阿富汗市面上出售的产品没有保修期的概念,孟晓丽便给自己的设备增加了三年保修服务。因为诚信、专注,她逐渐成了阿富汗IT市场的名人,所经营的电源品牌也成为当地无人不知的存在。她本人还成为阿富汗华商协会的会长。
去年8月,人在国内的孟晓丽没能亲眼见证阿富汗一夜“变天”的场面。但由于放不下生意,11月时她再度回到阿富汗。
短发的孟晓丽过去从不戴头巾,这次出发前她的心里直犯怵,便准备了一条头巾。抵达喀布尔那天,孟晓丽发现街上的男人都留起长胡子,过去年轻男子刮得干净整洁的面庞一个也没见到,她一下子觉得,“这不再是从前的阿富汗了”。
第一次出门时,孟晓丽套上了阿拉伯式的女士长袍,但感到行动极其不便。在街上,她看到一些本地女性没穿长袍,而是穿着彩色大衣。于是她不再穿长袍,只是出远门时会戴上头巾。
不久后,孟晓丽去银行办事,接待她的是一位戴着头巾的女员工,对方和她闲聊,告诉她几天前塔利班来过,要求她把鼻子和嘴巴遮起来,手套也要戴上,但她以戴手套不方便工作为由拒绝了。
几天后她再去银行,又见到了那位女员工,对方包着头巾,但仍然露着脸。孟晓丽猜测,这是因为塔利班一方面要恢复教法规范,一方面又要迎合外界的意见,所以对于着装要求仅做出“建议”。当地年轻人大多从父辈那里听说过塔利班上一次掌权时的严苛,他们出于恐惧也多会照做。

2021年9月,一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在街头巡逻
但如今,阿富汗全国上下的经济形势只能用“惨淡”来形容。孟晓丽的店铺开在喀布尔的电脑城,周边销售的都是电脑、打印机等IT设备。去年政权更迭时,好多店主蒙受了损失,一些和前政府签下的单子还没结款,政府就倒台了,有的商户甚至赔了100多万美元。
随着国际机构纷纷撤离,也让她失去了一大批客户,订单量下降了70%-80%。新政府的生意也不好做,孟晓丽说,“现在各级政府都是塔利班的官员,他们文化程度不高,用电脑的需求不大,自然也不会来配置电源”。
在她看来,新政府的财政情况也是极度紧张,从上到下都在“勒紧裤腰带生存”。她偶然瞥见新政府官员吃午饭的场景,盘子里只有米饭和豆子,“以前我去政府谈事情,对方会招待茶水、糖果;最近再去时对方只提供茶水,连糖果都不提供了”。
由于阿富汗国内现金严重短缺,塔利班政府对银行实施管制,每人每周最多只能取款200美元(后放宽至400美元),公司账户每周只能提款总额的5%。
资金管控甫一实施,让在阿中国商人叫苦不迭。孟晓丽不敢再往银行账户存钱,只能将挣来的现金锁进保险柜。有人告诉她,若想一次性提取大额现金,只能求助黑市——例如,若要从账户中提取2万美元,需向“经办人”支付2000美元的“好处费”。虽然从没验证过,但她相信这类操作一定存在,“现在大家都太穷了,为了取钱,什么办法都会使出来”。
孟晓丽最近听说,一家本地银行的招标因无人参加,最终流标,原因是参加招标要先往银行存一笔保证金。她算了一笔账,“假设一笔生意的利润能有20%,现在阿富汗尼贬值很快,等到政府付款,钱已经不值钱了,并且很可能卡在账户里取不出来,意味着还要赔一笔钱”。

2021年9月,喀布尔街头,人们在银行外排队取钱
孟晓丽在阿富汗经商近20年,她坦言,最近的情况快到自己能承受的极限,“我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比现在更糟糕,但既然我回来了,能做的就只有等待”。
她的公司有三位阿富汗籍员工仍在坚守,他们都很珍惜这份工作,“现在一个七八口人的家庭,能有一个成年人挣钱,算是比较好的了。普通老百姓也不奢求生活质量,能把最难的时候熬过去,别饿死就很好了。”
但她依然对阿富汗的未来抱有一丝希望,“如果塔利班政府能更加包容,国际上有政府能承认它,各国的使馆、国际机构可能会回来。但这一切取决于现政府的行动,如果它能让世界慢慢接受它,事情就会一点点好起来。”

喀布尔街头,车窗外乞讨的小女孩
“其他人全跑了,只有你们中国人还在”说起中国企业进驻阿富汗市场的桥头堡,不能不提中国城。
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中国城大楼高11层、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内有商场、办公室。去年8月阿富汗“变天”时,绝大多数在阿中国人都随着中方撤侨专机离开,中国城的几位管理者留了下来,一度成为从阿富汗向国内发声的重要渠道。
中国城于2015年立项,经过数年的筹备和招商,于2019年9月起试营业,2020年7月正式挂牌营业。据执行董事余明辉此前介绍,商城经营的主要产品有浙江的注塑机、天津的电线电缆、河北的日用化工产品和江苏制造的鞋、服装、涂料等。
中国城运营总监李西京向《凤凰周刊》介绍说,过去多是阿富汗商人来中国采购商品,货物质量参差不齐,以廉价小商品为主,导致阿富汗人对“中国制造”普遍印象不佳;他们则希望通过中国城将中高端产品引进阿富汗国内,吸引白领及有更高消费能力的人群。

阿富汗中国城
李西京是2019年9月起常驻喀布尔的。但没过多久新冠疫情暴发,中国商人出境考察活动大幅减少,给他的工作带来巨大影响。他认为自己来之前对阿富汗市场做了充分的考察,对局势也有预判,但千算万算还是没料到疫情的发生,还持续了如此之久。
2021年春季起塔利班的“反攻”让全国上下进入紧张状态,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纷纷撤走,整个市场陷入疲软。尽管早就做好政权更迭的预案,李西京依然没想到局势变化如此突然。
8月15日当天,得知塔利班已经进入喀布尔,李西京立马要求中国城的商户将物资收好,拉下卷帘门,防止社会动乱对商铺造成冲击。员工们还把商城门口的中国、阿富汗和商城的三面旗帜降了下来。
为了安全起见,中国城暂停运营了几天,但很快恢复营业。李西京说,由于商城面对中高端客户,以前商城保安几乎不对客户进行搜身,塔利班掌权后的一段时间里,商城加强安保,对一切外来人员进行搜身检查。但当9月中下旬局势相对平稳后,搜身也停止了。

喀布尔中国城外竖立着中国、阿富汗、商城的三面旗帜
和其他经商者一样,中国城的商户也要面对经济危机下阿富汗人购买力下降的难题。近半年以来,阿富汗尼兑美元贬值了一半,以至于物价上涨了50%甚至翻倍。多重因素下,阿富汗人生活捉襟见肘,遑论购置消费品了。
过去半年,李西京接到不下十次上门或电话询问,都是来找工作或毛遂自荐做翻译的,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曾来过中国留学的青年。由于经营情况不好,中国城没有接收他们。另一方面,塔利班上台后,商城担心惹上麻烦,解雇了四名阿富汗籍女性员工,想等到经营情况稳定了再雇用她们。
加尼政府时期,中国城曾向政府申请加装广场护栏,手续还在办理中,政府就倒台了。李西京回忆,补办手续时,商城派出阿富汗同事和塔利班进行接洽,对方一听是中国城派来的,立刻汇报上级,上级亲自接见了同事,还询问中方有什么麻烦、困难,并承诺若有需要可以找他,他会出面处理。
李西京说,政权更迭后,有不少人找到中国城管理层想要建立联系,他们都保持谨慎、一一拒绝了。直到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们才开始恢复对外接触。
经此一役,阿富汗商务部、矿产部、公共工程与铁道部等多个部门全部“换血”,只有承担政府职能但属民间机构的“国家贸易办公室”没有大的人员变动。
让李西京感到欣慰的是,这些部门均对中国城的工作表达了感激,“有人说,‘其他国家的人全跑了,只有你们中国人还留在这里,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也会大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正因此,2021年5月中方承诺在阿投资的300兆瓦燃煤发电项目得以继续推进;政权更迭时卡在海关的一个海运集装箱,也在新政府的协助下顺利通关。
李西京还记得,在与新任公共工程部长见面时,对方表示,中国城项目做得不错,他们早有所耳闻。但除此之外,中国城的商户们还未感受到“变天”后营商环境的实质性变化。李西京猜测,这是因为新政府正忙于国家建设和民生问题,其他方面还顾不上。
2022年伊始,中国城团队已有一半员工重回工作岗位。接下来,李西京和同事们将筹办阿富汗首届中国商品技术展销会及第二届中阿商务洽谈会。去年的博览会吸引了十五六家中国企业参加,展出商品包括电动车、取暖器、风扇、塑料制品、家具、日化等中国商品,吸引了在阿外国企业的关注,今年将加入技术交流环节。
李西京在与阿富汗人交谈时,对方希望能引进中国的技术,或者通过和中国人合办企业来促进生产和对外贸易。在他看来,中方2008年在阿投资建设的明海钢铁厂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自明海投产后,阿富汗逐步建立了25家钢厂,“可以说,我们中国人的钢厂带动了阿富汗一个产业的发展。”
中国人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过去,王翰在喀布尔坐办公室,每天与阿富汗政府打交道。他当时所在的中国企业承包了当地的光伏能源项目,但对接的公务员中无一拥有相关专业背景,在审批工程时没法提出针对性修改意见,却常常关注一些无关核心技术的问题。
“按照中国人的思路,电站肯定要设计成长方形的,内部空间可以合理安排设备。但他们非要把方形房顶改成圆的,可我在喀布尔,从没见过哪座房子的屋顶是圆的。”王翰觉得,对方似乎以为提的问题越多,就越显得他们专业。
王翰记得,每次将修改后的方案提交上去后,对方回复时间都长达两三个月,而终于等来的答复,却总伴随新的修改意见,这意味着可能又要经历两三个月的等待。就这样,王翰所在企业提审的两个项目,直到前政府垮台还没获批。
在王翰眼中,加尼政府内部任人唯亲、尸位素餐、效率低下,只有拖关系、有背景才能进入政府部门上班。
当他改行经营松子贸易后,更是见识了阿富汗惊人的贫富差距。王翰收购来的松子通常交给喀布尔一家分拣厂处理,参与分拣的女工每天工作8小时,一天的工钱是250阿富汗尼(约合16元人民币),一个月也就300多元人民币,“她们打零工,并不是每天都有活干,一个月能工作20天就已经很不错了。”

女工们在工厂挑选松子
但他觉得,阿富汗人懂得知足常乐,“买个馕,两三个人吃,再配点茶水,就是一顿早饭了”。
最近半年来,王翰感觉过去频发的爆炸恐袭事件少了,但因为普通人生活潦倒,小偷小摸、抢劫事件越发普遍。他雇用的司机最近就被抢了手机、手表和钱包。为了安全,他的“生存法则”如故:人在院内上车,除了办事尽量不出门,晚上绝不出去。
虽然眼下光景不好,他仍打算留在阿富汗经商,没有松子的时节做些干果、藏红花的买卖。他没有给自己的停留设定期限和目标,“这得看阿富汗的产量,看国内需求,还得看这里的安全局势,一些都难预测”。
“谁都很难说会在这里待多久。有生意做,有活干,就待着,”王翰笑称,“都是为了生活嘛。”
【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观象台媒体】所有,今日头条已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家授权,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